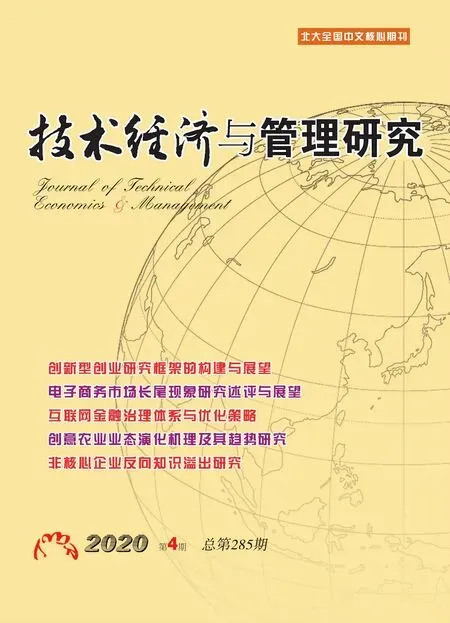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和股價關聯性分析
——基于SVAR模型的實證研究
夏 博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北京100036)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年至2004年):為抵御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主要采取增發長期建設國債、支持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充實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提高部分出口商品退稅率等措施。第二階段(2009 年至2012 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財政政策由穩健開始轉向積極,主要運用增加支出、加大投資、減稅等政策手段,拉動社會總需求,有效刺激經濟增長。第三階段(2013年至今):積極財政政策在收入側、支出側同時發力,赤字率不斷攀升,政策擴張力度尤為顯著。總體而言,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已經發生轉型:其一,從單純的需求管理轉型到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二,從單純的經濟政策轉型到包括社會政策的綜合性政策。
股票市場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晴雨表,與宏觀經濟運行密切相關,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股市發展一方面可以增加投資渠道,改善投資者信心和預期,為促進市場主體擴大投資提供充裕的流動性;另一方面股市價格波動也會阻礙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為財政貨幣政策制定實施帶來不利影響。因此,研究財政政策和股市發展的互動關系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且也是發揮財政金融政策協調效應、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內在要求。
本文選擇我國2013-2018年的月度數據,構建具有財政支出(CZ)、經濟增長(GDP)、通貨膨脹率(CPI)、貨幣政策(M1)和股票價格(SP)等變量的SVAR模型,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對積極財政政策和股票價格波動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本文從積極財政政策的視角探究股票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可為研究制定相關宏觀政策奠定一定的理論基礎;同時運用實證結果,對不同影響因素和股價波動的相關性進一步分析,對于促進股票市場健康運行,助力宏觀經濟平穩增長,也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從國外學者研究來看,Saraswati P.Singh 和Prem P.Talwar(1982)采用二元和多元自回歸模型檢驗了財政與股票價格之間的因果關系。S.Poon 和S.J.Taylor(1991)研究發現,宏觀經濟變量和股票指數變動相關。Eva Liljeblom 和Marianne Stenius(1997)利用芬蘭1920 年至1991 年的月度數據,分析了股票市場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股票波動性變化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以上可能與宏觀經濟波動性有關。Baldacci Emanuele,Gupta Sanjeev 和Mulas-Granados Carlos(2009)研究了1980-2008 年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118 起系統性銀行危機中財政政策的應對效果,發現股市往往恢復得要比實際產出更快。Foresti Pasquale 和Napolitano Oreste(2017)采用面板分析法,研究了歐元區11 個成員國財政政策對股市指數的影響,結果表明財政政策影響股市,隨著公共赤字的增加(減少),股市指數下降(上升)。
國內學者也進行了相關研究。比如,許均華和李啟亞(2001)采取回歸分析技術,構建政策綜合指標曲線,得出連續性宏觀政策與我國股市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史代敏(2002)運用干預模型分析政策影響股市波動的特征、深度和廣度,研究表明政策沖擊對股票市場的影響不僅是顯著的,而且影響幅度非常大。王春峰、李雙成和康莉(2003)通過事件研究方法檢驗了中國股市對政策性信息的過度反應問題,并發現政策對市場具有更重要的影響作用,從而體現出較為明顯的“政策市”特征。董直慶和王林輝(2008)基于我國時序數據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結果分析,認為財政政策對股市作用存在階段性并有著非中性和非對稱性特征,即政策變化對股市存在沖擊效應。田金方和王文靜(2018)使用五分鐘高頻數據,并運用事件研究法實證分析了金融危機后國家出臺的宏觀政策對股市的影響,其結果顯示,金融危機后國家實施的財政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波動,特別對于股票收益率的影響效果更明顯。
總的來看,國內外學者有的從宏觀經濟波動維度進行研究,有的從宏觀經濟變量視角,有的從財政貨幣政策與股市聯動方面,有的則從宏觀政策影響角度,而單獨從財政政策方面或者積極財政政策方面對股市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本文試圖從積極財政政策的視角探究對股價波動的影響,在促進股市健康發展的同時,為制定相關宏觀政策提供一定理論基礎。
三、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和發展
1.積極財政政策的概念
目前,對積極財政政策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具體而言,有以下說法:
百度(baidu)對積極財政政策定義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投融資進行國家基本建設與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經濟結構,引導、推動、扶持產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投資,增加就業,擴大內需,使本國經濟平衡可持續發展。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經濟穩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
葉振鵬(2002)認為,積極財政政策是在下面兩個含義上界定的:一是與自由市場經濟時期政府“不干預”相對而言的,消極政府變為積極政府,即政府從不干預經濟到積極干預經濟在財政政策上的體現;二是與財政政策中的“自動穩定器”相對的,是一種反周期的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或斟酌使用的財政政策的另一種表達。
陳共(2003)認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依法增加稅收、合理調整支出結構(簡稱為增收節支),適時適度地發行國債,有效地運用各種財稅手段,充分發揮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化資源配置、調整收入分配以及促進經濟穩定和發展的職能。
劉尚希(2018)認為,財政政策應該積極到什么程度,取決于公共風險與財政風險的平衡。中國社會的公共風險越來越大,經濟風險、金融風險、社會風險、老齡化等問題都正在轉化為公共風險,亟需財政應對,所以實際上財政風險也在加大。從風險的角度來看,所謂的財政政策就是把公共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比如說把銀行的金融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把企業的經營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把社會居民的個人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財政的手段就是減少稅負,讓企業、老百姓負擔更輕,也就承擔更少的風險;同時財政還可再增加支出,承擔更多的風險。所以,財政風險實際上由公共風險轉化而來,財政政策的擴張、收縮或轉型也都取決于公共風險的狀態。一旦公共風險的狀態發生變化,毫無疑問財政政策就要進行相應調整。
2.積極財政政策的發展軌跡
(1)1998 至2004 年。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出現內需嚴重不足和通貨緊縮現象,經濟增長減慢。為此,我國政府決定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和方向,及時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主要措施有三項:一是增發1000 億元長期建設國債;二是向四大原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2700 億特別國債;三是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截至2003 年,累計發行6600 億元長期建設國債,帶動銀行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形成3.28萬億的投資規模。扣除價格變動因素,五年間全國水利建設投資3562 億元,相當于1950 年到1997 年全國水利建設投資的總和;五年間全國公路建設投資12343 億元,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投入5800 億元,都達到1950 年到1997 年全國公路建設投資總和、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投入總和的1.7 倍;五年間高速公路由4771 公里增加到2.52萬公里,從居世界第39 位躍升到第2 位。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重大國計民生建設項目相繼開工建設。

圖1 1998-200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數額情況 (億元)
(2)2008 至2012 年。2008 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蔓延到全球各經濟體。中國受其不利影響,各項主要經濟指標持續回落,經濟增速明顯放緩。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我國財政政策由穩健轉向積極,出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其主要內容為: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體育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快地震災區重建各項工作,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實施增值稅改革,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同時提出到2010年底實施4萬億元的政府投資計劃。從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看,由2008 年的62592.66億元擴充到2012年的125952.97億元。

圖2 2008-2012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數額情況 (億元)
(3)2013年至今。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需要綜合考量,不再是單純的經濟職能,而是統籌推進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文明等方面。其內容主要包括適度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地方債規模、推進減稅降費、加快支出進度以及保障改善民生等。這一時期,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效,社會性支出規模不斷擴大,財政赤字率逐步上升。

圖3 2013-2018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數額(億元)和赤字率情況

表1 2013-2018年全國社會性支出情況表 (億元)
四、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
1.理論分析
(1)IS-LM 理論。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擴張型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減稅降費等措施刺激有效需求增加,拉動經濟增長,進而影響股票等資產價格的波動。其作用機理可以用IS-LM 模型來分析,它描述了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相互關系。
馬拴友(2001)估計了中國的IS-LM模型,計算我國的財政政策乘數大約等于2,并測算了歷年財政調控的效應,發現財政政策是調節總需求的重要杠桿。郭慶旺、呂冰洋和何乘材(2004)選取1999年1月至2003年4月的月度數據,利用IS-LM模型測算積極財政政策乘數效應,結果表明積極財政政策乘數在1.6-1.7 之間,財政政策在拉動內需、抑制經濟衰退方面效力顯著,說明政府選擇財政政策為主要穩定工具是正確的選擇。李永友(2006)借助IS-LM模型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平滑經濟波動能力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要提高中國穩定性財政政策有效性,提高不同財政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政策工具之間的協調效應至關重要,而且對經濟高漲時期政府財政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也至關重要。張延(2010)從動態均衡調整的過程出發,運用幾何圖形法研究IS-LM 模型中的財政政策效力變化,在LM曲線斜率不變的條件下,由稅率下降導致的IS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的效力越大;在IS 曲線斜率不變的條件下,貨幣需求收入彈性下降和利率彈性上升,LM 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的效力越大。
(2)公共風險論。劉尚希(2018)認為,當前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種不確定性,這已經成為一種常態。Eugene F. Fama 和G.William Schwert(1977)估計了1953-1971年期間各種資產對通脹率的預期和對沖程度,發現股票的收益率與通脹率的預期直接相關。鄒新月和代林清(2010)對影響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宏觀因素進行理論分析,認為實際利率、預期通貨膨脹率以及風險溢價因素均會影響股價波動。熊偉和陳浪南(2015)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下研究了股票價格波動原因,得出股票波動、股市風險和投資者情緒走勢呈一致性。王永蓮(2017)基于混頻數據模型對我國股票市場波動和經濟政策不確定的關聯性進行了系統研究,結果表明二者的關聯顯著存在,并且總體表現為正向相關。宿亮(2019)認為,2019年貿易摩擦、英國脫歐、貨幣波動等諸多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全球主要股市前景并不樂觀。面對這些經濟和社會的各類不確定性,積極財政政策應該如何作為?劉尚希(2018)提出,財政政策更要發揮“定海神針”作用,積極主動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持續不斷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改革深化注入確定性,把公共風險轉化為財政風險,讓風險不再擴散,使整個經濟社會狀況好轉,進而保持財政的可持續性。魏禮群(2019)認為,現代財政的新使命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新時代面臨的公共風險。
2.變量選擇、數據來源和模型設定
(1)變量選擇。本文選擇以下5個變量:①財政政策。財政支出具有乘數效應,可以反映出財政政策的擴張或收縮,因此本文采用財政支出作為財政政策的替代變量,記為CZ;②經濟增長。一般來說,在經濟學中用GDP 表示經濟增長,記為GDP;③貨幣政策。本文將狹義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替代變量,記為M1;④通貨膨脹率。本文選取CPI 作為通貨膨脹率的替代變量,記為CPI;⑤股票價格。本文選取每月末上證綜合指數的收盤價作為股票價格的替代變量,記為SP。
(2)數據來源和整理。本文采用2013 年1 月至2018 年12月的月度數據,共72個樣本期。所有數據來源于財政部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國家統計局網站、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中經網數據庫。整理數據時首先通過插值法將季度GDP調整為月度GDP,其次用X12 法進行季節調整,最后對變量取對數。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2。

表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3)模型設定和識別。本文選擇SVAR 模型,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對股票價格波動的影響。SVAR模型表達式如下:

其中:Yt為變量向量,C0和B為常數向量,Ai為參數矩陣,t為時間變量,p為滯后階數,μt為結構式沖擊。

為進一步識別模型,需對k 元P 階的SVAR 模型的結構式施加k(k+1)/2 個限制條件。因此對于上述5 個內生變量模型,需要施加10個約束條件。本文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6年的月度數據,因而選擇短期約束并做出如下假設:①財政支出不受當期經濟增長的影響;②經濟增長對當期通貨膨脹率影響程度為零;③當期股票價格與通貨膨脹率、財政支出、經濟增長和貨幣政策關聯不顯著;④貨幣政策對當期財政支出沒有影響。
(4)實證分析
①單位根檢驗。為避免“偽回歸”產生,本文采用ADF檢驗和PP 檢驗對所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經濟增長GDP、貨幣政策M1 和股票價格SP 三個變量的ADF 檢驗值和PP 檢驗值均大于臨界值,說明這三個變量是不平穩序列。因此,對所有變量進行一次差分處理后再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經一次差分后的所有變量均為平穩序列(見表3)。

表3 各種變量的ADF檢驗和PP檢驗
②滯后階數選擇。根據不同信息準則指標考慮,最終選取最優滯后階數為3(見表4)。
③平穩性檢驗。計算向量自回歸模型的特征根(表5),結果表明它們都在單位圓內(圖4),符合穩定性要求。
④協整性檢驗。對所有變量做Johanson 協整檢驗(表6),從結果中發現,不論是采用跡檢驗還是最大特征根檢,變量之間含有協整關系,VAR模型不會出現識別錯誤。
⑤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用于衡量擾動項的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的影響。圖5是脈沖響應函數曲線圖,橫軸表示滯后期數,縱軸表示沖擊程度,實現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個標準差偏離帶。從圖中可看出,在給通貨膨脹率(CPI)沖擊后,股票價格從當期開始下降,在第五期時達到最低點,然后一直平緩上升;對財政支出(CZ)沖擊后,股票價格開始下降,在第三期達到最低點后開始上升逐步趨于零;對經濟增長(GDP)沖擊后,股票價格小幅上升,第三期達到零后開始下降,在第四期時達到最低點后開始上升;對貨幣政策(M1)沖擊后,股票價格基本保持平穩波動態勢;對股票價格(SP)沖擊后,股票價格當期開始上升,在第二期達到最高點后開始下降逐步趨于零。

表4 滯后階數的選擇

表5 模型的特征根

圖4 特征根分布

表6 各變量Johanson協整檢驗結果
⑥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是將系統各個內生變量的波動分解成與各信息沖擊相關的組成部分,從而了解各沖擊對內生變量的貢獻度。表7的方差結果表明,股票價格對其自身波動影響最大,一直保持在55%以上;財政支出對股價變動的貢獻率從第一期開始逐步增大,此后一直穩定在13%左右,成為股價變動的重要因素;通貨膨脹對股價也會產生一定影響,說明當通貨膨脹控制在一定范圍內時,一些產業得到較快發展,股價隨之上升,反之經濟惡化,股價隨之下降;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對股價變化貢獻程度相對較低,不是股票價格變化的主要因素。

圖5 脈沖響應函數曲線圖
五、主要結論和對策建議
1.主要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結構式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圍繞積極財政政策對股票價格波動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
(1)在短期內,積極財政政策對于股票價格波動的沖擊效應更直接、更明顯。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對股票價格波動的刺激作用不顯著,對于低迷的股市,央行不應加大貨幣投放量對股票市場施加影響。
(2)通貨膨脹和股票價格波動具有顯著的關聯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采取政府投資、轉移支付和財政補貼等政策工具,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增加財政赤字,有可能導致赤字貨幣化效應,引起物價水平波動。物價水平上漲,帶動產品價格上升,公司利潤增加,股價相應上升;物價水平持續上漲,公司成本上升,商品利潤下降,同時會影響投資者的心理和預期,股價下跌。
(3)股票市場運行有其自身運動規律,自身沖擊影響是股價波動的主要原因。這特別地類似于化學中的布朗運動,具有隨機漫步的特點,其變動路徑是不可預測的。
(4)持續向好的經濟增長可以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但對于股票價格走勢來說,受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較小。

表7 各變量對股票價格影響的方差分解結果
2.對策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強化財政支出管理。從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不論是長期還是短期,政府支出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通過保持政府投入力度和支出強度,刺激產出增長,股票市場趨向利好,股價上揚。隨著政府支出規模的持續擴大,財政赤字壓力增大,CPI、PPI逐步攀升,實體經濟生產成本上升,通脹風險開始顯現,會阻礙實體經濟進一步發展。因此,應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厘清政府投資的邊界,積極開展政府投資項目的財政承受能力評估,要在滿足地區財政承受能力的條件下進行投資建設。同時加強政府投資項目的謀劃、論證和儲備,及時編制地方政府中長期投融資規劃,并與包含財政支出責任的中長期財政規劃相銜接,管理好通脹預期和風險,避免貨幣赤字化現象發生。
(2)加快推進中國股票市場高質量發展。股價波動與股票市場健康有序發展有著顯著的正關聯性。現階段中國股票市場還不完善,比如存在股票市場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行政干預存在、股票投機現象多、上市公司內部治理水平低以及股票市場監管有漏洞等問題,影響著各類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預期,制約著股市進一步發展壯大。在此情形之下,積極對標高質量發展要求,采取完善股票市場法律制度、健全股票市場運行機制、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市場職能、加強上市公司內部治理以及強化股票市場監管等有力措施,推動股票市場高質量發展,充分發揮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預警和促進功能。
(3)積極為股票市場運行注入確定性。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延遲企業或個人的投資、消費和支出,進而影響股票市場的預期和行為,而且股票市場過度波動會導致市場無序化,促使投機活動泛濫,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影響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要創新積極財政政策,著力為各類市場運行注入確定性,減少實體經濟內部、虛擬經濟內部以及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不確定性,穩定國民經濟;引導各類市場主體形成良好預期,降低消費、支出和心理的不確定性,有效防范和化解股票市場風險,助推股票市場實現穩定運行。
(4)發揮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同效應。財政方面,扎實推進減稅降費舉措,減輕實體經濟稅費負擔,降低實體經濟運行成本,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統籌好投資補助、以獎代補、投資基金等各種財政資源,支持引導實體經濟實現提質增效,帶動股票價格在合理區間內波動。金融方面,也要兼顧財政的承受能力范圍,保持適度的社會融資規模和充裕的市場流動性,保障實體經濟的合理融資需求;貨幣政策應避免對股票市場施加過多的影響,因為,這種影響不僅會干擾股票市場的正常運行,而且過多干預也會造成一定的道德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