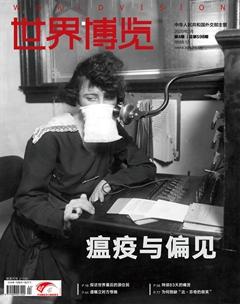皇帝的酒杯
汪洋

大明成化斗彩雞缸杯。
成化皇帝怎么也不會想到,他的名字是因為一只小酒杯而聞名于世的。2014年4月8日,香港蘇富比公司舉辦了一場“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品”拍賣會。會前,一件明代的小酒杯已經引起了收藏領域的廣泛關注。當這件小酒杯最后以2.8億港幣成交的時候,全世界為之震動。雖然在拍賣之前,收藏界已經對這件國寶級的藏品議論紛紛,但落錘的那一刻,人們仍然感到不可思議。
天價酒杯
這件酒杯的全名叫做“大明成化斗彩雞缸杯”。在拍賣之前,這件國寶級藏品的估價就在2億到3億港幣之間,拍賣僅僅是印證了專家們的判斷,并沒有特別地超出預期。而在此之前,這件雞缸杯于1980年被全世界最著名的古董商之一埃斯肯那齊收入囊中,后來轟動世界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也是被他拍下的。而1999年,同一件雞缸杯,以2917萬港元成交,創造了當時中國瓷器的拍賣紀錄。

明成化皇帝朱見深。
斗彩雞缸杯并非如元青花大罐那般橫空出世,它早已是家世顯赫、名震古今。事實上,只要我們稍稍了解斗彩雞缸杯在明清兩代的身世,那么它近幾十年來的表現,就根本算不上驚人。斗彩雞缸杯誕生于明朝成化年間,此后不久,它便迅速成為中國陶瓷史上的明星。明《神宗實錄》中就已經有“神宗尚食。御前有成杯一雙,值錢十萬”的記載,這是官方的說法。而《萬歷野獲編》里說“成窯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是文人的筆記。兩種記載在數字上也可相互印證。值錢十萬,換算成白銀是一百兩。博銀百金,不是黃金,意思還是白銀一百兩。以現在的銀價,折成人民幣還不到兩萬元。但以當時的購買力,卻極其驚人。一百兩白銀,在五百年前明朝的北京城,足以買一套不小的院落。

2014年4月8日,在香港蘇富比重要中國瓷器及工藝品春季拍賣中,這件繪有公雞、母雞領幼雛于花石間覓食“天倫”圖、小如掌中物的雞缸杯以總成交價2.8億港元拍出,刷新中國瓷器世界拍賣紀錄,買家為上海收藏家劉益謙,此舉轟動一時。
盡管如此,單純從價格上來判斷,還遠遠不足以說明雞缸杯在歷史上的地位。事實上,它在整個陶瓷文化史上舉足輕重。
雖然陶瓷在古代人們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生活中處處都有瓷器的身影,文人階層也鐘愛有加。但奇怪的是,文人士大夫對庸常的日用瓷器極少著墨,即便是文玩用具,也罕有提及。于是陶瓷的歷史上,被文人記載與談論的瓷器,少之又少。但雞缸杯,卻在歷史上反復被人提及、引人談論。這在整個陶瓷史上也是鳳毛麟角。
非但如此,歷朝歷代,無論是帝王的官窯,還是市井的民窯,都在不斷對雞缸杯進行仿制。最為著名的仿品,出自雍正與乾隆兩朝。皇帝不但命令御窯廠原樣仿制,還不滿足于依樣畫葫蘆,更要有自己的風格。雍正皇帝覺得成化斗彩顯得粗率,于是要求畫得更加細致更加寫實,甚至將這種改良的斗彩風格應用在其他的器物之上,杯之外,更有了碗,甚至筆筒。而乾隆皇帝則完全擺脫了原有器形與畫面的工藝及程式,不但杯子的形狀完全改變,畫面也重新設計,有些畫面的主題由雞變成了嬰孩,還配上了長長的詩句。而制作的工藝,也由斗彩變成了粉彩,因為粉彩可以把畫面表達得更為精細,比如雞的羽毛,真是細如發絲。
如此一來,雞缸杯非但自身是一件名作,進而還演變出一個家族。在這個家族身上,居然可以映射出彩繪瓷的歷史。這更使它在陶瓷文化史上的價值無可替代。如果我們進一步了解其在工藝史上的價值,更要為之驚嘆。
成化無大器
古玩領域流行這樣一個說法:成化無大器。說的是成化官窯,沒有大件器物的燒造。古玩行的說法不能全部當真,畢竟多是經驗之談,但很多時候大體不錯。成化一朝,少有大件的器物傳世,小件的名作倒是不少。人們容易認為成化朝少有大件的器物,恐怕是工藝上不及前朝。畢竟,大件的瓷器總要比小件的難燒。但這實在是個大大的誤會。
比如成化時期的高足杯。高足杯又叫把杯,因為足像個把手,據說是符合蒙古人的習慣,在元代開始流行。高安出土的一批窖藏元青花,共有19件,其中有9件都是把杯。另外還有9件大瓶、大罐,任何一件的體積都超過9只把杯的總和。有趣的是,大件的瓶瓶罐罐都燒得精彩紛呈,而所有的把杯幾乎全部燒得歪瓜裂棗,可見有時候小件的燒造并不比大件容易。
我們要從哪里看出這樣一件小小酒杯的精彩與技藝?
即使是在博物館里隔著厚厚的玻璃欣賞,您也一定很快會發現,雞缸杯完全是一種半透明的狀態。我們很容易觀察到這樣一個小杯的杯壁極薄而且透光。即使走進一家現代的瓷器店,售貨員也常常會用一個強光的手電筒對著瓷器的內部照射,讓您贊賞所銷售瓷器的薄與透。的確,即使放在今天,這仍然令人稱嘆。但雞缸杯的燒造時間,距今已有五百余年。而歐洲燒制出第一件硬質瓷,還要在它誕生兩百多年之后。于是我們可以想象,這在當時是一個多么驚人的成就。景德鎮瓷“薄如紙”的美名,也由此開始。
做到薄而透之所以異常困難,首先在于對瓷土材料的加工處理以及配比都有更高的要求。如果胎體較厚,即使胎壁內偶有雜質,也很容易被忽略。而器身一旦做得薄,所有的瑕疵就都容易被放大,于是需要對瓷土進行更為精細的淘洗與加工處理。此外,胎壁一薄,胎體的硬度就要更高,否則燒制時很容易變形,這就要求對高嶺土與瓷石的配比進行調整。而每一次的調整,釉料以及燒成溫度都需要進行相應的改變。這些調整說起來容易,卻都需要反復的嘗試才有可能最終達成,甚至還可能以失敗告終。單單提升材料還遠不足以取得這樣的成就。沒有工藝的配合,一切都是鏡花水月。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雞缸杯的器形,會發現它極為精巧:比如口沿的部分微微外撇,與底部的線條相呼應;底部的處理也很巧妙,從外面看,杯子沒有“足”,其實是把足做成內凹,隱藏了起來,這樣的處理方式叫“臥足”;杯口圓,非常周正,很少變形。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其實都需要依賴高超的技藝。
一個小杯的成形,主要有拉坯與利坯兩個環節,都是在轉動的輪車上完成。拉坯成形是大多數圓形器比如碗盤之類的基本成形方法,至今仍然被廣泛使用,電影電視中常常可以見到。《人鬼情未了》中,女主人公雙手隨著輪車的轉動將濕潤的泥土塑造成自己希望的形狀,就是拉坯。拉坯時,泥需要混合比較多的水,拉好的坯于是看上去濕漉漉的,行里叫“濕坯”。濕坯本身就難以做得太薄,因為胎坯根本就支撐不住,放在那里,可能就軟了。同時,手與濕泥接觸,也完全無法讓表面光滑并保持絕對的均勻,燒出來的瓷器不但表面不夠平整,也一定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變形。
為克服這一不足,制瓷界發展出了另外一項工藝,就是利坯。利坯也叫修坯,是在濕坯晾干之后借由鐵質的工具完成。這是對器形精修的過程,器形最終的定形與所有線條的精微表達,都需要借由這道工序。
比如口沿微微外撇,看似不經意,但其實很見功夫與巧思。因為杯壁本來就薄,口沿既要外展,就需要特別小心,稍不注意,就變成直線而沒有了細微的變化。更難的是外撇的口沿,會很容易比杯壁更薄,顯得太過鋒利,使用起來并不舒適。于是,利坯的時候,又要故意讓口沿處稍有厚度。當然,口沿這一點點外撇,除了美觀上的考慮,也會降低變形的風險。這一切細微的功夫,既有設計上的精妙考量,又有賴于匠師精湛的技藝,還需要材料上的充分配合。
成形上的細節難以一一列舉,成形之后施釉的工序也有諸多難題。比如采用了臥足的工藝,因而外壁是直接延伸到底面,但底部接觸桌面的一圈,不能有釉,否則燒窯的時候,釉就會把杯子與下面的墊餅粘在一起,瓷器就廢了。如此一來,外壁既要完全被釉面覆蓋,而靠近底部的地方又不能有釉。這個界線,要拿捏得干凈利落,恰到好處。

“拉坯”又稱“走泥”。“走泥”最初被中國古人指稱陶瓷鈞窯的釉紋,有蚯蚓走泥紋之稱。
以上種種工藝細節的難度,還不是最終的挑戰,因為所有的努力,都要在窯火中接受考驗。高溫下種種風險,都需要通過間接的手段來控制,以至于很多時候難以完全控制。有時明明各方面準備都相當充分,天時地利人和也毫無偏差,可開窯的結果卻大大出乎意料。某些無法預知的問題不經意出現,徹底地改變了燒窯的結果,于是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天意。在當時可以預知的范圍內,燒造這樣的小杯也有種種困難。例如因為壁太薄就極易變形,除了成型上要下足功夫,還要對泥料配方進行調整,需要使泥性更硬,更有“骨力”。但一味地加強硬度,又會增加成形的難度,同時還要提高燒制時的溫度。而任何燒窯溫度的調整,都是巨大的挑戰。
大明成化斗彩纏枝蓮花高足杯。
以上種種,讓人們知曉,與我們的想象不同,大件器物并非比小件的器物更難燒造。一些偉大的成就,恰恰是在細節上見功夫。對于小件器物的燒造,細節自然會被放大,在大件器物上不顯眼的瑕疵可能就成為了嚴重的問題。如此一來,工藝上便有了更高的要求。新的要求,帶來更多技術上的挑戰,一旦克服,不僅能夠漂亮地完成皇帝的任務,對于整個行業而言,工藝水平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顯然,這一次,瓷藝的巨大發展仍系于皇帝的品味與需求。成化皇帝如此偏愛精致小巧的瓷器的原因,人們總是從皇帝本人的心理狀態來考察:成化皇帝自小受宮女萬氏照顧,對其極為依戀,登基之后,將她封為貴妃,寵愛有加。依照現代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他有深深的戀母情結。這樣的皇帝,喜愛溫柔小巧的物件,也說得通。另一方面的猜測聽起來也容易成立,還多了幾分八卦的色彩,更讓人們津津樂道:這些小件器物其實是萬貴妃的喜好,皇帝的旨意,不過是為討好自己心愛的女人。
無論何因,斗彩雞缸杯之類的小件瓷器在成化朝大放光彩都是不爭的事實;只是斗彩這種陶瓷史上如此重要的裝飾手法,后世卻很少提及,專業領域之外,更罕有人知曉,“斗彩”這個名稱的確立,至今也不過幾十年。
什么是斗彩
沈從文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一篇談論皮球紋的文章中提到斗彩時還寫作“豆彩”。有時候,學者還會寫作“逗彩”。甚至歷史上,斗彩雞缸杯一直也被稱為“青花五彩雞紋小杯”。

大明成化白釉磬口加康熙五彩過枝松鼠葡萄盤。北京保利2016秋季拍賣會,2070萬元成交。
關于“斗彩瓷”名稱的由來,歷史上有很多種說法。《陶雅》里說:“何以謂之豆彩,豆者豆青也。……雜以他色曰豆彩。”這顯然是道聽途說的猜測。而《飲流齋說瓷》中說:“何謂豆彩?蓋所繪花紋以豆青色為最多,占十分之五六,故曰豆彩也;或稱斗彩,謂花朵之攢簇有類斗爭;或稱逗彩,謂彩繪之駢連有同逗并,實則市人以音相呼,輾轉訛述。”這里綜合了各種傳聞,有的已經接近真相。人們對名稱的疑議,多為不了解工藝所致。從工藝的角度來看斗彩,情況就要簡單得多。
讓我們從雞缸杯的制作流程來一探斗彩瓷制作的究竟。
首先將瓷泥通過拉坯和利坯等工序做出杯子的形狀,這時候,叫素坯。素坯完成后,在它的表面以青花料進行彩繪,但彩繪主要是用線勾勒,類似于國畫中的白描。勾畫完成后,施透明釉,入窯高溫燒制。燒制完成后,在瓷器的表面,于勾線的輪廓內填彩。比如雞冠的部分,填上紅色,葉子的部分,填上綠色。填彩完成后,再低溫燒制一次。一件斗彩雞缸杯就完成了。
于是,斗的意思就漸漸浮現出來。地方方言中,斗有拼接的意思,比如古代制作家具,接榫頭就叫斗榫頭。而斗彩,就是把釉上的彩色與釉下的青花拼在一起,還要嚴絲合縫。這樣看來,斗彩只是一種裝飾手法。
在明代,釉上能“斗”的彩,只有五彩;但等到清代出現琺瑯彩、粉彩以至后來出現了新彩之后,也都可以把它們“斗”上去。不過后世總是把斗彩、粉彩、五彩、琺瑯彩相提并論,就容易讓人們誤以為斗彩是某種特殊的彩料,常常讓人摸不著頭腦。
作為一種特殊的裝飾手法,斗彩常常會運用非常多的顏色(雍正、乾隆朝的官窯更是將其推向了極致),而且這些顏色多數都用于小塊面和細節的填涂,因此,古人認為“斗彩”的“斗”有爭奇斗艷的意思。如果單獨觀看釉上的這些顏色,必定會讓人感覺瑣碎而雜亂,但整體的效果卻并非如此。因為所有的顏色都勾勒在青花線條的范圍之內,同一色系的色彩會更為協調,而強烈的對比色又會因為青花的約束而變得柔和。不過斗彩之中,有時又只“斗”一種色彩,這時候,因為青花,又會使得單一的色彩并不顯得單調。因而,在斗彩之中,青花扮演著某種特殊的角色,類似于黑色或白色,起到調和的作用。
斗彩雖然僅僅是一種裝飾手法,但在彩繪瓷的歷史上卻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青花的繪制與五彩的彩繪完全屬于兩個不同的工序,此前也沿著不同的道路各自發展。而此時,兩種工藝融合在一起,裝飾風格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更為重要的是,釉上的彩繪,借由青花的配合,地位得以大大提升。畢竟青花瓷此時正如日中天,而釉上的彩繪卻很少受到重視。但這一次的閃亮登場,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甚至在兩百多年之后,搶去了青花瓷的風頭。
不過,把青花與釉上的色彩相結合方法很多,用青花勾線而在線內填彩其實是極為特殊的一種,如此特殊的裝飾方法卻成為主流,頗不尋常。
分水與分工
制瓷工藝的發展,從來不是某時某地某人靈感乍現的神來之筆,而是制瓷工匠們長期的勞作與積累,是面對新需求時的探索與創新,是在艱苦努力后的一點點運氣。斗彩瓷產生的過程,它所經歷的困難、挑戰、失敗以及一步一步邁向可能預先并不知曉的成功,完全無法重現。我們只能從傳世的器物和工藝發展的邏輯中做一些猜測。
青花瓷在成化朝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不但在成形工藝上達到了新的高度,青花的彩繪也有了新的發展。
讓我們來看一件成化朝的青花瓷器。如果我們將其與永宣青花的繪制方法對比一下,就會發現其間的差異:除了色調上發生的顯著變化(永宣青花所使用的蘇麻離青已然用盡,此時青花瓷使用的是今天隸屬于景德鎮市的樂平縣所產的青料,這種青料清晰穩定,但色調清淡,與永宣青花大異其趣),手法上也有了顯著差別。早期青花彩繪,勾線與蘊染遵循同樣的手法,因此全部繪畫都由一位匠人獨立完成,工序上沒有明確的區分。隨著青花瓷在陶瓷市場上高歌猛進,不但大受帝王的喜愛,在民間也極受歡迎,需求大增,產量隨之增長,產量的擴大,客觀上要求分工的進一步細化。
于是,在成化時期,青花瓷的繪制出現了一種后來被稱為“分水”的技法。分水的具體做法,是用茶水混合青花料,調和成不同的濃度,再用一種叫“雞頭筆”的大筆,飽蘸料水,貼近坯體表面(通常并不接觸),料水流出,以筆尖引導料水填滿勾畫的線條區域。與永宣青花的堆垛填涂不同,分水法用大筆飽蘸青花料,以料水的流動填滿塊面,不但工序上獨立出來,所用的畫筆也都完全不同。
青花瓷的繪制,于此分成了兩道相互獨立的工藝:一是勾線,二是分水。用國畫做個粗略的類比:前者是白描,后者則是暈染。前者為線,后者為面。事實上,后來勾線與分水徹底成為兩道完全獨立的工種,而勾線又進一步地細分,畫人物、畫山水、畫花鳥都各自分離。
由此,斗彩的出現似乎才更容易理解。因為細化了分工,匠人們或許忽然意識到,似乎只是勾線也可能有不錯的效果,于是省去分水的部分,勾線之后就直接入窯燒制。的確,歷史上也有這樣一路產品,就叫“淡描”青花。不過顯然并不特別受歡迎,燒造得不多,傳世更少,很少有人意識到它的存在。淡描的青花如果不受歡迎,再要分水來補救已經沒有可能,但另一種方法自然產生,就是用釉上彩來代替分水。工藝上完全順理成章。我們還可以有其他的猜測,但斗彩的出現與分工的細化,無疑有必然的關聯。
在此,我們得以從這樣一個細節,看到瓷業發展的大趨勢。有時候我們很難一一分辨是分工的細化導致了瓷業的發展,還是瓷業的發展加速了分工的細化,但毫無疑問,正是這一進程,把景德鎮的制瓷業推向了一個又一個新的高峰,以至于五百多年前燒造的一只小酒杯,今天看來,也令人驚嘆不已。產生這一杰作的工藝體系,發展到今天最先進的工業化陶瓷生產流程,非但沒有脫離數百年前景德鎮構建的框架,某些方面細化的程度恐怕還有不及。
小小的雞缸杯,標志著陶瓷史已然又跨入一個新的階段。不過或許在當時的人看來,這一步的意義還并不顯著。恰好官方文件的一個小細節,成為這段歷史的一個清晰注腳。成化皇帝繼位后發布了一道圣旨:“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派內官在彼地燒造瓷器,詔書到日,除已燒造完成者悉數起解,未完者皆停工。”
這道詔書令景德鎮與龍泉兩地的官窯瓷器停止燒造,停燒的原因不得而知。不過其中透露出一條重要的信息,即成化皇帝繼位之前,除景德鎮外,龍泉仍然承擔著為皇帝燒造瓷器的部分任務。不過很快皇帝又下旨恢復瓷器燒造,但在承擔任務的地區名單上,只剩下了景德鎮。這一細微的變化,在歷史上幾乎不被人察覺。不過,它卻是陶瓷史上一道巨大的分水嶺。自此,景德鎮在窯業一統江湖。

湖北兵工廠,1894年在中國湖北漢陽縣大別山建成。初名“湖北槍炮廠”,該兵工廠建立初期遭火災被摧毀大量設備建筑,1895年重建后開始制造88型步槍(仿德國Gewehr 88設計制造)以及各種小型武器。1908年,它更名為“漢陽兵工廠”。

張之洞,中國晚清官員,1889年任湖廣總督興辦洋務,1890年到1906年他籌措監修京漢鐵路。1890年起,張之洞在武漢興辦近代工業,湖北紡紗局,織布局,繅絲局,鋼藥廠,槍炮廠等相繼建立,奠定了武漢地區工業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