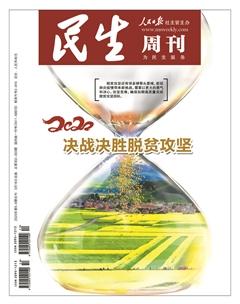脫貧攻堅目標不動搖
顧仲陽 常欽 鄭智維
截至2月底,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已有601個宣布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0.6%,累計減少貧困人口9348萬人。
過去的幾年間,我國建立了五級書記抓脫貧攻堅體制,實施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
在此過程中,各地探索創新了很多扶貧方式,也為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提供了可借鑒可復制的經驗。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決戰之年。受訪專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會帶來新挑戰,但目標能如期完成。
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時強調,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這是一場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緊繃這根弦,不能停頓、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影響最大的是外出就業
近年來,外出打工的工資性收入一直是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
“2018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有42.0%來源于工資性收入。在一些缺乏本地產業支撐的貧困地區,這一比例更高。”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說。
魏后凱分析認為,這次疫情對脫貧攻堅產生了一定的短期、局部性影響,加大了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的難度。在疫情帶來的影響中,影響最大的是貧困和低收入家庭人員外出就業。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吸納農民工就業較多的服務行業首當其沖。城鄉市場消費低迷,大批服務門店歇業,很多企業、工地暫緩開工復工,加上交通管制帶來的出行不便,這次疫情對農民工返崗和外出就業產生了很大影響。
“企業延期復工和各地采取的管控措施等會影響農民工返城務工,減少其工資性收入;疫情對鄉村休閑旅游、觀光采摘業和養殖業等影響大,會影響到農民的經營性收入。”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副秘書長唐麗霞分析說。
在她看來,疫情可能會造成返貧和新增貧困人口。
除直接影響群眾收入外,疫情期間,各地工作重點都在疫情防控上,扶貧工作的安排也會受到影響。尤其是農村自身衛生防疫能力薄弱,疫情防控措施更加嚴格,勢必會影響到農民生計恢復。
此外,武漢等地“封城”之后,各地都采取了封閉社區、封村、封路等管制措施,導致生產物流停滯,對農產品銷售、養殖業飼料供應、種業等產生了較大影響。

廣西馬山縣,扶貧干部在貧困戶家中同勞動,交談。圖/李德勝
前段時間,由于封路飼料運不進來,湖北存欄的4億只家禽、1692萬頭生豬面臨“斷糧”的危險。一些貧困地區的農產品運不出來,缺乏銷路。
“在疫情發生之后,政府既要抓疫情防控,又要抓脫貧攻堅。”魏后凱說,在政府配置資源能力既定的情況下,投向脫貧攻堅的精力、人才、物力和財力必然會有所減弱。
不會改變脫貧攻堅整體態勢
近年來,我國每年減少的農村貧困人口都在1100萬人以上。
2016至2019年間,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了5.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28個百分點。在832個貧困縣中,2016—2018年實現摘帽436個,2019年又實現摘帽340個左右。
即便是脫貧難度最大的“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其脫貧攻堅也取得了重大進展。2019年,“三區三州”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由上年的172萬減少到43萬,貧困發生率由8.2%下降到2%。
即便目前因為疫情對鄉村旅游發展有沖擊,但這種影響是短暫的,村莊綜合發展能力的提升對農民減貧增收的效果是長期的。
“目前脫貧攻堅已經進入到最后的收官階段,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全面打好脫貧攻堅的收官之戰。”魏后凱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脫貧攻堅的難度,但不會影響脫貧攻堅目標的如期實現。
從2016年開始,我國連續4年實現了中央財政扶貧資金每年增加200億元的力度,2019年我國中央財政安排扶貧資金1261億元,2020年中央財政扶貧投入力度不減。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作為今年農業農村工作兩大重點任務,所有舉措都是圍繞這兩大任務展開。這為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提供了政策保障。
“過去的幾年間,我國財政扶貧資金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在唐麗霞看來,雖然疫情會對扶貧工作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基本不會改變脫貧攻堅的整體態勢。
通過基礎設施改善、旅游扶貧開發等措施,我國有近萬個貧困村從根本上改善了村莊的綜合發展能力。即便目前因為疫情對鄉村旅游發展有沖擊,但這種影響是短暫的,村莊綜合發展能力的提升對農民減貧增收的效果是長期的。
據唐麗霞觀察,我國貧困人口中有20%左右是老年人,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以及一些地方實施的資產收益性扶貧項目也為這些貧困人口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
脫貧攻堅以來,我國扶貧工作的一大轉變是:從過去政府主導變成了不同類型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從專業部門扶貧轉變為多部門共同扶貧等,扶貧力量得以加強。

蘋果小鎮,豐收的喜悅。圖/古船
此外,我國近年來發展成立了220多萬家農民專業合作社。一半農民已經加入合作社,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農戶抵抗風險的能力。
“目前,我國的扶貧方式多樣,針對不同致貧原因有不同的扶持方式,并且采取了打組合拳的方式,每個貧困戶獲得的扶持是多樣化和系統性的,將貧困戶的增收、改善生活質量和能力提升綜合考慮。”唐麗霞說。
中國特色減貧道路
通過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我國凝聚全黨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扶貧開發,形成了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支撐、共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中國特色減貧道路是我國脫貧攻堅戰能夠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重要法寶,也是當前對沖疫情不利影響的壓艙石。”魏后凱說。
擁有諸多明顯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脫貧攻堅提供了保障。比如,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制度優勢就得到了充分展現。
在精準扶貧階段,我國有了很多創新的并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扶貧方式:以解決貧困戶就業問題為目標的設在鄉、村的加工車間的扶貧車間,以解決貧困戶農產品銷售為目標的消費扶貧,以利用貧困村和貧困戶閑置土地和其他設施增收的光伏扶貧……
這些扶貧方式將繼續發揮作用,確保農戶收入持續增加。
談及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二者的統籌協調,魏后凱建議,在加強疫情防控的同時,各地要全面搞好復工復產工作,擴大市場需求,增加就業崗位,并采取有效措施穩定農民工就業,尤其要支持貧困和低收入群體、貧困地區外出農民工返崗就業。
一方面,要抓好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發展。確保農產品運輸和銷售渠道暢通,保障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努力將疫情對農業農村的影響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要防止已脫貧的人口返貧和新發生貧困人口,全面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要加大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力度,大力發展農村富民產業,抓好扶貧搬遷移民的安穩致富工作。
談及當下的工作重點,唐麗霞提醒,除了加大農村公共衛生和防疫知識的宣傳和培訓以降低農村疫情傳播的風險外,目前還要盡量減少疫情導致的直接損失。
“例如,通過電商平臺、農超對接等方式對農戶的農產品進行采購,支持冷鏈保鮮基礎設施建設延長農產品儲存周期等。”她說。
針對影響群眾收入較大的就業問題,唐麗霞建議:
一方面各地要積極了解因疫情影響不能及時返城就業農民的基本信息和當地復工企業勞動力需要信息,做好二者的對接服務。
另一方面,要發揮村兩委、扶貧工作隊及第一書記等基層扶貧隊伍的組織優勢擴大本地就業,可將一些扶貧的小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委托給村集體來實施,采取以工代賑和公益性崗位等方式來增加農戶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