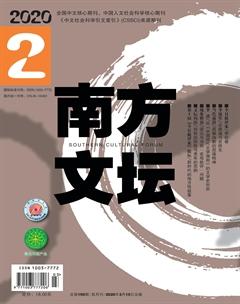鄉紳文化·性·政治博弈與鄉村秩序的書寫
江臘生 趙晶晶
討論當代文學七十年的話題,一直無法繞開小說《白鹿原》的文學史影響。它的出版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無論在宗親社會與鄉紳文化的回望與挽歌中,展示鄉村歷史變遷;還是從鄉村性史的流動,揭示鄉村社會權力的另一種脈動,或者立足于鄉村社會形態的更迭,審視政治革命斗爭與鄉村社會秩序的關系。這些方面構成了此后當代文學鄉土創作的重要方向引領。作家陳忠實站在文學尋根的脊背上,右手執魔幻現實主義之劍,左手執新歷史主義的盾牌,在文化審視和歷史把握的整合中成為當代文壇創作的一座峰巒。此后,莫言的《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賈平凹的《古爐》《老生》《山本》,閻連科的《受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當代小說創作沿著這條軌道繼續前行。《白鹿原》的文學史價值不可忽視。
從古老中國到現代中國,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動。變與不變,在鄉村秩序與現代中國政治革命之間形成了巨大張力。也就是說,一次次激越的現代中國革命運動中,往往以相對穩固的鄉村社會秩序運行而融入民族的日常生活肌理。陳忠實在《白鹿原》卷首題詞為:“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按照作家自述道,“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說太遠,在我之前的兩代或三代人,在這個原上以怎樣的社會秩序生活著?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經歷過怎樣的生活變化中的喜悅和災難”①。“秘”在于鄉村社會秩序如何與政治話語、鄉村習俗、宗族力量相互結合,以何種方式存在于鄉土中國。“究其根本,它的基石乃是對中國農村家族史的研究;它是枝葉繁盛的大樹,那根系扎在宗法文化的深土層中。”②小說以宗族村落為敘述基點,敏銳地把握到鄉紳社會結構的分層,集中在白嘉軒、朱先生、鹿子霖等鄉紳的日常活動、言行舉止,比較全面、生動地展現了鄉土中國的社會形態、權力結構和運作機制,揭示一個鄉土中國相對靜肅的文化世界。同時,鄉土中國還有充滿活力的一面。男男女女身上激情流淌的力比多,集中體現了鄉村秩序下的欲望存在,考量著人性命運與倫理秩序之間的沖突。在這一動一靜的兩個文化世界中,“翻鏊子”似的革命運動與斗爭,一次次動搖了鄉村社會的政治格局,卻難以改變鄉村秩序的超穩定一面。可見,探尋小說“秘”之所在,揭示鄉村秩序和民族生存的密碼,觸摸到民族文化性格中超穩定的一面,應該是小說《白鹿原》的文學史努力之一。因此,本論文以鄉村社會秩序的運行為核心,考察其中的宗親關系和鄉紳文化、鄉村性史與欲望流動、政治革命和鄉村權力更迭三個維度,探討其如何將魔幻元素、傳統鄉紳文化、鄉村秘史、政治話語融入鄉村世界的社會結構當中,支配著當代作家創作的用力所在。
一、鄉紳文化的復雜構成與鄉村秩序的運行
現代中國的風云變幻,并沒有在一次次政治話語的更迭中打破農村社會的生活秩序與文化結構。這種超穩定的文化生活秩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鄉村的精英,即鄉紳的維持與傳承,并以一系列民間倫理、情感結構、文化秩序等方式存在。鄉村社會里,鄉紳本質上是引領鄉村習俗的核心人物。明末清初顏茂猷認為:“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后進,其為功化比士人百倍。”③費孝通先生所說:“一個農民從生到死,都得與紳士發生關系。比如在滿月酒、結婚酒以及喪事酒中,都得有紳士在場,他們指揮著儀式的進行,要如此才不致發生失禮和錯亂。在吃飯的時候,他們坐著首席,得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④在傳統的鄉村世界,鄉紳集教化、祭祀、訴訟等為一體,化入到鄉民日常生活每一個瑣碎經驗中。這些鄉紳往往憑借在鄉村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層面的優勢,成為鄉村秩序維護與傳承的主體。實際上,鄉村社會結構中鄉紳這一群體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過渡中,呈現出文化的復雜性。
對于朱先生、白嘉軒等民間鄉紳力量,很多研究者從儒家文化入手,將其視為文化守望的符號,也是對所謂革命現代性質疑和反思的依托。按照這個邏輯出發,鄉紳文化延續和承載了20世紀80年代文化尋根的追求,構成了當代文學文化厚重感的一面。實際上,鄉紳階層的復雜性正是鄉村社會秩序運行的前提。“白鹿原上,最堅實的基礎不是別的,而是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存留下來的那一套倫理規范,幾千年文化積淀形成的那一種文化心理,幾千年相沿流傳的那一番鄉俗風情。”⑤朱先生、白嘉軒、鹿子霖等身上承載著儒家文化的不同側面,通過一系列禮俗文化與宗族制度的實施與維持,共同完成鄉土社會文化秩序的建構。
鄉村秩序的確立,離不開政治系統與民間系統的共同支撐。朱先生在白鹿原上的傳奇與神秘,轉化為一種文化優勢,在贏得人們的服膺和敬重中溝通了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他自幼聰明過人,十六歲應縣考得中秀才,廿二歲赴省試又中頭名文舉人。”但其儒家的“仁愛”哲學,又建立在悠久厚重的土地上。有關朱先生的出場,作者這樣描述:“他一身布衣,青衫青褲青袍黑鞋布襪,皆出自賢妻的雙手,棉花自種自紡自織自裁自縫,從頭到腳不見一根洋線一縷絲綢。”這種既崇尚自然質樸又彪炳傳統守舊的衣著裝扮,顯然隱喻了他的仁義境界來自土地,這與朱先生的經典名言“房要小,地要少,養個黃牛慢慢搞”。達成一致。在此基礎上,作家又賦予了朱先生一種類似民間神話的仙氣。他能預測天氣,預知來年何種作物豐收,甚至算卦幫農民尋找丟失的老黃牛。這些類似于知曉天機的神秘話語,浸透在鄉民的日常生活當中,為朱先生在白鹿原上推行仁義秩序提供了一種文化威信。同時,“每有新縣令到任,無一不登白鹿書院拜謁姐夫朱先生”。于是,朱先生憑借其文化威信和政治平臺,擁有了建構白鹿原上鄉村秩序的文化領導權。
在具體的鄉間文化建構上,朱先生親自動手推倒庵內的四座神像,改造為白鹿書院,進而成為儒家仁義文化的弘揚之所。然后主持白鹿書院,教書育人,既擁有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權,又從人格上點化如黑娃之流,從而在鄉間社會發揮著文化培育和引導的作用。辛亥革命發生之時亂象叢生,社會秩序混亂。他訂立《鄉約》,內容涉及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諸多方面,將民間儒家文化規范與鄉民生活整合成民風民俗代代相傳,形成了白鹿原上日常生活的秩序系統。作家指出,“緩慢的歷史演進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鄉約族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個鄉社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族,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這一方地域上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⑥。這種文化心理結構,正是白鹿原上超穩定的文化生活秩序的基礎。社會事務方面,朱先生在白鹿原上罌粟花開的時候,親自扶犁下地,毀苗禁種鴉片。國民革命時期,冒著生命危險,以其完美的人格魅力,只身勸止方升二十萬大軍的全線進攻,避免了三秦地區的生靈涂炭。饑饉年月,他勤廉公正為災民發放舍飯,與饑民共甘苦。日寇進犯中條山,逼近西安城,他義結八位老先生欲投筆從戎奔赴前線。朱先生的這些奇行、奇言、奇事,體現了儒家文化超越政治、黨派、時空,而以一種文化權威的方式進入民間的生活狀態。也就是說,朱先生的身上,體現了古老中國的鄉村秩序之文化根本。他是一個文化符號,卻深刻地影響著古老中國的日常秩序和價值倫理建構。
從古老中國走來的鄉村秩序,需要一個群體來加以守護與延續。白嘉軒作為族長,他奉行朱先生的文化理念,卻比朱先生更注重沉入世俗的生活當中。白嘉軒本質上是一個傳統農民,耕讀傳家,發家致富,光宗耀祖。他率先在民風淳厚的白鹿原上種植鴉片換取銀圓,作為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改造老屋,門樓上刻寫“耕讀傳家”,以訓后世。偶然發現鹿家的土地上長出白鹿形狀的仙草,便設計以好地換劣地來保證白家的興旺。面對農事,耕棉田、翻稻地、鍘谷草等農活,他都與長工鹿三一起搭手干著。靠著自己的艱辛勞動,白嘉軒沒有卷入一次次的“翻鏊子”運動,帶著家族從亂世中走來。如果說朱先生身上體現的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宏略,那么在白嘉軒的身上,更多地體現了民間儒家文化中“修身齊家”最世俗一面。
同時,白嘉軒作為白鹿兩家的族長,是白鹿原上具有主導性力量的鄉紳代表。如果說朱先生在鄉村社會引領著鄉民們的文化精神,那么,白嘉軒則是日常生活秩序的守護者。一方面,為了實現鄉村社會的正常運轉,白嘉軒是鄉村社會的代言人與保護人。承擔宗族的責任是白嘉軒聲望的來源,立身的基礎。面對縣府征收的名目繁多的賦稅,他發起“交農事件”,又上下周旋,救出交農事件中被抓的鹿三、徐先生等人,保住白鹿原的一隅平安。在農民運動失敗之后,田福賢回到鎮上瘋狂報復,白嘉軒提出代族人受過。即使對手鹿子霖被抓進牢后,白嘉軒也上下斡旋,出面搭救。因此,白嘉軒以德報怨的大度與寬容不僅僅是一種注重個人修身的儒家文化,重要的是與他作為“族長”的社會身份不可分割。
鄉紳是鄉村公共事務的組織者或提供者。民事糾紛調解、修筑公共工程、教化鄉民、整肅民風和慈善救濟等都是由鄉紳主持或組織。白嘉軒聯手朱先生,立鄉約、辦學堂。當黑娃帶著田小娥回到村里,白嘉軒阻止黑娃入祠堂成親。他嚴施酷刑,整治違反族規者,不僅煙鬼、賭徒、淫亂者要受嚴懲,就連他的愛子白孝文觸犯戒律,也毫不手軟。于是宗族生活秩序在白鹿原上確立。“從此偷雞摸狗摘桃掐瓜之類的事頓然絕跡,摸牌九搓麻將抹花花擲骰子等賭博營生全踢了攤子,打架斗毆扯街罵巷的爭斗事件不再發生,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拘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作為族長這樣一個鄉村最為基層的鄉紳,他沒有將自己完全交付給皇權或黨派政治,而是以延續千年的鄉紳文化維持和保護著鄉村的秩序。所以小說的前半部分,浸透著鄉村文化的詩意,在一種挽歌情調中回望傳統鄉紳與鄉村秩序的文化價值。后半部分,頻繁的政治運動,使鄉村秩序無法延續,白嘉軒的家族地位雖然在白孝文手中沒有敗落,但這種鄉村文化秩序已經終結了。
因此,白嘉軒一方面極力以其仁義文化、鄉約制度來維持和統治白鹿原這個鄉土世界,另一方面又以民間最為原始的非仁義的實用生活智慧,來實施白鹿原上的文化秩序。實際上,小說中仁義文化中非仁義的一面正是儒家文化中現世主義的主導力量,通常體現在民間諸多日常細節之中,諸如白嘉軒心懷鬼胎與鹿子霖換地,種鴉片,田小娥之死等,而仁義的一面則似乎是儒家文化已經正如白鹿神話一樣,成為一種遠離現實的想象性虛構。仁義與非仁義正是構成鄉村社會秩序對于民眾的復雜構成,真實而歷史地回應了以往的文學創作中地主階級虛偽性的文學塑造。
當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之際,鄉村社會秩序自然會出現分化和重組。鹿子霖屬于鄉紳文化中一個政治投機者。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由于舊有的政權機制被打破,一些鄉紳不再倚靠傳統功名和文化身份來維持鄉村文化秩序,而是以“革命”的名義攫取鄉村權力。鹿子霖為了走出鹿家沒有文化這一魔咒,辛亥革命之后搖身一變加入到“縣政”這一軌道上。這類“土豪劣紳一般都兼作收捐人、廟宇管事、公有土地管事、公有糧倉管事……說明了行政公職對土豪劣紳有多么大的好處”⑦。鹿子霖擔任了第一保障所鄉約后,第一件政務就是“傳達縣府史維華縣長的命令,要對本縣的土地和人口進行一次徹底清查,先由保障所逐村逐戶核查造冊,再由白鹿倉匯總之后統一到縣府加蓋印章,一畝一章,一丁一章,按土地畝數和人頭收繳印章稅”。繁重的捐稅,激起了白鹿原上一場“風攪雪”。隨后的農協運動,國民黨的鎮壓清算,鹿子霖幾度浮沉,將權力作為自己的法寶,跟隨田福賢作惡鄉里。他利用職務之便,誘使鄉里多個女人上床,甚至有了眾多私生子。白孝文當上縣長后,他徹底失去了權力的庇護,最后在柴房里瘋癲而死。顯然,鹿子霖和白嘉軒兩人迥異的命運寫照,體現了作家的價值立場始終站在民間文化的一面,而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甚至對立。文本將這一價值取向建立在傳統社會的“善惡相因”“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基礎上,潛在地完成了對鄉紳階層中“惡”的批判,從而接通了以往的革命歷史敘事傳統。
本質上,《白鹿原》第一次走出了將地主或鄉紳臉譜化和一體化的話語定勢,而是通過朱先生、白嘉軒、鹿子霖三個鄉紳結構了現代中國鄉村文化的復雜性。這一處理打破了以往二元對立的思維,而將鄉紳階層作為鄉村文化存在的復雜本身。其中既有儒家文化的浸染,又有神秘氛圍的支撐;既有政治權力的左右,還有世俗智慧的滲透。可以說《白鹿原》開啟了當代文學創作中復調性的鄉紳階層書寫的先河。
二、性史的流動與鄉村秩序
性欲的沖動是鄉村秩序下的暗流涌動。當代文學從莫言的《紅高粱》開始,性成為民間話語對主流話語構成解構的一種原始力量。賈平凹的《廢都》中一系列性的描寫,“有一種反諷效果,它拓展了意義空間,指涉著禁制、躲閃,也指涉著禁制、躲閃的歷史,它與主人公的經驗有一種緊張關系。如果去掉,這部小說就少了一重意思”⑧。這些性的書寫往往有一種話語反抗的沖動,卻缺少了性欲與生活秩序之間常態書寫。小說《白鹿原》中,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存的性欲沖動既是白嘉軒、鹿子霖等男性確立文化秩序,競爭宗族權力的體現,也是田小娥、鹿冷氏等女性在強大的文化秩序下掙扎、抗爭、屈服的體現。性欲的沖動,實際上宣示了鄉村社會道貌岸然的宗族秩序下還有一個真實的隱秘世界及其內在激烈的沖突。
在小說中,無論是白嘉軒還是鹿子霖身上,都有性渲染的地方。這兩人的性欲世界是他們爭奪鄉村宗族權力,掌控鄉村秩序的戰場。“白嘉軒后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有研究指出,“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這位人格神強大的雄性的能量,暗喻他的出現如何不同凡響”⑨。但從小說情節的布局和白嘉軒的性格發展邏輯來看,他的“引以為豪壯”不是炫耀他性能力的旺盛,而是他百折不撓地生下兒子,保證族長權力的延續。相反,旺盛的情欲卻造成他先前無子的災難。因此,一旦有了子嗣,小說便將筆墨集中在他對鄉村秩序的維護和鄉村權力的掌控,不再書寫白嘉軒的力比多。白嘉軒很快從一個力比多的旺盛者變成了一個老態的族長,其性生活突然一片空白。他不但沒有力比多的激情,反而進一步控制田小娥和白孝文等人的欲望用以維護鄉村秩序,確立其鄉村權力。在他身上,自然態的力比多轉化為一個社會態的權力欲望,從一個欲望神轉化為一個人格神,從而與儒家文化作了倫理上的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