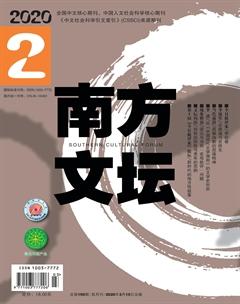通過(guò)碎片來(lái)重建整體性的可能
盡管文學(xué)史的出現(xiàn)與民族國(guó)家觀念的興起密切相關(guān),但是,在海外學(xué)界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從來(lái)都不是熱門(mén)選項(xiàng),尤其是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更是如此。雖然海外也有一些具有“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形態(tài)的研究著作,甚至也有夏志清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史》、顧彬的《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史》等,但是與國(guó)內(nèi)汗牛充棟的書(shū)寫(xiě)體量相比,海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書(shū)寫(xiě),實(shí)在乏善可陳。饒有趣味的是,海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發(fā)生,又以夏志清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史》(以下簡(jiǎn)稱《小說(shuō)史》)為起點(diǎn)和標(biāo)志。而這本《小說(shuō)史》之所以成為發(fā)軔經(jīng)典,大抵在于它劃定疆域、標(biāo)識(shí)特征、明確標(biāo)準(zhǔn),既有時(shí)間的起落,又有敘事的線索,具有鮮明的史觀,不至于讓初識(shí)者迷失于個(gè)別的作家作品或文學(xué)現(xiàn)象,而無(wú)法建立起對(duì)“現(xiàn)代”的整體認(rèn)知。與此同時(shí),夏志清秉承西方人文主義立場(chǎng),以世界文學(xué)的視野,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作家作品展開(kāi)審美性的細(xì)讀與評(píng)判,從而獨(dú)樹(shù)一幟,卓然而成“夏氏范式”(王德威語(yǔ))。半個(gè)多世紀(jì)之后,回顧夏志清《小說(shuō)史》所做出的種種品鑒和論斷,我們必須承認(rèn),這樣的文學(xué)史不以溢美為能事,而更注重辨析“美”的形態(tài)與可能。學(xué)界對(duì)該書(shū)的思辨,往往圍繞夏志清的標(biāo)準(zhǔn)或立場(chǎng)來(lái)展開(kāi),反而忽略了他所做出的不同評(píng)價(jià)如何形成有趣的對(duì)話,如何可以在同一個(gè)歷史場(chǎng)域中并存。比如,既然《小說(shuō)史》標(biāo)榜對(duì)“優(yōu)美作品的發(fā)現(xiàn)”,為什么那些“不優(yōu)美的作品”也同時(shí)與之并存?這些所謂的“不優(yōu)美”與“優(yōu)美”構(gòu)成怎樣的關(guān)系?或者說(shuō)理解“優(yōu)美”必須以所謂的“不優(yōu)美”為對(duì)照,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本來(lái)就是以拉鋸的方式來(lái)加以理解和定位?這是否意味著,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從一開(kāi)始就是一個(gè)問(wèn)題,而不是一種事實(shí)?
夏志清《小說(shuō)史》之后,海外具有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典型形態(tài)的著作難得一見(jiàn)。最近幾年,鄧騰克(Kirk Denton)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張英進(jìn)主編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 2016)、羅鵬(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編的《牛津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手冊(cè)》(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王德威主編的哈佛版《新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以及顧明棟主編的《盧特利奇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手冊(cè)》(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2018)橫空出世,分別展示出他們對(duì)文學(xué)史的全新理解。這幾本文學(xué)史著作,無(wú)論是以“文學(xué)史”命名,還是以“指南”或“手冊(cè)”命名,其實(shí)都沒(méi)有傳統(tǒng)中國(guó)文學(xué)史的典型形態(tài)。這樣的非典型形態(tài),表明主編者們嘗試以更靈活、更多元也更輕松的方式來(lái)展開(kāi)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書(shū)寫(xiě),也從另一個(gè)角度回應(yīng)了后現(xiàn)代思潮下,“歷史重寫(xiě)”的可能性,呈現(xiàn)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嶄新風(fēng)貌。但是,我們必須承認(rèn),“文學(xué)史”無(wú)論其形態(tài)如何,都必須在嚴(yán)謹(jǐn)?shù)男问胶妥杂傻牧⒁庵g拔河。在整體性消解之后,我們?nèi)绾纬尸F(xiàn)具有一定邏輯關(guān)聯(lián)的文學(xué)史敘事,而不只是給出一些吉光片羽,仍是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者的基本使命。本文嘗試以張英進(jìn)主編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指南》(以下簡(jiǎn)稱《指南》)為例,對(duì)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的形態(tài)問(wèn)題做出探索,希望既揭示該書(shū)的特色,也借此追蹤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的新動(dòng)向。
一
《指南》的篇幅五百七十余頁(yè),三十二位作者圍繞“歷史與地理”“文類(lèi)與類(lèi)型”“文化與媒體”“議題與論爭(zhēng)”四個(gè)板塊進(jìn)行論述。粗略來(lái)看,“歷史”不過(guò)是《指南》所要處理的話題之一,并不獨(dú)立構(gòu)成論述的結(jié)構(gòu)或線索。張英進(jìn)本人也坦言,不準(zhǔn)備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涉及的諸種運(yùn)動(dòng)、流派、文類(lèi)、作者、文本、風(fēng)格及主題進(jìn)行綜合性的概觀,使其呈現(xiàn)為通史式的或作家作品導(dǎo)讀式的著述。顯然,“文學(xué)史”所面對(duì)的不只是一段連貫的歷史,也同時(shí)包含其他方面各種復(fù)雜而多元的內(nèi)容。在這個(gè)意義上,《指南》幫我們辨析了“文學(xué)史”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即其對(duì)象或范疇的問(wèn)題。張英進(jìn)指出,“文學(xué)史”其實(shí)是一個(gè)所謂的“空間”或者巴赫金(M.M. Bahtin)意義上的“時(shí)空體”。此“空間”既包含地理上的跨境、跨國(guó),也同時(shí)承載不同議題和觀念之間的拉鋸,充滿運(yùn)動(dòng)性。人文地理學(xué)者曾經(jīng)仔細(xì)辨析地方與空間的不同。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兩者既緊密相連,但也有明確區(qū)別。相比起“地方”(place)所代表的熟悉感,“空間”(space)不僅投射更大的領(lǐng)域意識(shí),而且也表征一種陌生和不確定的感覺(jué)。我們可以用一系列充滿矛盾的概念來(lái)描述它們,比如,它既是自由的,但同時(shí)也可以是充滿威脅和限制的①。之所以視文學(xué)史為“空間”,一方面既可以指明“文學(xué)史”寫(xiě)作不是一種四平八穩(wěn)的知識(shí)組裝,而是一種探索知識(shí)講述的新路徑,不斷給我們帶來(lái)陌生感;另一方面,這種探索本身不是隨性而為的,它受到各種認(rèn)知經(jīng)驗(yàn)的限制,比如它仍需回應(yīng)時(shí)間的問(wèn)題,總與既往的文學(xué)史觀念發(fā)生牽連。
以第一部分“歷史與地理”為例,張英進(jìn)的編排有意突出一種不連貫的敘事視角。即使從時(shí)間的編排來(lái)看,由陳曉明執(zhí)筆的第五章“激進(jìn)現(xiàn)代性驅(qū)動(dòng)下的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20世紀(jì)50年代至80年代”,就和陶東風(fēng)所撰寫(xiě)的第六章“新時(shí)期文學(xué)的三十年:從精英化到去精英化”存在重疊。前者著力說(shuō)明文學(xué)與政治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系,試圖幫助我們理解:即使在政治的變動(dòng)中,文學(xué)書(shū)寫(xiě)受到影響,但這種影響也從側(cè)面表明“中國(guó)現(xiàn)代性”的特色,并非一無(wú)是處。而后者顯然凸顯經(jīng)濟(jì)因素的介入如何使文學(xué)轉(zhuǎn)變成對(duì)文化事業(yè)的追求,各種流行現(xiàn)象怎樣驅(qū)使社會(huì)主義文學(xué)有了“后”的征兆,表現(xiàn)出一種因體制轉(zhuǎn)變而來(lái)的去精英化效應(yīng)。是否有可能糅合經(jīng)濟(jì)和政治,乃至更復(fù)雜的要素,對(duì)這段歷史進(jìn)行重排,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既然張英進(jìn)“放任”了這種重疊的出現(xiàn),是否表明即使是一種更綜合性的標(biāo)準(zhǔn),也很難對(duì)歷史做出連續(xù)、有效的切分。畢竟這種綜合性的考量體系,在不同的區(qū)段內(nèi),構(gòu)成的情況亦存在差異,隨時(shí)變動(dòng)。換句話說(shuō),標(biāo)準(zhǔn)本身也是變動(dòng)不居的。
這種敘事上的不連貫性,同樣表現(xiàn)在編者將歷史和地理并置這一點(diǎn)上。這種并置多少說(shuō)明我們沒(méi)辦法在歷史的進(jìn)程中有效地容納地理上的轉(zhuǎn)變,或者不同地理空間的差異,并不能形成一種時(shí)間上的有效貫通。在通常的文學(xué)史敘事中,港臺(tái)文學(xué)常被單獨(dú)討論,就是這種不連貫性的表現(xiàn)形態(tài)。顯然,與傳統(tǒng)文學(xué)史不同,張英進(jìn)邀請(qǐng)張誦圣進(jìn)一步說(shuō)明了造成這種不連貫性的原因,而不只是單獨(dú)地羅列出一個(gè)地區(qū)的創(chuàng)作實(shí)績(jī)。通過(guò)再現(xiàn)一個(gè)復(fù)雜的文學(xué)機(jī)制和一段復(fù)雜的歷史,張誦圣說(shuō)明了臺(tái)灣文學(xué)為什么無(wú)法被有效地整合進(jìn)大陸文學(xué)演變的進(jìn)程之中。差異化的在地經(jīng)驗(yàn)雖然讓海峽兩岸的文學(xué)無(wú)法同步前行,但是,她也著重指出其共同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之路乃是對(duì)語(yǔ)言現(xiàn)代性的尋求。臺(tái)灣文學(xué)仍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因由,不僅在于政治,也在于它們分享了近似的歷史驅(qū)動(dòng)力,即與近代東亞的殖民經(jīng)歷存在莫大關(guān)聯(lián)。這似乎也彌補(bǔ)了我們對(duì)時(shí)間和地理無(wú)法進(jìn)行同步觀察的遺憾。
二
如果說(shuō)歷史和地理的問(wèn)題,是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不得不面臨的難題,兩者的錯(cuò)位,本身就說(shuō)明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不可能是一個(gè)連貫的時(shí)間故事,那么《指南》的第二部分將“文類(lèi)與類(lèi)型”并置,就有點(diǎn)自我挑戰(zhàn)的意味了。畢竟我們可以通過(guò)所謂的“文類(lèi)史”來(lái)給出若干“走向清晰”的故事。即使這種走向不一定沿著線性進(jìn)化的方式展開(kāi),但實(shí)在沒(méi)有必要把類(lèi)型作為它的補(bǔ)充或并列的對(duì)象。小說(shuō)、詩(shī)歌、戲劇、散文之中,未嘗不可以列出翻譯文學(xué)、女性主義文學(xué)、通俗文學(xué)或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分支來(lái)加以討論。我們的問(wèn)題是,這些被單獨(dú)羅列的寫(xiě)作類(lèi)型寄寓了編者怎樣的用心?
誠(chéng)如張英進(jìn)所說(shuō),在上述四種文學(xué)類(lèi)型之外,其實(shí)還有更多的題材值得注意,比如自傳文學(xué)、兒童文學(xué)、報(bào)告文學(xué)、游記文學(xué)等。這些文學(xué)類(lèi)型的研究在西方也行之有年,相關(guān)成果不容忽視。僅以“報(bào)告文學(xué)”而言,弗吉尼亞大學(xué)羅福林(Charles A. Laughlin)教授的專著Chinese Reportage: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早在2002年就由杜克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是目前為止英語(yǔ)世界唯一一本有關(guān)報(bào)告文學(xué)的研究著述。透過(guò)這本著述,我們可以進(jìn)一步追問(wèn),報(bào)告文學(xué)真的只是散文書(shū)寫(xiě)的分支嗎?還是可以視為全新的文類(lèi),代表一種全新歷史經(jīng)驗(yàn)的美學(xué)形態(tài)?劉禾在《跨語(yǔ)際實(shí)踐》中,已經(jīng)指出四大文類(lèi)的說(shuō)法源自西方,日本作為中介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跨語(yǔ)際實(shí)踐代表了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歷史進(jìn)程中,不同的意識(shí)觀念和文學(xué)認(rèn)知的交流、切磋和紛爭(zhēng),背后甚至裹挾著國(guó)家利益和政治訴求②。換句話說(shuō),詩(shī)歌、小說(shuō)、散文、戲劇的分類(lèi),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國(guó)家間的對(duì)話甚至對(duì)立,它們的中國(guó)化過(guò)程,也代表了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主體的自我定位和抉擇。但問(wèn)題是,這個(gè)過(guò)程是否已經(jīng)終結(jié)?此后漫長(zhǎng)的文學(xué)實(shí)踐,有沒(méi)有可能對(duì)這種分類(lèi)提出挑戰(zhàn)?或者至少在其內(nèi)部發(fā)出異議和多音?
正是在這個(gè)完而未了的進(jìn)程中,我們認(rèn)為張英進(jìn)嘗試將“文類(lèi)和類(lèi)型”并立,代表了一種持續(xù)推進(jìn)文學(xué)跨語(yǔ)際實(shí)踐的努力,呈現(xiàn)了在新的語(yǔ)境里繼續(xù)發(fā)展文學(xué)文類(lèi)的思路。被挑選出來(lái)作為類(lèi)型代表的四種寫(xiě)作題材——翻譯文學(xué)、女性文學(xué)、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和通俗藝術(shù)——通常被視為文學(xué)的弱勢(shì)力量。它們?nèi)绾闻c代表主流與“不言自明”之權(quán)威的虛構(gòu)寫(xiě)作、男性文學(xué)、漢語(yǔ)文學(xué)和精英文學(xué)形成對(duì)話,本身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跨語(yǔ)際實(shí)踐。只是這個(gè)“語(yǔ)際”未必在國(guó)家和地區(qū)之間發(fā)生,而是在文學(xué)內(nèi)部展開(kāi)。以女性文學(xué)的定義而言,杜愛(ài)梅(Amy Dooling)似乎并不準(zhǔn)備將之完全地性別化,反而一再指出跨性別思考的可能,特別是在晚清的世代里,作者的身份并不能被完全確認(rèn),故事里的女性主義思考就無(wú)法簡(jiǎn)單地和具體的生理屬性相勾連。特別是顧及當(dāng)下酷兒政治流行的情況,這種“女性”定位更可以有她的權(quán)宜和機(jī)變。在此我們自然會(huì)想到周蕾在她的大著《婦女與中國(guó)現(xiàn)代性》里的論述,理解到“婦女”其實(shí)是一種特征和立場(chǎng),而不是本質(zhì),代表的是在給定的境遇里去發(fā)展抗議和變革的行動(dòng)及思考。③
在此意義上,“翻譯”不妨有了新的維度。它代表的不是一種寫(xiě)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或者轉(zhuǎn)述,而是一種發(fā)明,一種持續(xù)的意義推進(jìn)。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來(lái)世”點(diǎn)明其中的關(guān)鍵點(diǎn),但不妨繼續(xù)追蹤,這樣的“來(lái)世”面臨身份歸屬之際,又可以形成怎樣的張力?林紓所譯述的各國(guó)文學(xué),是中國(guó)文學(xué),還是外國(guó)文學(xué)?在何種意義上,我們視它為中國(guó)文學(xué),可以置入中國(guó)文學(xué)史?是以其傳統(tǒng)的表述風(fēng)格,用漢字來(lái)呈現(xiàn)的形態(tài),還是采用中國(guó)式的選擇立場(chǎng)和判斷?此外,翻譯與翻譯文學(xué)又和當(dāng)下流行的“世界文學(xué)”形成怎樣的對(duì)話關(guān)系?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視世界文學(xué)為在翻譯中受益的作品④,這種受益除了傳播層面上的表現(xiàn),怎么看待它被大幅刪削、修改,甚至被冒名當(dāng)作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shí)?文學(xué)史除了客觀地再現(xiàn)過(guò)去,有沒(méi)有可能向我們闡明這種“翻譯”所帶來(lái)的問(wèn)題,就如同它總試圖揭示文學(xué)的流變方向?
三
繼“文學(xué)與文類(lèi)”之后,《指南》再以“文化與媒體”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做出展示。在這一部分,我們不僅看到了其他的文學(xué)類(lèi)型,如都市文學(xué)、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而且也據(jù)此了解到文學(xué)如何與政治、語(yǔ)言、新興媒體和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發(fā)生交鋒的故事。我們?cè)僖淮巫⒁獾剑阅撤N單一的視角來(lái)講述中國(guó)文學(xué)史,永遠(yuǎn)有所遺漏,必須附加但書(shū)。這部分的討論,乍看之下是以外部研究的方式來(lái)補(bǔ)充完善前兩個(gè)部分的講述,揭示文學(xué)外圍的一些活躍力量怎么滲透到文字實(shí)踐之中。不過(guò),從“后”的視角來(lái)看,如此的內(nèi)外之隔,其實(shí)是人為設(shè)障,然后又自我取消。如果沒(méi)有物質(zhì)載體的基礎(chǔ),文字的實(shí)踐本身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對(duì)作品的命名或指認(rèn),雖然主要指代它的文本內(nèi)容,可是,作為基礎(chǔ)的載體問(wèn)題始終如影隨形,甚至有時(shí)候還成為文學(xué)命名的關(guān)鍵。比如,章太炎即以“有文字著于竹帛”來(lái)定義“文學(xué)”,以為踵事增華的文采、文字的操練,不過(guò)是華而不實(shí)的細(xì)枝末節(jié),真正的根本在于文字,在于竹帛。他回顧本根,以如此“退化”的方式來(lái)看待文學(xué),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換一個(gè)角度來(lái)看,好像又恰恰代表一種最時(shí)髦的看法:文學(xué)的實(shí)踐和物質(zhì)文化的發(fā)展不能割裂。⑤
當(dāng)然,如今的文字實(shí)踐不再著于竹帛,而常常流布于網(wǎng)絡(luò),甚至文字本身也不見(jiàn)得要照過(guò)去最嚴(yán)格的規(guī)范來(lái)書(shū)寫(xiě)和運(yùn)用,種種網(wǎng)絡(luò)語(yǔ)言的出現(xiàn),勢(shì)必要再次沖擊我們目前所理解的“語(yǔ)言學(xué)轉(zhuǎn)向”。“語(yǔ)言學(xué)轉(zhuǎn)向”關(guān)注“我們?nèi)绾伪硎鑫覀兯獣缘氖澜绲谋举|(zhì)”。在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里,其直接的體現(xiàn)是一系列的科學(xué)主義文論,諸如俄國(guó)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píng)、布拉格學(xué)派、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hào)學(xué),乃至解構(gòu)主義。這些流派雖然紛繁各異,卻似乎共同標(biāo)舉內(nèi)部研究作為其解題關(guān)鍵,以為“語(yǔ)言”乃文內(nèi)之事,無(wú)論其輻射能力多大,首先還是一種文學(xué)“語(yǔ)法”——無(wú)論是作為風(fēng)格、修辭,還是一種普遍結(jié)構(gòu)⑥。這樣一來(lái),就與《指南》的定位頗為不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被置于“文化與媒體”的板塊之中,被視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
盡管馮進(jìn)用文本細(xì)讀的方法辨析了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亞文類(lèi)——穿越小說(shuō)的風(fēng)格和情節(jié)模式,但其著力點(diǎn)仍在澄清其所代表的道德意識(shí)和新的閱讀范式,將這種全新的轉(zhuǎn)變看作是具有活力的文學(xué)叛逆和創(chuàng)新。她沒(méi)有回應(yīng)上面陶東風(fēng)所謂的“去精英化”問(wèn)題,而是采用了一種新的立場(chǎng),將“娛樂(lè)”這個(gè)一度被貶抑的文學(xué)態(tài)度,重新定位為新語(yǔ)境下的“創(chuàng)造力”。她由此就把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接續(xù)到了通俗文學(xué)和大眾文學(xué)的脈絡(luò)之中。在這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被當(dāng)作一種新的類(lèi)型來(lái)處理,而不是一種基于載體的文學(xué)實(shí)踐。換言之,它排除了其他一些也經(jīng)由網(wǎng)絡(luò)傳播的文字,比如當(dāng)代的一些古典詩(shī)詞創(chuàng)作。我們似乎無(wú)法將其看成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它背后強(qiáng)大的傳統(tǒng),使它免于被簡(jiǎn)單地定性。因此,我們需要叩問(wèn)到底什么是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我們將之視為文學(xué)的依據(jù)或者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而這些新的觀念是否足以幫助我們修正對(duì)“文學(xué)”整體觀念的理解?
與此相似,近年來(lái)風(fēng)行的“視覺(jué)文化轉(zhuǎn)向”也同樣促使我們對(duì)文學(xué)或語(yǔ)言的定義加以重新調(diào)整。圖文的互生關(guān)系,古已有之,于今為烈。魏樸(Paul Manfredi)把目光聚焦到了雜志圖像和木刻版畫(huà)之上,并指出當(dāng)代詩(shī)人身份日趨多元化,其中的一維便是畫(huà)家。這種以回向傳統(tǒng)來(lái)面向未來(lái)的趨勢(shì),點(diǎn)出了文學(xué)史所具有的回轉(zhuǎn)和跨界的特性。那么,“文學(xué)”的定義是否也會(huì)因之回轉(zhuǎn)到過(guò)去?相應(yīng)的,我們對(duì)其“語(yǔ)言”和“功能”是否也要進(jìn)行調(diào)整?而這種調(diào)整又怎樣和西方理論、西方文化的影響合而觀之,一并處理?王斑在第17章里給出了他的看法。在他看來(lái)近代中國(guó)的文學(xué)實(shí)踐強(qiáng)化了“文以載道”的理念,而西方美學(xué)的傳入并無(wú)助于我們形成某種超越意識(shí),恰恰相反,它強(qiáng)化了文學(xué)的政治性傾向。
四
在此,有必要說(shuō)明,這種“政治”不必局限在社會(huì)層面上的權(quán)力運(yùn)轉(zhuǎn)和事務(wù)管理,而同時(shí)代表不同觀念間的張力關(guān)系。第四部分“議題與論爭(zhēng)”可以視為文學(xué)政治性的表現(xiàn)之一。通過(guò)將現(xiàn)象或思潮的論爭(zhēng),看成是刺激文學(xué)發(fā)展的動(dòng)力甚至機(jī)制,《指南》有效地傳遞出了這種文學(xué)的政治性運(yùn)轉(zhuǎn)機(jī)制,給出了一種文學(xué)史的發(fā)生學(xué)解釋。在早前的一篇論文《從文學(xué)爭(zhēng)論看海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范式變遷》中,張英進(jìn)已經(jīng)明確地表明,要將文學(xué)論爭(zhēng)或觀念變遷看成是促進(jìn)文學(xué)史發(fā)展動(dòng)力的看法。在他看來(lái),1960年代夏志清和普實(shí)克圍繞《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史》的著名論爭(zhēng),1993年劉康、張隆溪、林培瑞(Perry Link)和杜邁克(Michael S. Duke)圍繞理論和經(jīng)驗(yàn)的筆談,或者2007年史書(shū)美和魯曉鵬關(guān)于華語(yǔ)語(yǔ)系的分歧等,恰好階段性地勾勒了海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發(fā)展軌跡,說(shuō)明其在方法論上的演進(jìn)。⑦
論爭(zhēng)在此變成一種動(dòng)力機(jī)制(institution),代表的是一個(gè)開(kāi)放、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而不是一個(gè)自治、自足的(autonomous)的系統(tǒng)。就多數(shù)的文學(xué)史而言,對(duì)重要作家作品進(jìn)行導(dǎo)讀和梳理,仍是最基本的選擇方案。這種方案中的“史”的觀念主要是追隨時(shí)間的線索,并不能特別說(shuō)明文學(xué)史的內(nèi)生動(dòng)力的問(wèn)題。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關(guān)于“重寫(xiě)文學(xué)史”的論爭(zhēng),基本上還是屬于這種方案。而《指南》則有所不同,它從論爭(zhēng)看歷史,重在說(shuō)明論爭(zhēng)如何與靜態(tài)的歷史觀形成對(duì)話,文學(xué)史的內(nèi)生原則與外部的推力并不是決然割裂的。陳思和特別提醒我們,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也在一定意義上扮演了推動(dòng)文學(xué)史發(fā)展的力量。韋勒克(René Wellek)早在他的《文學(xué)理論》中就說(shuō)明,文學(xué)史、文學(xué)批評(píng)和文學(xué)理論是一體互融的,難于精確區(qū)分,整體性的觀念于焉浮現(xiàn),它將文學(xué)閱讀、文學(xué)寫(xiě)作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冶為一爐。在《中國(guó)學(xué)界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概覽》一章里,陳思和以三個(gè)變遷的概念來(lái)理解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從“新文學(xué)”到“現(xiàn)代文學(xué)”以至“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命名的變化,指涉了研究動(dòng)機(jī)的轉(zhuǎn)變和學(xué)科定位的變動(dòng)。“新文學(xué)”以批評(píng)“舊文學(xué)”“死文學(xué)”而建立合法性;而“現(xiàn)代文學(xué)”則因應(yīng)現(xiàn)代化的國(guó)家建設(shè)而生,到最后鑒于文學(xué)研究日益僵化的分科建制而提出反思,以期凝成一種文學(xué)整體觀。
與中文學(xué)界多樣化的動(dòng)力機(jī)制不同,海外學(xué)界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在張英進(jìn)看來(lái)更集中地表現(xiàn)出一種“現(xiàn)代性”的戀物癖。從早期現(xiàn)代性、翻譯現(xiàn)代性到都市現(xiàn)代性、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性,乃至后社會(huì)主義的美學(xué)現(xiàn)代性,名目繁多,令人目眩。研究者持續(xù)深耕現(xiàn)代性的諸多層次,表面上看各有千秋、迭代有致,但張英進(jìn)指出,這毋寧更像是一種拓?fù)浣Y(jié)構(gòu),其彼此貫通,相互折返,并不是一條前進(jìn)的直線。拓?fù)涞挠^念,除了有對(duì)文學(xué)史線性意識(shí)的反叛,也不妨揭示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自身的發(fā)展特性。“現(xiàn)代性”徘徊不去,既可代表一種屬性,但又因其如此的反復(fù)、不定,充滿變化的前綴,所以還可以被進(jìn)一步地定性為“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如此一來(lái),聯(lián)系到上述的“整體性”,我們似乎可以推論:文學(xué)史的不穩(wěn)定性,恰恰在于它試圖去囊括更多的內(nèi)容,以求完整。整體觀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種拓?fù)涞囊庾R(shí),而不是一個(gè)與寬度和廣度相連的平面。
“記憶”或者可以看成是這種拓?fù)鋵W(xué)發(fā)生的重要節(jié)點(diǎn)。在這部分的其他兩個(gè)章節(jié)中,柏佑銘(Yomi Braester)和陳綾琪有志一同地處理了時(shí)間、記憶和創(chuàng)傷的問(wèn)題。作為引申,文學(xué)史本身也可以視為一個(gè)記憶的成果。透過(guò)勾連過(guò)去的種種來(lái)疏通知識(shí)、展示變化。當(dāng)然對(duì)兩位作者來(lái)說(shuō),記憶本身是被高度選擇和把控的結(jié)果,怎么記憶、記憶什么,有其不得不為的無(wú)奈,但透過(guò)實(shí)驗(yàn)性的寫(xiě)作和私人的回憶,那種整體的、集體的記憶有望得到補(bǔ)充或修正。這是否在一定意義上回應(yīng)了錢(qián)鐘書(shū)所謂的“片斷”意識(shí)?龐大的、精巧的歷史架構(gòu),總有趨于支離的趨勢(shì),總有轟毀坍塌的一天,最后得以保存的還是那些“零星瑣屑的東西”和片言只語(yǔ)⑧。再一次地我們注意到重要的不是那個(gè)連貫的“現(xiàn)代性”,而是補(bǔ)綴在前面的那些修飾“早期”“翻譯”“都市”“社會(huì)主義”等。因此,“整體性”不是周?chē)?yán)的系統(tǒng)工程,而是本雅明的星座圖(constellation)。它們遙不可及,卻又遙相呼應(yīng)。
在關(guān)于海外學(xué)界文學(xué)研究范式的討論中,張英進(jìn)不無(wú)遺憾地指出,整體性的消失正在成為一種共識(shí)。這種共識(shí)驅(qū)策研究者們以異質(zhì)性和片段性來(lái)建構(gòu)他們的批評(píng)實(shí)踐。這種實(shí)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的持續(xù)低迷。但是,他同時(shí)堅(jiān)信,文學(xué)史的寫(xiě)作不妨通過(guò)這些碎片來(lái)進(jìn)行整合。他不無(wú)預(yù)言性地寫(xiě)道:“鄧騰克(Krik Denton)在某種程度上達(dá)到了這一要求,他在介紹東亞文學(xué)的一部參考書(shū)中負(fù)責(zé)編輯長(zhǎng)達(dá)329頁(yè)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部分,包括開(kāi)頭的四篇專題長(zhǎng)文,及隨后42篇分述作家、作品、學(xué)派的文章……然而這本書(shū)名為‘指南、竟不敢妄稱文學(xué)史。”⑨張英進(jìn)的這番評(píng)述頗有自況的意味。通過(guò)三十章的內(nèi)容、四個(gè)板塊的設(shè)計(jì),張英進(jìn)提出了如何通過(guò)碎片來(lái)重建整體性的可能性。當(dāng)然,這個(gè)整體并不是一個(gè)被復(fù)原的華美宮殿,而更可能是一個(gè)廢墟群落。他所謂的整體性,不是連貫、完整、協(xié)調(diào)和有序,而是使它們成為問(wèn)題的思辨和導(dǎo)向。
2019年12月12日
【注釋】
①Dara Downey, Ian Kinane, and Elizabeth Parker,eds.Landscapes of Liminality:Between Space and Place. London&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6, p.2.
②劉禾:《跨語(yǔ)際實(shí)踐:文學(xué),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中國(guó):1900—1937)》,宋偉杰等譯,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4,第262頁(yè)。
③周蕾:《婦女與中國(guó)現(xiàn)代性: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閱讀政治》,蔡青松譯,上海三聯(lián)書(shū)店,2008,第261頁(yè)。
④大衛(wèi)·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學(xué)?》,查明建、宋明煒等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⑤相關(guān)論述參閱王德威:《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新論:義理·倫理·地理》,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4,第69-71頁(yè)。
⑥有關(guān)語(yǔ)言學(xué)轉(zhuǎn)向和現(xiàn)代文論關(guān)系的簡(jiǎn)要論述參考朱立元主編:《當(dāng)代西方文藝?yán)碚摗罚A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7,第7-8頁(yè)。
⑦張英進(jìn):《從文學(xué)爭(zhēng)論看海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范式變遷》,見(jiàn)《理論·歷史·都市:中西比較文學(xué)的跨學(xué)科視野》,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5,第146-161頁(yè)。
⑧錢(qián)鍾書(shū):《讀〈拉奧孔〉》,見(jiàn)《七綴集》(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33-34頁(yè)。
⑨張英進(jìn):《歷史整體性的消失與重構(gòu):中西方文學(xué)史的編撰與現(xiàn)當(dāng)代中國(guó)文學(xué)》,見(jiàn)《理論·歷史·都市:中西比較文學(xué)的跨學(xué)科視野》,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5,第100頁(yè)。
(季進(jìn),蘇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本文系國(guó)家社科重點(diǎn)項(xiàng)目“英語(yǔ)世界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傳播文獻(xiàn)敘錄”的階段性成果,項(xiàng)目批準(zhǔn)號(hào):17AZW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