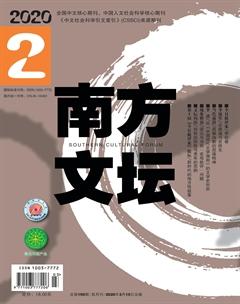空間的時間化詮釋
龐白的新出散文詩集《唯有山川可以告訴》在對“山川”進行空間化呈現時,卻總貫以時間維度進行詩意詮釋,而在徹悟時間的神秘性、消逝性和不可逆性等本質后,又以“空間化”的形式定格“時間”,是一種直抵時間本質與存在意義的時空之思,超越了以往散文詩拘泥于書寫“小感傷”“小情緒”的囿限,對擴大散文詩題材疆域與傳達方式均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山川”作為空間的時間化
“山川”本屬地質學概念,主要指山岳、河流,但在文學場域中常泛指各種景色、風景,而在《唯有山川可以告訴》中主要指廣西各山林、村莊、港口、關卡、建筑、江河湖海等,具體而言有元寶山、花山、西山、漓江、大明山、鎮南關、八角寨、南湖、黃姚鎮、揚美鎮、大瑤山等,但關涉這些地名的詩并非對廣西各地區各民族的民俗風情、地域特色進行呈現,各地名其實只是“空間”的一種標識名稱和具象呈現形式,是“空間”的具體依托載體。這些“空間”都不僅僅是地理、自然意義上的空間,更是一個蘊含歷史、文化、思想的精神空間。
龐白在對這些“空間”進行書寫時最大的特點是讓空間時間化。所謂“空間的時間化”,是將空間的靜態形式納入時間的動態過程中,體現萬事萬物的變動過程和衍變軌跡。時間與空間都是宇宙間萬事萬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二者“如同一對孿生子,總是結伴而行”①,由此空間的時間化與時間的空間化亦成為一體二面的存在合體,二者無法剝離而獨立存在。黑格爾曾指出“空間的真理性是時間,因此空間就要變為時間,并不是我們很主觀地過渡到時間,而是空間本身過渡到時間”②,王夫之在《周易外傳》卷四中亦對空間向時間的轉化作過分析:“天地之可大,天地之可久也。久也持大,大以成久。若其讓天地之大,則終不及天地久也。”“大”為空間,“久”為時間,二者相互關聯,“大以成久”則說明空間可轉化成時間的規律。可見,空間的時間化是空間與時間之關系的基本規則。事實上,宇宙本是一個時空結合體,空間永遠無法割裂于歷史之外,任何空間都不是純粹的空間,而與時間、歷史記憶結合于一體,列斐伏爾曾提出的“空間的意識形態”概念所強調的便是空間與時間、歷史記憶之間的結合。對此法國杜夫海納也曾指出“時間”是“內部意義的形式”,是主體性的,而“空間”是“外在性的根本”,“自我同時包含時間性和空間性,‘在此(即‘定在)的‘此,既有時間的意義又有空間的意義”③。可見,任何空間都必須處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流之中,時間的終結則意味著空間的崩塌與毀滅,由此人們通過對空間的感性審美把握內在的生命變動過程,以時間擁抱宇宙,以時統空,不同時代的人都處于異時同空的狀態。詩人體悟到這種狀態并在詩中呈現出來,體悟了空間與時間的關系以及空間的時間性本質。龐白顯然對空間的時間性本質進行過深入探索與思考,他在詩中將時間觀念分解在各個空間及不同空間的轉換中,以時間融會空間,使時間以潛在形態存在于每一個空間形式中,使空間不限于“此時”的瞬間限制,從而達到時空統一。龐白在面對“山川”等任何地理、自然空間時,這些“空間”都不僅僅是“此時”和“此地”的存在,而是被置放于時間維度上的歷史記憶,任何景點、風景都貫穿他對“時間”的思考,如在“元寶山”時龐白的思緒綿延至“16億年前”,由此思考瞬間與永恒的關系“一萬年,一億年,于他們,是瞬間,也是永恒”(《瞬間。元寶山》);在花山欣賞壁畫時他思考的是“時間行經此處,此處即是世事;時間行經彼處,彼處均為浮云。/時間行經至此,正逢月光灑滿大地,四野溫存,天地寂靜”(花山·壁畫)。在揚美古鎮,他想到的是“它們躺下,不知又要躺幾千幾萬年”(《揚美那些轉彎》)。幾乎每一首詩中都潛涌著龐白對“時間”的思考,幾乎每一處景點都被他“時間化”,被置放于時間、歷史的縱向維度上進行審視、思考,如《竹林深處有大圩》中的“時間,又過去一千年”,《一碗粥里的狂歡》中的“黑鍋煮著人間白粥,一熬就是五六百年”,《海·聽》中的“此岸到彼岸,有時很遙遠,遠得一輩子也望不到邊際”等詩句。可見,龐白筆下都是以“山川”的各種場景為基點,他總由眼前的“景”追溯至歷史深處,思考時間在空間上的作用力與歷史,動輒追述上千年甚至上萬年、億年,是一種典型的空間時間化。“山川”本是作為空間的一種存在形式,龐白卻將之作為介質與載體,表達他對時間的感慨,他通過空間思考時間的流逝、歷史的悠遠、歲月的無情,并由此思考時間對空間的超越。
同時,空間的時間化其實是空間的一種歷史化,海德格爾曾指出,“時間”是“歷史”的根據,“歷史”則是“時間”的“存在方式”,因而被時間化的空間被賦予了歷史感。而每個人都是宇宙間的匆匆過客,都處身于暫時的、有限的“此時”與“此地”的時空交會處而無法超越時空,因此空間的歷史化在詩人筆下大都需要通過想象,需要詩人用自己的感覺與審美經驗去補充時間距離造成的經驗“空白”。故而,空間的歷史化常通過想象的空間展開,龐白常憑借一些“物”而展開對歷史的追溯,在他詩中,苗瑤侗寨的歌謠都“隱約逸出第四紀冰川冷杉的氣息”(《瞬間。元寶山》),他由一座山而聯想到“寒武紀”:“寒武紀時期形成的褶皺山,雄壯又殘忍。”(《只剩下風的聲音》)將風聲聯想成清兵的馬蹄聲:“每天清晨,馬蹄聲自動鳴響,整齊劃一。/……他們是馮子材、蘇元春、王德榜、陳嘉部、蔣宗漢的部隊。”(《鎮南關背后》)所有的“空間”無不投射出“時間”的影子,而這時間的影子中沉浮著的是源遠流長的歷史軌跡和歷史故事。
龐白將空間轉化成對時間的感嘆,形成其獨特的藝術符碼、審美取向和殊異的詩歌風貌。
二、時空的神秘化呈現
西川的《在哈爾蓋仰望星空》曾感嘆:“有一種神秘你無法駕馭/你只能充當旁觀者的角色/聽憑那神秘的力量/從遙遠的地方發出信號/射出光來,穿透你的心。”這種“神秘”是在“哈爾蓋”和“星空”兩個“空間”之中被感知與發現的,但如前所述,任何空間都不能脫離于“時間”之外,而“時間”本身對于每個生命個體的長短、存在與消失、短暫與永恒均具有不可知性和不可預測性,從本體學意義上言之具有不可言說的神秘性,因而西川所感嘆與發現的“神秘”其實是時空交錯中的“神秘”,是宇宙中存在卻無法言說與道明的“神秘”。人類存在于時空之中,縱向的時間與橫向的空間組成宇宙,人類不過是時空之中的存在形式之一,任何一種物都是一種空間存在,亦都存在于時間之流中。而時空的運行不受人左右,人無法全知世界,因而其未知領域便具有神秘性。由此,人在感知時空之時,常受限于自己的視域與認知而發現時空、宇宙的神秘性。
龐白深知自己存在于有限的、短暫的“此時”“此地”,無法全知世界、宇宙,因而他頗為重視來自大自然的“神秘感”,并在詩中對這種“神秘感”進行發掘與呈現。《唯有山川可以告訴》原本名為《廣西,廣西》,新標題的巧妙處不僅在于突破了“廣西”的地域限制與狹隘性,更在于揭示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神秘性。波德萊爾善于“傾聽”大自然的聲音,將大自然視為與人相應同等的存在個體;而龐白是“告訴”山川,讓山川傾聽自己的聲音,顯然與波德萊爾的觀念具有相通性。波德萊爾曾借用斯威登堡的話指出“天是一個很偉大的人,一切形式、運動,數、顏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應和的”④,龐白對此心有同感,將自然作為“人”,作為“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應和的”對象進行交流、對話,這種交流對話與應和本身就具有神秘性。因此,龐白不是對大自然進行浪漫主義式的直抒胸臆,而是用通感、夢幻、靈魂對話等方式隱秘暗示,形成人與“山川”之間的隱秘交流,既凸顯出山川的神秘性,亦呈現出波德萊爾所重視的人與自然的應和契合。
美國威廉·詹姆斯曾指出神秘主義具有四個特性,即不可言說性、可知性、暫時性、被動性⑤。龐白在其散文詩中常強調“不可言說”,呈現出萬事萬物所附著的非理性的神秘之感,如《天湖觀鷹》中他將蒿草、青苔、琥珀都視為“不可言說”的:“不可言說的,還有堤壩上的蒿草、隱居深山的青苔和湖底的琥珀”;在龐白眼中,許多動作、行為都具有神秘感、儀式感,連“俯瞰”都是“不可言說”的,如《去參觀合浦漢墓,途中看見》中他所言的“俯瞰是不可言說的秘密”。在“不可言說”的背后,神秘性的根源在于龐白覺得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靈、有神性的。在龐白筆下,萬事萬物皆有靈性、神性,他擷取了大量富有“神性”的物象,如《經幡》中的“經幡”,《通靈的陽光》中的“陽光”,《云梯,通天直上》中的“云梯”,《天湖觀鷹》中的“鷹”,都是富有“神性”“靈性”的充滿神秘之物。《經幡》中的“經幡”在龐白“第一眼”便延伸到“前世”,“第一眼看到的經幡,是前世留下那條”,將空間意象附著“時間記憶”,顯然是一種空間的“時間化”。而這些在“溝壑之上,樹林之上,蔚藍之上”的“五色經幡”如凝固一樣,只有“蒼鷹”不知疲憊,“一整天都繞著自己的圈子”,字里行間的儀式感凸顯出神秘感,“直到半夜,光芒飛過山梁,才把我生命的重量,護送到高處”,詩句中的“一整天”“半夜”“生命”都是時間性詞語,而“山梁”“高處”則是空間性詞語,在這時空轉換之中“經幡”所附著的“不可言說”的神秘性不言而喻。龐白詩中還常出現“神秘”“神圣”“神”等詞語和眾多體現神秘感的詞匯,如“美,有美的源起、延展和縱情,也自有美的內斂、節制和神秘”(《只剩下風的聲音》)。“大海,除用遼闊、壯麗、恐懼、神秘來形容,還能想出些什么別的詞語?”(《海·聽》)等。而且龐白還相信在與“我們”共同的時空中有神仙、鬼魂的存在,如《桂西北,會諸神》中的“會諸神”行為呈現出龐白有泛神論思想,連“紅”這種顏色都成為神靈、鬼魂:“那紅,是神靈,是鬼魂。”(《褚紅》)他還直接寫到神仙或鬼魂等非世間物:“一定有神仙或者鬼魂與我們朝夕相處。”(《要相信手臂的搖動》)“可能還有別的。比如神、人類和命運。”(《桂西北,會諸神》)這種神秘更多地在于時間、歷史的久遠所沉淀的神秘性。在對“山川”、自然的“神秘性”的感知中,龐白對秘密的通道、洞口頗有興趣,如《黃昏,勾漏洞遇隱士》中“洞口仍然灰著、綠著、暗淡著、蒼茫著,如微醉的明月,有千年之約”,《表白》中“有一條不為人知的神秘通道,引領我走向大海”,《穿過迷路》中的“一千年后,珠城白龍打開了所有通道”,這些“通道”“洞口”都是空間存在,但在龐白筆下總會延伸到時間范疇,由于時間、歷史的久遠而更顯出“神秘性”。此外,龐白詩中對“他們”的使用,帶有一種講故事的神秘感。“他們”是神,是精魂,如《澄碧湖畔,琴聲沖天直上》中塑造了一個神秘的“男人”形象:
舟上,素衣布鞋的男人,雙眼微閉,久久不語。
他仰望上蒼。
蒼穹如琴。
“素衣布鞋”顯示出男人是不同凡俗之人,“雙眼微閉,久久不語”中透露出男人的神秘之感,而“仰望上蒼”則喻示著男人與上蒼的對話、交流,更突顯出莊嚴感與神秘感。此外,龐白詩中的“水手長”“哲人”“占卜師”“巫師”“仙姑”等都帶有神秘感,凸顯出龐白時空之思的神秘性。
三、在“禪悟”中超越時空
在對時空的思考與感悟中,龐白詩行間流露出一種禪意和道家之風,這是對時間、空間參透后方能擁有的情懷與意味,是一種超越時空囿限的大徹大悟。他的很多詩都富有一種禪悟之后的禪理。《四妙閃一閃的光》中塑造了一個“哲人”:“他是個哲人,常盯著燈塔替代我們思考。”這個“哲人”在龐白筆下是一個水手長,他對“時間”的體悟直抵時間本質:“這個時候,沒有什么比那四秒閃一閃的光,更及物了——/遙不可及,又近在咫尺;閃爍不定,但光芒萬丈;萌芽生命,也窩藏死亡。”全詩只有兩句,卻蘊含深意。“四秒閃一閃的光”既有“四秒”的時間維度,亦有“光”的空間維度,這“四秒閃一閃的光”其實是“此時”與“此地”時空交匯處的一種隱喻,因而在哲人眼中,沒有什么比“四秒閃一閃的光”更為及物,龐白在詩中通過“哲人”的視角道出了“四秒閃一閃的光”所蘊含的時間與空間、短暫與永恒、生與死、遠與近、強與弱、存在與消失等相對性哲理。
其實龐白正是這樣一個“哲人”。在其詩中,龐白始終如一個高高在上的智者,觀世間變幻,思時空輪換,透出一種大徹大悟的智慧與禪味。而這些“觀看”與“思考”都是站在時間維度上進行,或思考時間的短暫、流逝和不可逆性,如“——流逝的,永不重來。/就像頭頂上的藍,雖然穿透來世今生,每一寸光亮,卻已截然不同”(《海·島》);或呈現對瞬間與永久的體驗,如“瞬間即永久,即一去不復返,即所有的從未來臨”(《水上人家》);或徹悟在時間面前的無能為力和人類能力的有限性,如“我們能伴隨冬季順利走向春天,但無法觸摸一次影子的溫度”(《無數影子浮現邕江》);或揭示時間與人類的關系,如“在這之外,一天又一天,淡化仇恨的是時間,消解恩情的也是時間。”(《西山又一日》)。在對“時間”的徹悟中,一些詩蘊藏一種看破世事的滄桑與達觀、徹悟,如《西山晚鐘》中:“世間的紛爭、煩惱、無著,如霧靄升騰,隱入茶山。/山間最后一絲殘陽,照亮歸一之萬物。”人世間所有的紛爭、煩惱在時間之維上其實太過渺小,在時間的統治下,最后一切都“萬物歸一”,顯示出龐白站在時間之維上對人類喜怒哀樂的思考深度。龐白還在《德保山村看占卜》中刻畫了一個對時間深有體悟的“占卜師”:“占卜還給了我另一個告誡——/除了耐心,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幫我們渡過時間之河。”龐白通過“占卜師”的“告誡”揭示了“空間”與“時間”的關系和時間無法超越的真理。在對“時間”徹悟之后,龐白意識到人世間的一切在時間之維上都“很難還有別的”(《西山又一日》),因此他還參透了“愛”的本質:“愛又如何?/往事已忘,往事沒在往事里。”(《風起的日子,新月如鉤》)在時間河流中,“愛”不過是人在“某時”產生的一種情緒,在時間的沖洗下都變成“往事”,無論如何轟轟烈烈的愛最后都被掩蓋在“往事”里,其實是被“時間”無情地掩埋,顯示出“此時”和“曾經”的重要性。同時,龐白亦參透生死真諦,如《水上人家》中的“所謂遼闊、壯美,對他們而言,只是觸手可及的死亡”,《南湖邊,柳樹下》中的“那棵柳樹看盡了人間的生離死別和無常變幻”等都是對生死的看透與參悟。而且,龐白還在時間維度上對人的存在本質進行了“徹悟”,如《那山·那坡》中的“人只是從它們身邊經過,也可能連經過都算不上”。“經過”二字是“此時”與“此地”的交匯,其背后潛藏著“某時”“某地”,但人的存在相對于世間之物而言的意義僅在于“經過”甚至“連經過都算不上”,這是龐白在時間之維上對人的存在的思考。事實上,人與物、自然之間是相對的存在,都作為“空間”的一種具體形式而呈現,都處在瞬間與永恒的終極話題中無法逃脫“時間”的統帥。這是龐白在時間維度上對人的存在的體悟,人與世間萬事萬物一樣都只是一種存在,甚至人是比很多事物更短暫的存在體,相對于“山”“坡”而言,人只是“經過”甚至“連經過都算不上”的一種存在。龐白道出了在時間面前人作為一種存在體的渺小,透出一種看破一切、大徹大悟的禪意。
龐白還將他對美的體悟亦納入“時間”范疇中,因為美關系到瞬間與永恒,最后回落到“時間”這一主體,如《夏日午后,漓江邊,蜻蜓飛臨》:“它們的美漸次開放…/還來不及接受這濃重的美,夜色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覆蓋下來了。/是夜色青煙般的彌漫和消散,如終將消逝于時光中的容顏。”《只剩下風的聲音》中“美,從來不會無聲無息、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美,有美的源起、延展和縱情,也自有美的內斂、節制和神秘”。“美”是“空間”在某一瞬間所呈現出來的審美特征,亦是最無法抵擋“時間”而易消失的,“美”的存在與呈現需要“時間”的依托,其在“時間”范疇中的短暫、不可逆、瞬息萬變而讓詩人們愿意以文字的形式將其定格,附著了人們對于時間的美學思考。
在體悟到時間的不可超越性和不可逆性后,如何超越“時間”的時間限制?龐白所做的便是將時間“空間化”,如前所述,時間與空間本為一體而構成宇宙,所謂“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即上下四方為空間,古往今來為時間,空間是凝固的時間,時間是流動的空間,因此當詩人意識到時間不可逆、無法阻止其流逝,因而將時間性積淀到空間中,以“空間”的形式延續到“古往今來”的時間流之中。龐白對任何事物的思考都以“時間”為維度展開遐想思緒,當他徹悟到時間的流逝性、不可逆性、不可重復性等本質后又回落到“空間”,試圖以“石頭”“家”等空間意象定格“時間”,如《隨便一塊石頭都是家》中所傳達:“用一塊石頭寄存流逝的腳步,用一塊石頭埋葬旅途上的青春,用一塊石頭壓縮無窮思念。”龐白在徹悟到時間的短暫、流逝和不可逆性后以“石頭”“家”等空間意象作為時間終結本質的暫時依托之所,從而在一定程度和精神意義上超越時空,這是將時間空間化的一種方式,亦是對空間時間化的一種回應與應和,蘊含一種對時間本質體悟透徹后的滄桑、淡定之感,不無道家與佛禪中的“無為”“空無”之蘊。
【注釋】
①張今杰:《奧利費·賴澤的時間觀研究》,《湖南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②黑格爾:《自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0,第40頁。
③[法]杜夫海納:《審美經驗現象學》,韓樹站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第188頁。
④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第99頁。
⑤[美]威廉·詹姆斯:《宗教經驗種種》,尚建新譯,華夏出版社,2005。
(羅小鳳,揚州大學文學院。本文系2018年度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媒體語境下新詩傳播轉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8ZWB002;2018年度江蘇省“雙創人才”項目、第64批博士后基金面上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18M64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