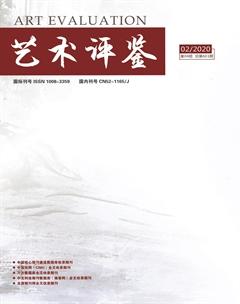攝影對行為藝術的二次創作
馬丁 李琦 胡意娟
摘要:行為藝術作為一種現場表演形式的藝術,其作品必須通過媒介來進行傳播和保存,此時影像就成了最適合的那個媒介。同時,除了記錄功能,攝影也對行為藝術的延伸起到二次創作的作用。所謂二次創作,是指攝影在記錄的同時,也會對行為藝術進行解構,最后再以影像的形式保留傳播。此時的影像作為行為藝術的“衍生品”也具有一定的創造性、藝術性。本文將結合東村藝術家榮榮的實例,論述攝影對行為藝術的二次創作。
關鍵詞:觀念攝影? ?行為藝術? ?二次創作
中圖分類號:J0-0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04-0183-02
一、攝影的觀念性
在以進行攝影創作時,不管是客觀記錄還是主觀導演,攝影所體現的真實總是與客觀事實存在偏差的攝影師將個人的意識作用于照片上。所以攝影在誕生之時,就具備“觀念”的性質。
攝影史上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證:如雷蘭德的《人生兩途》、亨利佩奇魯濱遜的《秋》《彌留》等,在這些作品中體現了攝影對觀念表達的作用,體現出觀念的特性,但當時“觀念攝影”這一概念在當時并未被明確定義。觀念攝影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其概念起源于西方后現代社會,并逐漸波及全球成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蕭沉在《攝影一觀念,人們就傻眼》[1]一文中曾提到:在運用“攝影”表達“觀念”時,應考慮攝影在其中扮演的究竟是“記錄”工具的角色還是“語言”工具的角色。如果是前者就不是觀念攝影,如果是后者,當可以接受,因為攝影只有作為表達某種觀念的“語言”工具時,才是必須的,才與觀念產生不可割舍的關系。
攝影必須是觀念的成果,而不僅僅是記錄的工具。[2]
二、攝影對行為藝術的延伸
行為藝術本質上是一種表演,它的第一受眾是現場的觀眾,表演的過程既是作品創作的過程,也是展示的過程。這就意味著行為藝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當表演結束時,作品就算完成了。能完整觀看到它的只有現場觀眾,若想被廣為人知,必須借助其他媒介來傳播。于是對行為藝術家來說,此時攝影就成了一種很好的手段。保存下來的影像資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個行為藝術作品的延伸,也能算作作品的一部分。因為如果沒有這份資料輔佐,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個作品就不存在。
因此,在做行為表演的這個過程中,利用攝影這一媒介,可對其進行再創作,通過凝固的畫面提煉表演,為其增色,助其傳播。但如果要將其畫面拿出來單獨作為一個作品,那此時的攝影只能算是一種“權沖藝術”。因為行為藝術是先有行為表演,后再靠攝影將其傳播,攝影只是將行為進行再創作。如果以影視制作作為類比,行為藝術家與攝影師的關系就好比導演與攝像師的關系。在電影的創作過程中導演處于絕對核心的位置,他擁有最高權限,可以調度大量資源,但從具體執行再到最終完成作品是需要各個部門的成員合力完成的。同樣,以劇照攝影為類比,劇照在電影制作中主要起到對電影的宣傳作用,并對電影的劇情、人物等也起到塑造作用。這些劇照基于電影本身,但不僅限于記錄拍攝的過程,而對電影的內容有再次的創作和提煉。
所以對攝影師來說,他拍攝的行為藝術照片不僅僅是表演的附屬品,更源自于他自身獨特的視角,對行為表演的凝縮。
三、攝影師榮榮對行為藝術的二次創作
以榮榮的經歷為例,他作為獨立藝術家的生涯確實是從東村開始的。從最開始的拍攝各個藝術家肖像和記錄周遭生活環境,到后來他對拍攝自己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自己的相機前,邊表演邊記錄。這些照片具有的強烈的行為藝術特征與他個人生活中的變化產生出共鳴。[3]
從1995年1月的《原音》開始,包括了倉鑫的《踩臉》、張洹的《鐵箱》、馬六明的《芬·馬六明的魚》、朱冥的《泡沫》,以及張洹和馬六明聯合作品《第三類接觸》,榮榮逐漸從一個攝影師的身份逐漸往導演者的方向發展,他不光記錄行為的過程,也參與行為的設計。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由于東村藝術家們關系的變化,榮榮不再是行為項目的發起者,他更像一個獨立的觀察者,從“東村藝術家”的群體身份中剝離出來,一邊記錄,一邊分析眼前目睹的過程,開始制定自己的獨立項目。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往往將行為和攝影相結合,并多以自拍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觀念和情感。在相機前,他表演;在相機后,他拍攝。而攝影本身既賦予了畫面中表演行為的內涵,又承載了記錄的功能,也可理解為是一種行為表演。
在當時的中國攝影界,攝影參與到行為表演屬于初探,而榮榮由懵懵懂懂的記錄者到參與者,最后成為影像的導演的轉變過程。意味著攝影對于榮榮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強調技巧手法和光影構圖的唯美甜膩的沙龍寫真,而重視的是攝影鑒定、樸素的描述力,圖片的價值意義是照片里描述的行為本身。“東村群體”以身體表演的藝術方式進行表達,采用了20世紀中葉的新聞攝影風格,即不確定的手法隨意即興的快照(snap),使照片具有一種隨意而為止的感覺。看似漫不經心,卻充滿了概念行為藝術的精心設計,兩者彼此抗衡。[4]
四、二次創作的邊界之爭——行為藝術與觀念攝影
就行為藝術而言,行為表演本身是主體,攝影只是為其傳播的一種載體;而對于觀念攝影,行為表演可以是表達觀念的一種形式,影像才是主體。所以單純將行為藝術記錄下來的過程并算不上觀念攝影,觀念攝影應該是有計劃的、有核心架構的攝影。同樣是運用記錄的功能,其兩者的本質卻不同。
在榮榮將他在東村拍攝的影像出版成冊后,攝影和行為藝術的矛盾也在此引發。他把這些在東村拍攝的照片命名為《榮榮的東村》,并在香港的蘇富比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場上以三十一萬元的價格成交,這無疑轟動了當時的行為藝術家們。他們認為榮榮只是對其行為藝術進行了簡單記錄,圖片的創作是基于表演的,是行為藝術的附屬品;而榮榮則認為照片的包含著他作為攝影藝術家獨特的觀察視角,是他的智力創作成果,照片可以作為他個人的再次創作,是對行為藝術家表演的解讀。
榮榮在接受采訪時也曾自述:“我拍他們,最重要的是心靈需要。那個時候自己處于一個完全迷茫的狀態、處于一種困境,但我還是有一種激情熱血,因為有些東西跟你心靈上是有碰撞的,所以你才能產生一種交流。我用相機拍他們,跟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意思,是沒有矛盾的,但其中的意思已經不一樣了。我要用相機把它表現出來,我決定擇取一些部位、擇取一些瞬間、擇取一些角度,這個都是影像的另外一種力量,而他們的行為是在這個過程里頭。”[5]
若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把榮榮拍攝的東村影像看作一個整體、長期的項目,這些影像毫無疑問就是屬于他個人獨一無二的紀實作品。但其中拍攝的行為藝術表演的部分,應該算作是榮榮和其他行為藝術家共同創作完成。或者說,行為藝術家們的表演和榮榮的攝影記錄本就是相輔相成的,行為藝術表演為榮榮提供了攝影創作的素材,激發了他拍攝的欲望;而榮榮的照片也為行為藝術家們保留下了重要的作品資料,也有利于作品的傳播。
五、結語
攝影和行為藝術并不是二元對立的。靜態的圖片作為行為藝術的工具,對瞬間的抓取消解了行為藝術表演稍縱即逝的特性,同時也融入了攝影師的二次創作。所以在藝術創造中,它們相輔相成,彼此啟發,使得整個行為表演藝術成為一個復合多重創作的有機整體,成為了當代藝術中獨有的一種創作方式。
參考文獻:
[1]蕭沉.攝影一觀念,人們就傻眼[J].中國攝影家,2007,(09).
[2]孫宇龍.觀念攝影:在藝術的路上能走多遠?[J].藝術·生活,2009,(01).
[3]巫鴻.榮榮的東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黃樂婷.當代攝影雙重身份的構建——榮榮攝影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8年.
[5]段君.東村行為與攝影紛爭之述[EB/0L].雅昌新聞,2006-05-31.
[6]段君.20世紀90年代北京東村行為藝術[M].香港:香港四季出版社,2016.
[7]王棟棟.對藝術家曾廣智的苒定義[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3年.
[8]沐曉熔.當代觀念攝影創作的瓶頸與突破[J].民族藝術研究,2016,(03).
[9]顧欣.當代觀念攝影表現方法的實踐與思考[D].蘇州:蘇州大學,2010年.
[10]郭晨旭.紅色色彩藝術及其在中國觀念攝影中的情感表現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2年.
[11]王芳.當代文化語境中的中國觀念攝影[D].南京:南京林業大學,2009年.
[12]王海夢.當代觀念攝影中重構表現手法運用的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6年.
[13]畢艷菲.中國紀實攝影的審美性研究[D].貴州:貴州大學,2015年.
[14]鮑昆.記憶·尋找·重構——中國當代風景中的攝影和影像藝術[J].畫刊,2007,(06).
[15]肖明華,陶水平.本雅明的傳統藝術與現代藝術比較研究[J].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