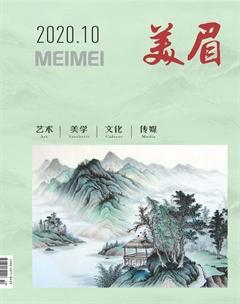踐行達斡爾族“畢力杜爾”舞蹈文化傳承與發展
孫慰慰
達斡爾族人口偏少,現階段總計約12萬人,在黑龍江省、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均有分布。達斡爾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這些傳統的民間舞蹈文化,主要憑借言傳身教的方法進行傳承和發展,但此類藝術家年齡逐漸增快,后繼人才匱乏。隨著民族融合與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達斡爾族舞蹈文化正瀕臨著失傳的危機,如何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達斡爾族“畢力杜爾”舞蹈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理清達斡爾族“畢力杜爾”舞蹈文化脈絡
達斡爾族舞蹈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早在契丹人時期其就已經出現,并屬于一種重要的民族舞蹈文化。就達斡爾族“畢力杜爾”舞蹈而言,主要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地區的阿西爾民族鄉達斡爾族聚居區流傳,該區域大約有六千多的達斡爾族人民。居住在新疆的達斡爾族作為一個西遷的民族,他們遠離本民族原聚居地,其先民由黑龍江遷移過來,時間大概在清乾隆十八年。兩百多年來,達斡爾族人和新疆少數民族共同生活、交往,進而使得生活方式、習俗等發生了部分改變。
新疆塔城地區的達斡爾族舞蹈存在著即興以及自娛等相關特點,經常在親友聚會、春節等場合出現。在動作方面,與達斡爾族日常生活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同時在保留“魯日格勒”某些動作的基礎上,融入了內蒙古族、哈薩克族以及錫伯族等舞蹈風格,最終形成了獨特的“畢力杜爾”舞。
就“畢力杜爾”舞的形成而言,當地流傳著一個傳說。早在1867年,上千戶達斡爾人受戰亂的影響而向北方遷移,此過程中很多人失去了性命,最終抵達塔城時,只剩下三百余戶。達斡爾人在西遷的艱難環境中,期望身處伊犁的首領可以如同云雀一般,在冰雪融化之后,春天到來之時,帶來希望。后來,達斡爾人的期望和云群遨游天際的姿態融合在了一起,再與民間舞蹈動律進行結合,最終形成了畢力杜爾舞。盡管這只是一個傳說,但通過某些線索,如達斡爾人認為云雀代表吉祥、歌詞等,也可以從側面看出一絲真相。
二、掌握達斡爾族“畢力杜爾”舞蹈風格特征
筆者在田野考察中走訪了當地的學者以及民間藝人,了解到“畢力杜爾”舞主要模擬鳥的形態,步伐較為輕快,采用男女對跳的方式,因此,也被稱為“云雀舞”。從人文歷史、民俗風情、藝術文化等多種角度來劃分,新疆的達斡爾族“畢力杜爾”舞蹈是集呼號、舞蹈、音樂為一體的傳統歌舞。呼號多是模仿動物叫聲,舞蹈動作大致為模擬動物、勞動、梳妝照鏡等,大多數反映一些生產勞動及日常生活形態。所用歌曲節奏規整、旋律清晰,每種舞蹈都較為固定的歌曲伴奏。達斡爾族舞蹈基本動作為:提壓腕、彈指、拖步、拖踏步、跺點步以及上下抖肩;其形態特征為:后背直立,屈膝半蹲,手指并攏,時而指間向內握住再展開。行禮動作男女不同,男士:右腳撤后一部,同時左腳腳尖稍稍抬起,落下的同時右膝跪地,雙手置于膝蓋前,低頭行禮;女士:正部位,雙膝朝前半蹲,雙手置于膝蓋上方,低頭行禮。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新疆的達斡爾族受周邊草原民族的影響,動作剛勁有力,節奏輕快活躍,顯示了其質樸粗放的舞蹈風格。而東北的達斡爾族作為漁獵民族,動作較為輕柔,以腰部擺動為基本動律。由此可見,不同的動作形態如實的反映了該民族的生存歷史、生活習俗、心理特征及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多種內容。
三、發揚達斡爾族“畢力杜爾”舞蹈文化內涵
正是一代代達斡爾族人民對本民族傳統舞蹈文化的重視與保護,頑強地延續著文化的有機生命力與活力,才構成了達斡爾族現有的舞蹈文化生態環境。筆者通過實地觀摩、圖像展示、訪談記錄、現場教學等方式的采集和梳理,對新疆達斡爾族的歷史文化和民間舞蹈特點有了新的認知和理解。為了更好的發揚達斡爾族民間舞蹈文化,筆者將本次田野調研的“畢力杜爾”舞蹈文化內容進行了分析、整理、加工,將民間的達斡爾族舞蹈按照教學的要求,對基本手位、基本腳位、基本體態進行了規范,并在不破壞原生態達斡爾族舞蹈風格的基礎上進行適應教學體系的組合編排。并以傳播新疆地域文化特色為根脈,創作了反映新時代達斡爾人民面貌的藝術作品。踐行以創新為動力,積極促進文化認同,傳播中華民族文化思想內涵和審美風范。
總之,達斡爾族“畢力多爾”舞蹈文化傳承是繼承和發展的統一,只有重視對達斡爾傳統民間舞蹈文化的繼承,重視對傳統民間舞蹈文化辯證的分析和選擇,通過創造地繼承,和有繼承地創造,才能在達斡爾舞蹈文化的發展中使文化連續性和創新性得到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