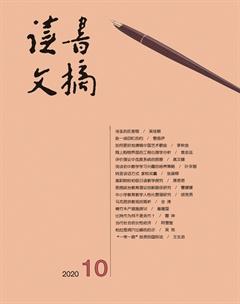柏拉圖洞穴比喻的啟示
摘? 要:我們之所以可以將理想國中的“洞穴”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相聯(lián)系,是因?yàn)槲覀兣c“洞穴”內(nèi)部的人在生活方式上有著相似性。“洞穴”外部是理念世界無疑,但仍留下來一個(gè)疑問,即為什么外部就比內(nèi)部更加真實(shí)。囚徒,面對(duì)哲人王帶來的新的倫理體系,他們并非一定要接受新的倫理體系。
關(guān)鍵詞:柏拉圖;洞穴比喻
一、洞穴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關(guān)系
學(xué)者對(duì)“洞穴比喻”的探析是建立在“洞穴”已經(jīng)存在,并且,他們認(rèn)為“洞穴”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生活的世界這個(gè)基礎(chǔ)之上的,為什么我們要這么默認(rèn)?從“洞穴”到我們的世界,為什么會(huì)有人輕易的接受了這個(gè)觀點(diǎn)?再者,“洞穴”為什么是我們生活的世界?為什么洞穴之外不是我們生活的世界?
柏拉圖將洞穴描繪為有一群人在里面生活的地方。在洞穴中,“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們對(duì)面洞壁上的陰影之外,他們還能看到自己的或同伴們的什么呢?……因此無疑,這種人不會(huì)想到,上述事物除陰影而外還有什么別的實(shí)在”。這表明,洞穴內(nèi)的人都看到同樣的事物,也表明“洞穴”內(nèi)存在“公共領(lǐng)域”的。這樣的描述使得洞穴內(nèi)部與我們的世界有了相同的地方,我們生活的世界,也是人與人共同搭建的公共領(lǐng)域,維持這個(gè)公共領(lǐng)域的要素在于人們需要共同構(gòu)建并遵守一套倫理體系、法律體系、話語體系等,我們的行為并沒有超出由人們共同構(gòu)建的領(lǐng)域的閾值。因此,可以說人類之所以能夠聚合在一起不僅僅因?yàn)榭萍嫉陌l(fā)展,更因?yàn)楣┪覀兊乃枷氲馁|(zhì)料具有一致性,亦可說我們也“觀看”洞壁上的陰影但不自知。有了思想質(zhì)料“那么,如果囚徒們能彼此交談,你不認(rèn)為,他們會(huì)斷定,他們?cè)谥v自己所看到的陰影時(shí)是在講真物本身嗎”。從“洞穴”內(nèi)的人討論日常事情的情形與我們相似,我們并不能證明我們的基礎(chǔ)與囚徒的基礎(chǔ)有何區(qū)別。結(jié)合這兩方面,我們確實(shí)會(huì)很容易就將“洞穴”內(nèi)部的世界看作我們的世界。
二、哲人王與囚徒的關(guān)系
面對(duì)“洞穴比喻”的時(shí)候,我們經(jīng)常把自己立足于哲人的一方,這時(shí)候我們眼里的囚徒是無知甚至讓人憎惡的。但如果我們自己是洞穴里的普通人,面對(duì)哲人、政治哲學(xué)家、哲人王我們會(huì)與之前的看法有何不同?我們要直接面對(duì)的是哲人帶給我們關(guān)于知識(shí)和真理的挑戰(zhàn)。我們現(xiàn)存的知識(shí)也是根據(jù)我們所看到的事物及其經(jīng)驗(yàn)歸納出來的,而這樣的經(jīng)驗(yàn)為什么又不能稱之為真理呢?亦或說,它比哲人所得出的知識(shí)差在哪里?我們可以一眼貫穿漫長的時(shí)間線,我們可以說洞穴里的人不知道何為真理,不明白伯羅奔尼撒海戰(zhàn)中幾位海軍將軍的冤屈,這是因?yàn)槲覀儞碛斜人麄兊闹R(shí)更確切的知識(shí)。所以,站在囚徒的角度,面對(duì)意見與真理,囚徒與哲人王,哲人與政治哲學(xué)家,哲人與哲人王,我們應(yīng)該明晰一些事情。
首先,我們平時(shí)所說的意見常指處于“有”和“無”之間的地方。意見不像是柏拉圖所規(guī)定的真理那樣具有單一的特點(diǎn),它因其本身的根據(jù)而具有差異性。凡是具有差異性的事物都可能顯示出一種確立自己地位的現(xiàn)象,這將導(dǎo)致他們之間的競爭關(guān)系。一般學(xué)界認(rèn)為“蘇格拉底之死”是蘇格拉底自己的選擇,這是因?yàn)樗心芰μ优埽诒粚徟械倪^程中,蘇格拉底確實(shí)敗于雅典人不負(fù)責(zé)任的意見,這個(gè)事實(shí)使得蘇格拉底的弟子們嘗試將意見和真理對(duì)立起來,并要建立可以用來判斷人類行為的絕對(duì)標(biāo)準(zhǔn)。在柏拉圖看來,解決真理與意見之間的沖突的辦法在于尋求一種存在于意見領(lǐng)域之外、高于意見領(lǐng)域的標(biāo)準(zhǔn)。
其次,盡管囚徒不具有相應(yīng)的關(guān)于真理的知識(shí),但囚徒仍具有一套屬于自己的倫理道德體系,“看”是受過教育的人在理念世界的活動(dòng)也是囚徒的唯一活動(dòng),但他們既不言說也不行動(dòng),而哲人在“洞穴”中是需要行動(dòng)的。所以成為一個(gè)哲學(xué)家和成為一個(gè)公民是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導(dǎo)致這兩種存在方式的經(jīng)驗(yàn)現(xiàn)實(shí)的模式是不同的和不相容的。而且,哲學(xué)的經(jīng)驗(yàn)是一種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囚徒的經(jīng)驗(yàn)是一種富有差別的經(jīng)驗(yàn)。那么作為囚徒,面對(duì)哲人的哲學(xué)經(jīng)驗(yàn),囚徒本身被消解了作為人的主體性,取而代之的是作為概念中的一員活著。哲人王降臨于世必將因其要清楚活著的特性,對(duì)善好的追求而改變現(xiàn)有的風(fēng)俗習(xí)慣、倫理準(zhǔn)則和知識(shí)體系等等,面對(duì)這些變動(dòng),作為囚徒就不得不問,如果我接受了這些變動(dòng),我還是我嗎?況且,我有什么理由接受哲人的理論呢?有什么事情可以證實(shí)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是混亂且雜亂無章的?沒有了更準(zhǔn)確的知識(shí)的我們幾乎完全不能判斷眼前這種違背習(xí)俗的話的真理性。
注釋
汪靜教授認(rèn)為,“漢娜.阿倫特通常被視為公共領(lǐng)域思想的開創(chuàng)者。在其1958年發(fā)表的早期著作《人的境況》中,阿倫特將公共領(lǐng)域禪師為一個(gè)公開的共同世界”。其中“共同”有來源于共同之基礎(chǔ)的意思,這與洞穴內(nèi)部囚徒們有著共同的經(jīng)驗(yàn)來源的事實(shí)相似。
參考文獻(xiàn)
[1]柏拉圖,郭斌,張竹明,譯.理想國[M].北京:商務(wù)出版社,2017.
[2]汪靜.西方“公共領(lǐng)域”思想的歷史考察[J].載于《新聞傳播》,2014(03).
[3]柏拉圖,吳飛譯.蘇格拉底的申辯[M].華夏出版社,2007.
[4]陳志偉.哲學(xué)與政治:柏拉圖《理想國》的一種新的解釋視閾[D].陜西師范大學(xué),2005.
作者簡介
吳憲(1996—),男,漢族,河北人,西南民族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院外國哲學(xué)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哲學(xué)史。
西南民族大學(xué)? 四川? 成都? 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