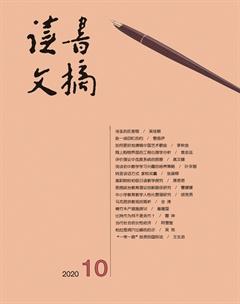近十年國內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文獻綜述
張燕 胡淋娟
1引言
民族語言指的是一個民族的人們在生產、生活中,彼此交流思想感情、交往聯系時所使用的語言。民族語言既包括了一個國家使用范圍最廣的主體民族語言,又包括了該國所有其他的少數民族語言,以及由這兩類語言演化而來的地方變體,方言。近十年國內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繁榮發展,取得了不錯的研究成果。國外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語言復興、瀕危語言保護項目、語言政策等方面。國內學者主要對瀕危語言、少數民族語言(方言)、漢語方言的保護和傳承、華僑的漢語傳承以及語保工程等內容進行了研究。本文將根據知網上近十年有關國內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幾十篇文獻,結合國內外研究的相關背景,總結和分析國內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現狀,以期為該領域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2國內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背景
國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孕育階段和探索發展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國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研究的孕育階段,這個階段只有一些有關瀕危語言的零星研究(徐世漩&廖喬靖,2003)。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是國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研究的探索發展階段,隨著瀕危研究的深入,語言瀕危現象的嚴峻性和普遍性日益暴露,除了語言學界,聯合國和其他國家組織,以及各國政府等都開始關注語言瀕危現象,并且采取一定措施保護和傳承民族語言(徐世漩&廖喬靖,2003)。
國內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深受國外相關政策和研究的影響,也開始于瀕危語言,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92—2003 年是瀕危語言研究的啟蒙和探索階段,國外引進的瀕危語言概念及相關研究逐漸得到國內語言學界和政府的理解和接受(范俊軍,2018)。2004—2014年是瀕危語言研究的繁榮和發展階段,國家給予了經濟支持并且出臺了很多切實的語言政策,如2010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明確規定“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權利”(范俊軍,2018)等。第三階段從 2015 年開始至今,國家政府啟動了“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簡稱“語保工程”),旨在對中國境內所有語言資源進行調查、保存、研究和開發(周慶生,2019)。
3國內外近十年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研究的內容
3.1國外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內容
近十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號召下,世界各國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已經全面展開,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語言復興、瀕危語言保護項目、語言政策等方面。在語言復興方面,研究者主要通過和相關社區合作,發起語言復興項目,如新西蘭毛利語復興、澳大利亞土著語言復興、巴基斯坦北部的語言復興等(杰拉德·羅謝 & 琳恩·辛頓 & 萊納·胡斯,2019)。在瀕危語言保護項目方面,國外研究者幫助成立了很多瀕危語言保護項目,如歐洲瀕危語言記錄項目、瀕危語言項目、語言記錄和保存項目等,而且這些都是以目標導向來管理、運營和實施的,這樣使得項目實施更加明晰化,但是其中也存在規范不足等問題(袁丹&詹芳瓊,2017)。在語言政策方面,研究者們主要研究的是語言政策理論與實踐、語言政策多元化、民族志與語言教育政策、語言政策評估體系等內容(賈連慶,2019)。
3.2國內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內容
3.2.1國內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理論研究
國內近十年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理論研究數量非常多,內容主要涉及了瀕危語言的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語保工程”研究、漢語方言的保護和傳承以及華僑的漢語傳承五個方面,其中有關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是最多的,而研究漢語方言保護和傳承的文獻是最少的。
目前,國內學者對瀕危語言保護和傳承的研究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研究國外的相關成果,通過借鑒國外的研究理論和對比國內外瀕危語言的研究現狀,為國內瀕危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的保護和傳承提出新的見解,如提高少數民族語言自救深層覺悟、完善語言文化多元并立格局、制定法律法規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等(何麗,2014;田有蘭,2013;)。第二條路徑是分析國內的語言現狀并提出對策,如史春穎(2020)根據國內瀕危語言赫哲語保護和傳承的現狀,提出國家進一步扶持、語言文化環境建設、跨境民族的溝通與交流等新的語言保護對策。也有部分學者從“互聯網+”、“多元一體”和文化傳承等不同的角度對國內瀕危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和傳承提出建立“互聯網+瀕危少數民族語言”的共享平臺、語言博物館、瀕危語言文化傳承人制度等新的保護路徑(肖榮欽,2013;吳坤湖,2016;劉祥友,2017)。總的來看,對于瀕危語言的保護和傳承,研究者們已經有了共識,首先要記錄和保存瀕危語言,其次是根據語言瀕危的真實情況,從雙語教育、語言環境、法律法規、傳承人培養、現代化技術以及國外經驗等方面保護和傳承瀕危語言。
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是研究者們重點關注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呈現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兩種趨勢。在宏觀上,研究者們重點分析整個少數民族語言的現狀,并針對這一現狀提出相應的策略。例如,部分研究者在分析了少數民族語言的現狀后,從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語文媒體、語言生態學、國際文化競爭背景、數字化保護、“社會轉型期”背景、英語全球化背景以及文字立法等方面,對少數民族語言保護提出了樹立民族語言文化觀、營造少數民族語言使用環境、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進行立法保護等可行的建議(肖建飛&劉海春,2011;高紅娜,2015;楊菁,2019;張靜&李醉海,2018;吳娟娟&唐軍,2018;郭建華,2018;張濤,2019;左廣明,2018)。也有部分研究者從宏觀上對比分析了國內外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差異,提出國內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應依據當下語言生態進行“科學保護”,尊重語言、文化多元化,大力發展民族語言教育等建議(哈正利&楊佳琦,2012;何山華,2019;周靈霞,2019)。在微觀上面,研究者們重點研究某些少數民族群體的語言現狀和相應的保護措施,比如研究跨境壯語、古苗疆走廊民族語言、民族雜居區民族語言、朝鮮族語言以及彝族語言等,通過對這些特殊的少數民族語言群體的語言情況進行分析,他們針對性地提出了擴展少數民族語言使用功能、培養少數民族語言傳承人、少數民族語言與旅游業相結合等保護對策(駱牛牛,2015;李秀華,2019;李蕊,2016;吳畏,2018;張靜,2016)。
關于“語保工程”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們主要闡釋了與“語保工程”相關的基礎性問題,如指出了“語保工程”的定位是國家工程、社會化、科學性,目標是調查、保存、研究、開發語言資源,任務是中國語言資源調查、中國語言資源平臺建設、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國語言資源開發應用等內容(田立新,2015;曹志耘,2015;周慶生,2020;王春玲,2018)。還有部分研究者則是從語保工程的實踐出發,根據已經開展的語保工作對其進行反思,提出新的語保措施,如戴慶廈(2017)通過對五年語保工作的分析,總結出了語保工作待解決的問題,成功的經驗,取得的成績等。再如李小萍(2016)對“語保工程”所對應的語言保護觀進行分析,指出中國的語言保護觀經歷了“語言文化遺產保護”和“語言資源保護”兩個階段,即保護的關注點從語言的人文性發展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兼顧。這些研究者從理論構建和實踐運用兩方面對“語保工程”進行研究,推動了“語保工程”的進一步發展。
除此之外,還有個別研究者致力于華僑的漢語傳承以及漢語方言的保護和傳承問題。在華僑的漢語傳承方面,胡士云(2017)和王建勤(2017)分別對華僑的漢語傳承能力進行了研究,分析了華僑漢語傳承的優勢和不足,發現了華僑的漢語傳承還有助于漢語國際傳播。在漢語方言方面,任弘(2017)分析了中國臺灣地區語言文化的雜糅現象,提出有關語言文化雜糅的研究目前少有學者涉及,存在極大的研究價值。
從瀕危語言的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語保工程”研究、漢語方言的保護和傳承以及華僑的漢語傳承五個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近十年國內研究者們的研究集中在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和傳承上,尤其是一些瀕危和有瀕危趨勢的少數民族語言,這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漢語方言的研究。據調查,“在漢語方言中,廣大農村、偏遠地區的方言處于絕對弱勢狀態,其中如浙江九姓漁民方言、澳門土生粵方言以及各地的小方言島則已成為瀕危方言(田立新,2015)。”與此同時,研究中提及的關于華僑漢語傳承的問題,也值得更多學者給予關注。
3.2.2國內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實證研究
和理論研究相比,國內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的實證研究數量非常少,主要涉及的研究內容包括少數民族語言、瀕危少數民族語言和少數民族方言三個方面。在少數民族語言方面,研究者們結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分別調查分析了云南省麗江市華坪縣傈僳語、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華藏寺鎮和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馬克堂鎮藏語的語言使用情況,發現通過創造普通話和少數民族語言良性互動的生態環境,可以同時進行推普和少數民族語言保護工作(姚春林&賈海霞,2016;嚴珺&王國旭,2019)。也有個別研究者通過定量和定性結合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描寫和分析了較少族群瑪麗瑪薩人母語的現狀及語言生活,發現他們的母語在多語環境中穩定發展,且和其他語言和諧共存(和智利,2015)。這表明使用人數較少的族群語言,即便處于強勢語言包圍的大環境下,也不一定都會走向瀕危。在瀕危少數民族語言方面,龍海燕(2013)通過實地調查,結合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貴陽市郊瀕危的少數民族語言布依族語言的使用情況,并進一步分析了它的語言現狀、保護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在少數民族方言方面,王艷和張雨江(2018)同樣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結合定量和定性分析對鎮沅苦聰話與補遠基諾語的使用情況進行了研究,發現這兩種方言都有衰退跡象,而且他們也結合衰退原因對這兩種方言的保護提供了對策。
從上述實證研究中可以發現,這些研究采用的都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的研究方法,主要通過田野調查、訪談、文獻查閱的方式收集特定地區的某個少數民族語言的數據進行分析。而且實證研究也表明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語言使用情況存在差異,這也提醒了研究者們民族語言的保護和傳承要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具體使用情況來開展工作。
4結論和反思
根據上述文獻可以發現,一方面相比國外的相關研究,近十年國內研究雖然在語言保護項目和語言政策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瀕危語言復興研究在中國國內依然未被重視(何麗,2014),這一領域有待更多學者關注。另一方面從國內研究來看,國內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主要從兩個層面開展,一是借鑒國外經驗或者根據中國國情研究宏觀的語言現狀和語言政策,二是對某一民族語言或語言群進行微觀研究,這時多采用田野調查、訪談、文獻查閱等方式收集數據。其中以宏觀研究為主,重點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很少關注方言。因此,國內民族語言保護和傳承研究在微觀方面,尤其民族語言方言的微觀研究方面,還存在很大不足,有待進一步加強。
參考文獻
[1]曹志耘.關于語保工程和語保工作的幾個問題[J].語言戰略研究,2017,2(04):11-16.
[2]曹志耘.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定位、目標與任務[J].語言文字應用,2015(04):10-17.
[3]戴慶廈.“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理論與實踐——“語言保護”實施后的五年回顧[J].貴州民族研究,2017,38(02):185-188.
[4]丁文樓.雙語教育:“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根本途徑--以“本溪模式”滿語教學為例[J].滿族研究,2017(02):1-5.
[5]范俊軍.中國的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0(10):1-18.
云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