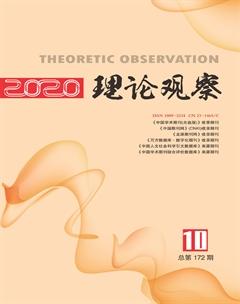《紅樓夢》里的“循環圈”
陳展
摘 要:《紅樓夢》的敘事時間整體上采取“編年體”,而在“編年體”之上,是以一個個的“循環圈”為時間單位。曹雪芹不僅用“循環圈”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還用它組織起龐大的人物、故事,以表達自己的人生體驗與思考。同時,“循環圈”還作為小說重要的時間意象,反復、多次地受到不同層面、不同角度的渲染、照應、強調,從而形成圈里套圈、圈外有圈、圈圈相套的嵌套結構。這些大大小小的循環圈,在《紅樓夢》中承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因而也就構成循環圈的多重意蘊,使得紅樓故事寓意深深、耐人回味。
關鍵詞:紅樓夢;時間;循環;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0)10 — 0142 — 03
“曹雪芹比較徹底地突破了中國古代小說單線結構的方式,采取了多條線索齊頭并進、交相連結而又互相制約的網狀結構。青埂峰下的頑石由一僧一道攜入紅塵,經歷了人間的悲歡離合,又由一僧一道攜歸青埂峰下,這在全書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契合天地循環的、圓形的結構。”①這個“契合天地循環的、圓形的結構”是否是《紅樓夢》的結構尚有待研究,但它確實揭示出《紅樓夢》時間運行的基本形式與特點。
中國古代小說常依據“時間循環”來組織敘事。雖然這種形式大致相同,但其組織形式與承載的文化內涵卻各不相同。《西游記》中師徒四人在取經路上遇到種種磨難,磨難往往被安排為“遇險——排難——再遇險——再排難”的模式,形成大大小小的循環圈。但這一連串的循環圈是取經人百折不回意志的象征,也是“八十一難”的具象。再進一步來看,唐僧前世本為如來的第二個徒弟金蟬子,因不聽如來說法以及對佛法持輕慢之態,被貶下凡轉生為唐僧,必須經歷西天取經途中的八十一難才能即身為佛。這也是一個循環圈,對應著佛法的圓滿與不可輕慢。《三國演義》也存在著循環圈,作者還在文中點明,這樣的循環將無休止重復下去,有道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古代歷史意識的外化。《紅樓夢》也劃出了一個大圈:無材補天的頑石凡心偶熾,請一僧一道攜入凡間,在塵世中歷劫一番后又由一僧一道帶回到原處。而在這個大循環的內外又生出大大小小的循環圈來,使《紅樓夢》比其他幾部小說的意蘊更豐富,更具文化意味。
一、“循環圈”的特征
《紅樓夢》在“天人合一”時空觀的觀照下,寫神界時間以“幾世幾劫”為單位,寫塵世時間以“日”為單位。它以一個個日子構成一個個集合元,以一個個集合元構成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環,以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環構成“編年體”,而在“編年體”之上,還有宏觀的“循環圈”關照著。
《紅樓夢》時間與空間的設置都以大荒山為起點,亦為終點。曹雪芹把石頭安放在女媧補天的創世紀時期的大荒山下,讓它通靈,然后讓它在仙境和塵世了走了一遭,最后又讓它回到了原來的起點。這個循環圈“以終為始,以終為始”的特征,表現出中國文化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趨向。
在中華文化中,表現出“循環”思想的,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周易》認為,“一陰一陽,謂之道”,世間萬事萬物都是由矛盾著的雙方對立、轉化的結果。它以陰、陽兩種元素的對立統一去描述世間萬物的變化,認為世界是在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下衍生著、發展著、變化著。而陰陽相互依存、互相轉化是一個動態過程,這一動態過程伴隨事物終身,并決定著事物的發展進程。《周易》以陰陽彼此轉化、融合的過程,架構起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宇宙;生命彼此“互化”,呈現出生生不息的運演節律,同時為自然天地提供了多樣、繁復、循環及演化的可能。至老子,他將《易經》的思想精華融入《道德經》,構造了一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萬物起源圖式,提出了“有無”這對重要的基本概念。“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兩者相反相成,就是“道”,而“道”就是對立面的矛盾、統一與超越。“道”從無至有地創生萬物,萬物又從有而復歸于無。任何事物都要經由“無—有—無”和“有—無—有”這個對立、統一且得到升華的運動循環過程。
此外,曹雪芹還借用“轉世”這一形式,構成時間循環的結構。在中國古代神話中就有轉世的思想。釋家講因果報應。因果是循環的、往復的,是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今世果乃前世因,今世因造來世果。正是業因的不同,于是眾生在六道輪回中生生死死、來去往復,猶如車輪的回旋,在這六道中周而復始、無有出期。道教則認為,人應修性守道、清靜寡欲,才能返樸歸真、與道同體。
《紅樓夢》中循環圈“以始為終,以終為始”的特點,深層反映的正是《周易》《道德經》中多樣統一、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的創生思想,老子“以無為有”“有無相生”的思想,以及釋道兩家的輪回轉世說。
《紅樓夢》時間上的這種循環圈,在神界與塵世兩個不同的空間中展開,這是“循環圈”的第二個特征。
從敘事文本來看,開篇的“女蝸氏補天之時”與“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是個共時性的結構,它們在時間上超越了歷史,在空間上超脫出塵世。作者在此便交代了整個故事的緣起與歸宿,但同時又由石頭上的記錄回溯到故事最開始、故事本身的演繹。如此,小說呈現出的時間循環,是個首尾相銜的圓圈。從故事的整體來看,石頭在塵世的一番歷劫,則集中表現在賈府興衰輪回之中。也就是說,神界中的輪回包融著塵世的輪回,紅樓故事的循環圈在神界與塵世兩個不同空間中各自展開又相互交匯。雖然曹雪芹寫神界與塵世的輕重、疏密、詳略有別,但二者之間并沒有偏廢。塵世敘事為故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亦是小說最動人的部分;而神界敘事又為現實敘事錦上添花、畫龍點睛,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神話與現實、寫意與寫實并置共生,經驗世界與外部世界彼此呼應。
這種安排暗合“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的內在秩序。石頭下凡歷劫,從無材補天的一塊頑石演化為“神”(神瑛侍者),“神”托身入世,又演化出“人”(賈寶玉)和“玉”(通靈寶玉)。曹雪芹所要表達的就是“物”進化為“神”,“神”進化為“人”,“人”進化為一個力圖擺脫一切外在束縛以求獲得精神超越、獨立、自由,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意義上的“人”的故事。①
石頭不但進入大循環,它還在不同的循環圈中流轉,在循環圈之間互動著。這是《紅樓夢》循環圈的第三個特點。在賈府最熱鬧的時候,石頭曾想起自己在大荒山受苦之時;在賈寶玉試才題匾額時,曾想起自己見過的“洞天福地”;在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時,在他人生剛剛起步之時,就以夢幻的形式與他還無法領悟的人生終局打了一個照面,“形成人與天、人與情欲、后代與祖先、現實與命運的多重對話”②,呈現出天、地、人之間生動奇妙的互動和連通。
二、“循環圈”的結構方式
循環圈作為小說重要的時間意象,反復、多次地受到不同層面、不同角度的渲染,形成大大小小、互相印證的循環圈。從石頭循環的本身來看,它經歷不知“幾世幾劫”之后又回到了原處,這個循環圈因強調的重點不同,也就形成了種種復合的意象,多了種種言外之意。如,強調石頭從大荒山下凡歷劫后又回歸大荒山,強調石頭離開青埂峰又回歸青埂峰,強調石頭出于太虛又回歸太虛,因側重點不同,人們就對這些循環圈有了不同的釋義和解讀。
首尾照應的強化,是實現《紅樓夢》循環圈的又一運行方式。正如一僧一道所告誡的那樣:“那紅塵中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持,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究競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③與石頭最后的回歸相照應,而這種照應在故事的首尾不斷得到強化。在第116回中,賈寶玉又重游太虛幻境,再次看到身邊眾人物命運的判詞,與第一次神游幻境亦形成照應,從“不悟”到“悟”。這種照應在《紅樓夢》中,不斷通過各種藝術方式得到強化,使得“循環圈”的文化意蘊也不斷得到突顯和強調。
如此,循環圈形成了環環相套的嵌套結構。所謂嵌套結構,指的是一環套一環的復雜的敘事結構。浩浩茫茫的大荒山既是紅樓故事的起源與開始,也是最后的歸宿與結束。有學者認為,“在元故事層面,我們所感受到的不僅是大荒山、無稽崖這地老天荒的‘無限空間,同時也感受到了循環往復、永劫永世的‘永恒時間”,“它的敘述‘時序是非線性的、反復周旋的——既是完全的‘倒敘,又是全面的‘預敘,更是循環往復、徹頭徹尾的‘順敘。”④確是如此,它是“全天候”的,又是“無時間”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在敘述的過程中不斷回旋、往復,一個個循環圈圈里套圈、圈外有圈、圈圈相套,賦予了紅樓故事不盡的意味。
《紅樓夢》最重要的循環圈,就是作者構想了由神降世為人,又由人復歸為神的生命歷程。在這個循環圈里,既有頑石被僧道攜著到紅塵世界經歷一番,又在“幾世幾劫”之后回到了原點;也有隨神瑛侍者下凡的這一干情鬼,按警幻仙子的安排走完紅塵。她們來自“太虛幻境”,在紅塵歷劫之后又復歸“太虛幻境”;還有絳珠仙草為了神瑛侍者而下凡報恩,最后淚盡而逝。這一個個循環圈相互共存。以上這些循環圈又都鑲嵌在賈府“樹倒瑚孫散”這個現實層面的循環圈里,鑲嵌賈府“成”“住”“毀”“壞”的大循環中,鑲嵌在流動的四季循環結構中,鑲嵌在《紅樓夢》的編年紀事里。
三、“循環圈”的文化內涵
《紅樓夢》的這些循環圈承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因而也就構成循環圈的多重意蘊。
《紅樓夢》敘事采取“循環圈”的形式,這本身也隱含著對人生、生命的傷懷。循環圈自身作為時間意象,在組織龐大的人物、情節時,也就寄寓著種種情懷。“‘四時循環所引發的節候感應,進一步將古代小說敘事‘悲天憫時情懷突顯出來;宿命化的‘時運觀,也形成了定向性與突轉性的意態化敘事構架。”①這里的“四時循環”與“宿命化的‘時運觀”實質上就是本文所說的眾多循環圈之一。
曹雪芹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與思想的熏陶,他借循環圈寄寓著他關于自己一生經歷的體驗與感悟,寫出他對人的存在的終極關懷。作者以一個超驗的空間作人生的本源,又以復歸這個超驗空間為人生的歸宿。作者把對“在生”的體味建立在超越于“在生”的基礎之上,將生命流程置于“形而上”的觀照中,消解了單一的時間鏈,因此對紅樓故事的解讀就帶有“頭即是尾,尾即是頭”的感觀。
但《紅樓夢》呈現出來的循環圈并不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思想,石頭入世前和入世后是不一樣的:“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②。作者通過循環的時間意識表現出循環的無窮性與生命的一次性的矛盾,從而消解了時間的虛無。就宇宙時空來說,時間的循環是一定的、必然的,它無始無終、無窮無盡、周而復始;但作為個體的生命,卻是一次性的。《紅樓夢》一開始就揭示了其悲劇的結局,時刻提醒著個體生命的一次性,并且隨著這種有限時間的流逝,也就越來越逼近那個悲劇的結局。正是如此,在不得不走向那個悲劇結局時,充溢在《紅樓夢》的字里行間的是無窮的眷戀和無奈。賈寶玉希望這種在大觀園內與眾女孩們的美好的生活能一直持續下去,但人世間的一切都是短暫的,寶玉在賈府,也只生活了19年。現時的歡樂和幸福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消逝,時光卻仍處在不斷的周流循環中。在無始無終的線性流動中,作為個體的生命,無論真的、假的、好的、壞的、美的、丑的,都是無可挽回的、一次性的。
《紅樓夢》的整體悲劇性,也就來自于此,就像人一生下來就要奔向死。但曹雪芹并沒有把“最終的死”和“最初的生”簡單等同起來,他希望能站在一個高度來重新認識生命的過程。這也就是空空道人所說的“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也就是曹雪芹所說的“味”。
在紅樓故事中,曹雪芹不僅僅給予了“色空”以自己的體悟,還在“色空”之間加入了一個“情”字。“情”作為“色”“空”轉化的中介,是極其重要的。可以說,石頭的故事蘊含的最具價值的人生哲理,就在于其對于“情”的命題的引入。《紅樓夢》開篇說到此書的來歷有一個人物不可忽視——“情僧”。按一般理解,佛教是無情哲學,根本否定自我情感,但曹雪芹卻特意設置了一個“情僧”。這看起來異常矛盾的稱呼,體現了作者的“情”觀。《紅樓夢》中曾提到南宗六祖慧能。六祖惠提出了“無情無佛種”的新佛性本體論,強調“心地含情種,法雨即花生,自吾(悟)花情種,菩提果自成”。這就說明,“佛種”亦可含“情種”,“情種”也可證得菩提。這種以本心至高無上以及大膽的懷疑精神和鮮明的自我解放,意圖打破一切形式的束縛,正是曹雪芹一生的追求。所以,在作者眼里“情僧”也是寶玉情感成長腳步的終點。
受到這種佛家色空觀念的影響,曹雪芹仍將生命的流向一語道盡:“萬境歸空”。佛教認為,萬事萬物不斷的運動、變化,經歷著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最終都會消融殆盡,隨之又重新開始,周而復始,無限循環。經歷了這個過程后,這個“空”已經飽含了人生或生命的存在與價值。正是如此,石頭即使在明知道“萬境歸空”的宿命,但還是想去到凡塵經歷一番;回歸之后,石頭將其所見所聞記在身上。這里不是終結,而且新循環的開始——石頭的故事最后由曹雪芹整理成冊,還通過小說的多重書名和書后題詩,對無數讀者表達了他對下一輪“循環”的期望——解得其中味。劉再復先生在談到《紅樓夢》的“空”時提出,悟“空”產生力量。或許這就是為什么讀《紅樓夢》不僅不會消沉,反而會積極面對當下的人生,從中獲得力量。
人們意識到或者談到《紅樓夢》時間敘事的循環時,一般認為,這是由于曹雪芹還不可能正確解釋整個歷史的發展規律、看不到社會出路的緣故。或許會有這方面的原因,但從中國古代小說的時間敘事傳統來看,時間不僅僅是一種自然時序的現象,而且還承載著厚重的文化意味,形成中國特有的“有意味的形式”。《紅樓夢》的循環圈像一個盤旋而上的寶塔,它下端緊貼現實,上端高居空中。因緊貼現實而被譽為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有意于終極關懷則被有人尊之為“中國的《存在與時間》”。
〔責任編輯:楊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