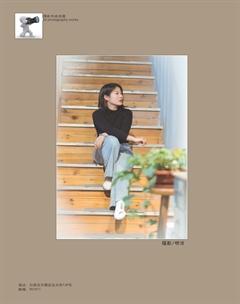從立法的角度論證正義高于律法
【摘要】從蘇格拉底和希皮阿斯的對話中可以看出,在蘇格拉底那里,律法是高于正義的。文章從立法的兩個不同層面探討在蘇格拉底心里正義高于律法的理由。
【關鍵詞】蘇格拉底 正義 律法
一、立法者的正義
在《回憶蘇格拉底》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希皮阿斯”,蘇格拉底問道,“你知道什么是不成文法嗎?”
“那是到處都一致遵守的律法。”
“那末”,蘇格拉底問道,“你能說這些律法是人類為自己制定的嗎?”
“那怎么能呢?”希皮阿斯回答道,“因為人類是不可能都聚集到一起的,而且也不是都說同一種語言啊”。
“那末,你想這些律法是誰制定的呢?”蘇格拉底問。
“我想”,希皮阿斯回答道,“這些律法是神明為人類制定的,因為所有的人類都以敬畏神為第一條律法”。
在這段對話中,蘇格拉底借希皮阿斯之口說出了自己對于一部正義的法律的理解:這樣的法律應該是由神明來制定的,而不是由人類自己制定,所以蘇格拉底認為,神明才是法律的最高決策者和制定者,而城邦的領導者只不過是神明旨意的傳遞者和執行者。那么什么樣的人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者即城邦的直接立法者呢?而作為間接立法者的神明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蘇格拉底在與色拉敘馬霍斯的談話中曾經說過一個城邦的統治者應該是那些利用自己統治的藝術為弱者的得益而操心,想盡辦法為他們謀得利益的人,他們是那些糾正邪惡的正義之人。 只有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視知識為報酬,愛智慧高于追名逐利的哲人才應該是一個城邦的統治者,才有資格是城邦律法的直接制定者。可見,蘇格拉底所說的“守法就是正義”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的,那就是所遵守的法律是由一個正義的統治者制定的,這一點在本章的開頭也可以看出:當三十僭主命令他做違背法律的事的時候,他曾拒絕服從他們, 可見在蘇格拉底的心中,由“不正義”的僭主所制定的“命令”并不是他所說的應該遵守的法律,不是所謂的正義。
那么同樣,在這里蘇格拉底所說的神明,或許并不是一個類似《圣經》中那樣會去懲罰自己最忠實的奴仆、最謹守圣法的臣民的這樣一個“不正義”的上帝,而是一個充滿善良事物的神祇——“邪惡的事物應該在別處尋求,不應涉及神”。而這樣的神靈是存在于人的肉體之上的,是管教著每個人的靈魂中的神明,每個人從兒童時期就開始接受一定程度上的管教,直到身上培養了一種與國家憲法差不多的原則之后,才能給予他們自由,那么這種存在于每個人靈魂之中的神明是不是就是一種原則的精神存在?這種原則性的存在是超越語言、超越民族、甚至超越歷史的,就像孝敬父母、近親不得結婚以及以德報德等這種原則性的法律在當今的社會仍然適用,這些東西經過歷史的沉淀,一步步演變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不成文規定,成為人類生活中的習慣法,它應當是現今法律社會中最重要的法律淵源,而不應該被立法者所摒棄。今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十條——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將習慣法正式寫入了我國處理民事法律關系的原則性規定當中,將其上升為法律的正式淵源,不可不謂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
二、所立律法的正義
在蘇格拉底的步步引導之下,希皮阿斯對于法律有了不一樣的認識,原文的對話是這樣描述的:
“的確,蘇格拉底”,希皮阿斯說道,“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是由神來的,因為在我看來,凡是其本身就給違犯的人帶來刑罰的律法,一定是由比人更好的立法者所制定的”。
“那末,希皮阿斯,你以為正義的律法和非正義的律法哪一個是由神所制定的呢?”
“非正義的律法當然不是由神所指定的”,希皮阿斯回答,“因為如果神不制定正義的律法就很難有什么別的人制定這樣的律法”。
在這個章節的最后,希皮阿斯終于明白一部正義的法律除了由正義的立法者來制定之外,其法律本身也應該是正義的,只有那些其本身就給違犯的人帶來刑罰的律法才是一部好的法律,才是那個應當遵守的正義的法律。就像本章提到的“以德報德”這條法律,用美德去回報別人對你的恩惠,那你結交到的朋友也是一個“美德”的人、一個善待你的人,這對你來說也是有極大的好處的。 也就是說,你所制定出來的法律,人們去遵守它是可以給自己本身帶來好處的,這樣人們才會愿意主動地、從內心地去服從它、遵守它甚至去維護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了危險駕駛罪,禁止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這樣的一條法律規定不僅保護了行人也使駕駛者自己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其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是守法者本身,我想這也是此條法律自實施以來效果顯著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是否可以把蘇格拉底在這里所說的法律上升到一個更為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僅是指狹義上的法律條文,而更是一個用于國民教育、引導公眾思想的讀物或者說是教材這樣的一種東西?蘇格拉底曾經在和阿德曼托斯的對話中提到過,他認為應該將那些邪惡的、非善的東西從詩歌、神話故事中“一掃而光”,而只留下那些“思想道德的楷模”和正義的東西,同時,作為城邦的統治者還應當建立一個檢查制度,對那些用于教育的讀物、教材進行審查,保證只留下一些好的東西、善的東西、正義的東西。也就是說在經過層層篩選之后,所流傳在人民群眾當中的“法律”已經是一個至善至美、純凈的、充滿正義的東西了,你去遵守的是這樣一部正義的法律,那么理所當然,你這樣的一個“守法”行為也就是正義的了。
參考文獻:
[1]劉小楓.王制要義[M].張映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2]色諾芬.會議蘇格拉底[M].吳永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3]馮象.信與忘:約伯福音及其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作者簡介:王雨璐(1995-),女,浙江衢州人,上海大學法學院2017級民商法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