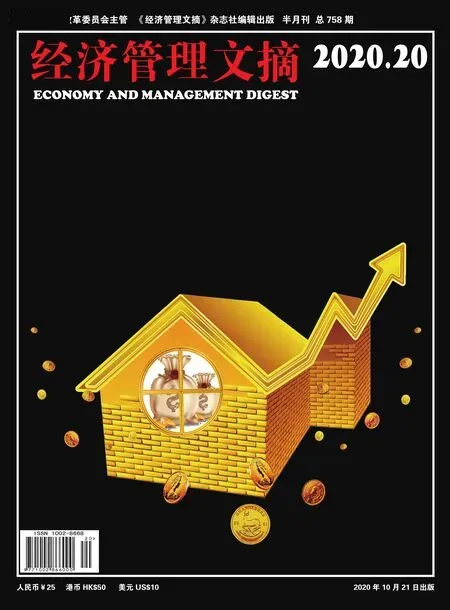銀行業金融精準扶貧機制構建的思考
——以商洛市商州區為例
■吳 剛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1 引 言
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勝之年,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從2012年年底的9899萬人減少至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以上。到2020年2月底,全國832個貧困縣中有601個實現脫貧摘帽,179個正在進行退出檢查,未摘帽縣還有52個,區域性整體貧困基本得到解決。
商洛市商州區位于陜西省東南部,秦嶺東段南麓,丹江上游,東西長67.5公里,南北寬65公里,橫跨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總面積2672平方公里。全區轄4個街道辦事處,14個鎮,總人口56萬,2019年末實現生產總值156.75億元。2017年精準識別后,全區建檔立卡貧困戶3.17萬戶,貧困人口10.35萬人,貧困村124個。經過脫貧攻堅工作,2020年2月商州區實現整區脫貧摘帽,截止2020年4月末剩余未脫貧貧困戶2875戶4646人,均為低保、五保等兜底保障戶。商州區屬于西部省份山區腹地,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經濟活躍程度較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存在一定差距。
現階段扶貧工作取得一定成績,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精準扶貧具有“金融”、“精準”特質,深化貧困地區的金融供給,解決脫貧過程中的資金需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銀行業金融機構如何在“精準”幫扶上精準發力,有效發揮人力、財力、物力作用,找準銀行業商業效益與風險控制的平衡點,是實現銀行業金融機構為貧困地區持續供給金融資源的關鍵。
2 商州區銀行業金融扶貧現狀
2019年末,全國金融精準扶貧貸款余額3.96萬億元,較年初增加3403億元。全國性銀行中余額最大的3家為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農業銀行,增量最多的3家銀行為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農業銀行。商州區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包含工、農、中、建、郵儲五大國有銀行,也有長安銀行、西安銀行等城市商業銀行,還有深入基層鄉鎮的農村信用合作社。2016年6月至2020年4月末,累計發放14474筆精準扶貧貸款,累計發放金額人民幣47394.4萬元,存量貸款8234筆,精準扶貧貸款余額人民幣24531.11萬元,截止2020年4月末,扶貧小額信貸逾期貸款22戶59萬元,逾期率0.7%。為激活金融精準扶貧內生動力,商州區重點做了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表1 商州區銀行業精準扶貧工作匯總
3 銀行業金融機構精準扶貧面臨的困境
3.1 “三農”視角
秦嶺山區農業產業發展難度大。商州區種植農產品主要包括食用菌、核桃、玉米、小麥、土豆等,養殖以生豬、蛋雞、蜂蜜為主,也有種植中草藥的傳統,但大多以農戶個體為單元進行耕種,農產品選擇余地較小,種養殖隨意性較大。受地區自然條件制約,難以實現機械種養殖,規模化程度低,缺乏抵御自然災害、價格波動等風險的手段。近年來商州區大力推廣食用菌產業,成立國有食用菌生產企業,每年分紅為貧困戶,但該類企業具有一定的“補貼性”,區域內具有現代企業管理運作模式的涉農企業、農產品深加工企業較少。
農村金融環境基礎薄弱。經實地調研,秦嶺山區貧困群眾對金融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存款、貸款等傳統銀行業務上,貧困戶擔憂貸款加重家庭負擔,且大多青壯勞動力外出務工,留守為老人及兒童,缺乏發展產業意愿,沒有主動承擔產業發展經濟杠桿的意愿。其次,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缺乏,農村生活容易自給自足,較城市生活違約成本低,長期的金融信用認知缺乏,導致貧困戶對建立自身良好信用數據未形成統一認識。
貧困戶認識上存在誤區。貧困很大程度上是“智”和“志”的缺失,由于貧困地區金融知識傳播及培訓不足,部分扶貧貸款主體仍存在有政府“兜底買單”的思想,可以不還或者延期歸還,即便最終不能償還,政府會幫忙歸還的錯誤認識;還有部分貧困戶獲得金融扶貧貼息貸款后,沒有用于發展產業,挪作他用,影響銀行業金融機構向貧困戶發放貸款的積極性,長期來看透支了貧困農戶的信譽,也制約著金融資源的流動。
3.2 銀行業金融機構視角
銀行業金融機構由于業務發展側重及風險偏好不同,與農業、農村、農民的金融需求尚未完全有效銜接,而主要面向“三農”的農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郵儲銀行等金融機構雖具備一定規模,輻射了大部分農村地區,但與貧困農村地區的金融需求相比,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金融精準扶貧對象包括貧困地區的個體農戶、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小微企業,貸款具有金額小、周期性等特點。一方面,農業生產投入大、周期長,生產收益不能立即兌現,而自然災害、價格波動、生產成本等因素極易導致虧損,貧困山區的自然稟賦條件,又制約著貧困地區農戶及中小微經營主體的創收能力,金融扶貧貸款風險高;另一方面,貧困地區經濟基礎薄弱,貧困家庭及經營主體無可用于抵押擔保的不動產或其他權證,銀行業金融機構對于此類情況缺乏專門的認定辦法及評估措施,同時缺乏涉農擔保機構為貸款主體提供增信措施,導致貧困人口及經營主體無法獲得精準扶貧貸款。
發展的根本在于人,除農業銀行等服務“三農”的銀行業機構外,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輻射及主要服務客戶集中在省會城市、中心城市,現有金融從業人員對農村金融需求的特點不熟悉,扶貧貸款審批標準、發放流程等與需求未能有效匹配。面對扶貧不良貸款,銀行業金融機構風險預警、管控、處置手段尚顯不足。可持續性精準幫扶的“中小企業(合作社)+農戶”模式尚在探索之中,銀行業涉農、扶貧貸款的發放,依賴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政府等監管部門的信貸窗口指導,精準幫扶的主觀能動性不足。
3.3 外部視角
銀行業金融機構是按照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成立的企業,其屬性決定其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經營目標。經營目標決定銀行會選擇性地運營金融資源,在考量風險后,注重綜合貢獻度較高的目標群體。而金融精準扶貧面向貧困地區農戶及涉農經營主體,經營信貸資產風險高,綜合定價因素后邊際收益小,使銀行業金融機構難以產生服務“三農”的內生動力。涉及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各級監管、政府部門存在多重管理,各部門均站在自身角度考慮問題,難以有效形成步調一致的決議行動。扶貧開發涉及多方協調協作,打贏脫貧攻堅戰離不開更高層面的頂層設計,不僅僅是銀行業的積極參與,有統一組織和相應制度支撐,金融扶貧資源方可形成合力。
4 銀行業金融精準扶貧有效開展的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解決好銀行業金融機構金融精準扶貧,離不開“三農”、銀行業及各個監管政府機構的共同努力,有效開展精準幫扶思路為“頂層設計,軟硬結合,有點有面”。
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4.1 加強頂層設計,護航脫貧攻堅
參與精準扶貧是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盡的社會責任,對精準扶貧工作進行頂層設計,有助于創新精準扶貧金融服務產品及風險控制措施,充分發揮金融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

圖1 金融精準扶貧路線圖
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與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機構協調,給予扶貧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傾斜,實現銀行業的商業可持續性,適當提高對貧困地區精準扶貧貸款的不良容忍度,調整貧困地區涉農涉貧金融業務業績任務考核,落實完善盡職免責和容錯糾錯機制,充分調動銀行業敢貸、愿貸積極性;統籌扶貧開發局、農業農村廳、民政廳、財政廳等政府職能部門的協同支持,深化戰略合作,共同推進金融精準扶貧機制的創新與完善、產品開發、考核評價等工作;發揮擔保、保險等類型機構在風險保障、風險緩釋、經濟補償方面的作用,形成“銀行+擔保+保險+三農”的風控構架,探索通過擔保、保險等分擔扶貧貸款風險,完善扶貧貸款風險保障。
4.2 加強金融“扶志扶智”,做好產業發展
金融“扶志扶智”助建農村信用體系。多渠道宣傳普及涉農金融知識,將金融征信與村規民約結合宣教,提高農民誠信意識,對騙貸、拖欠等不誠信或違法行為多維度防控,形成不誠信行為與農村生活掛鉤機制,提高違約生活成本,養成良好的誠信習慣。建立農村地區貧困戶、農戶、涉農企業、合作社等主體基礎信用和金融精準扶貧信息數據庫,打通人行征信與國辦、省市區脫貧攻堅數據庫的互聯互通,發揮人民銀行、銀保監局、扶貧局、工商、民政、稅務等部門和銀行業間的共享協作,實現對扶貧對象信用信息的動態管理。搭建多渠道、多層級的大數據平臺,做到信息共享,降低精準扶貧的風險防控成本,暢通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借助農村“三變”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通過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等主體運營發展,有效整合資源,化零為整,將零散的土地、人員等村級資源統一協調,按照現代企業運營管理,提高抵御農業生產周期性、經營性風險的能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依托“企業(合作社)+農戶”為農業產業經營主體和農戶提供幫扶貸款,發揮帶動作用,實現扶貧產業覆蓋到貧困人口,立足商州區農業、農村特色,帶動食用菌、光伏、中草藥、核桃、生豬、蛋雞、蜂蜜等種養殖產業,形成產業輻射到戶到人的精準扶持機制。
4.3 提升精準幫扶水平,實現可持續發展
充分發揮現有農業銀行、信用合作社、郵儲銀行等銀行業金融機構基礎作用的同時,完善貧困農村地區金融機構體系,鼓勵更多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到精準扶貧的隊伍中來。有能力的可以建立輻射區域的分支機構,沒有分支機構的通過網銀、手機銀行、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夯實基礎金融服務渠道基礎,更好地服務“三農”開展精準幫扶工作。
金融精準扶貧需從貧困地區實際出發,探索創新適合貧困鄉村特點的金融產品,提供差異化服務。銀行業金融機構可根據貧困戶種養殖、農產品加工等生產經營特點,提供免抵押、免擔保的小額信用貸款,靈活確定貸款金額、利率、期限,采取“授信總余額管控、借款隨借隨還”管理方式,提升貧困地區金融精準幫扶的服務質量;針對貧困戶缺乏抵押、擔保等風險緩釋情況,一方面成立專業涉農擔保公司,幫助銀行業金融機構做好金融服務,另一方面推進農村承包土地等抵押物價值認定,搭建適合農村的不動產抵押登記平臺建設,破解融資抵押難題;支持貧困地區致富能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用金融精準幫扶資金為貧困戶認領扶貧開發項目,如光伏發電等未來有穩定現金流支撐的產業,實現產業開發收益帶動貧困戶增收,切實覆蓋殘疾、孤兒、高齡等沒有勞動力的貧困個體,提高“兩不愁、三保障”脫貧實效。
實現銀行業金融機構商業經營的可持續,需嚴格把控、分散扶貧信貸風險。一方面針對扶貧信貸業務特點,重塑貧困地區授信主體信用評估體系,實時把控信貸風險,及時處置預警信號,對銀行業涉農業務人員開展專項培訓,提高金融精準扶貧業務的質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在沒有條件建立物理網點,但有業務或擬開展業務的地區,定期選派客戶經理進村入戶對接貧困戶金融需求,深入貧困地區涉農企業及幫扶開發項目,貼近農村金融市場,打通資金流入農村“毛細血管”的最后一公里,同時保證扶貧信貸資金合規有效使用,即實現精準幫扶目標,又兼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經營可持續性。
最后,金融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間節點,銀行業金融機構呈上“脫貧攻堅”,啟下“鄉村振興”,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自開展脫貧攻堅工作以來,我國銀行業精準扶貧實踐的時間不長,尚可在廣度與深度上繼續挖潛,通過監管、政府、銀行業金融機構等有關部門的共同探索、群策群力,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摸索完善,一定可以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夯實銀行業金融機構接續服務鄉村振興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