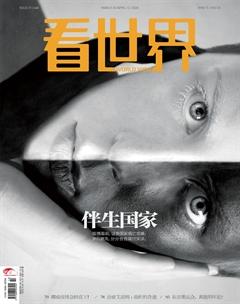印巴分治:揮不去的傷痛記憶

克什米爾仍然是印巴兩國的沖突焦點
今年1月正值印度共和國成立70周年。1947年,以宗教信仰為主要分界線,在原“英屬印度”地盤上相繼形成了兩個自治領—巴基斯坦自治領(覆蓋如今的孟加拉國領土)和印度自治領。兩個自治領分別于1956年3月23日和1950年1月26日宣布成立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印度共和國。
自獨立以來,印巴就因克什米爾等領土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三次爆發戰爭。即使20世紀90年代兩國都擁有了核武器,在邊境的擦槍走火也還是時有發生。2019年8月,印度莫迪政府宣布終止克什米爾地區的特殊憲法地位,再次刺激了巴基斯坦的神經,使得兩國劍拔弩張。
為何昔日同胞動不動就兵戎相見?兩國是否注定將一直走在爭斗的路上?這還要從殖民地時期國民大會黨(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穆盟)兩黨的斗爭說起。
宗教仇殺中的分治
同樣經歷過輝煌和落魄,同樣經受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印度教信徒在19世紀20-30年代就開始了啟蒙活動。而直到19世紀中期,曾拒絕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印度(1947年獨立前,均指“英屬印度”)穆斯林中,才開始了資產階級啟蒙活動。
穆斯林聯盟一方面想振興印度,另一方面也想促進穆斯林在印度的發展,而后者更是他們的重點目標。這一教派主義思想,為穆斯林與印度教信徒的斗爭埋下了伏筆。
隨著教派主義逐漸興起,穆斯林聯盟與國民大會黨在1934年中央立法會議選舉中的競爭,強化了印度穆斯林的斗爭心理。而在選舉中的劣勢地位,又加深了穆盟中教派主義勢力的不安。國大黨一方面在組織省政府時應許給予穆盟職位,另一方面也試圖控制穆盟勢力的擴大。這導致了穆盟認定遭國大黨排斥,從而號召印度全境的穆斯林抵制國大黨執政。

1944年9月,“穆盟”領導人真納(左)與印度國父甘地的合影
戰爭使得孟加拉國的獨立成為現實,印巴關系更加緊張。
英國人想通過穆盟,牽制要求印度獨立的主要力量國大黨,因而縱容著穆盟單獨建國的要求。不少印度穆斯林認為,自己與印度教信徒屬于不同民族—加上人數上處于劣勢—會受到印度教信徒的不斷排擠。在1940年3月拉合爾年會上,穆盟正式提出要單獨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的決定。這更激化了穆盟與國大黨之間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迫于國大黨、穆盟等領導的獨立斗爭的壓力,以及為了減少自身經濟利益受損,準備撤出印度。1946年3月,英國內閣使團抵達印度。這時的國大黨主張獨立后建立統一的聯邦國家,而穆盟依然堅持單獨建國。
5月,英國代表和印度的各黨派領導人在西姆拉召開會議,商討方案。雖然國大黨和穆盟均接受了英國提出的將印度分為三個“省集團”的方案,但穆盟只是將此方案作為過渡,依然未放棄單獨建國的目標。在臨時政府席位分配的問題上,國大黨與穆盟又出現了分歧。
在英國使團6月離開印度后,雙方矛盾更加激化。穆盟組織印度穆斯林開展斗爭,在雙方教派主義的挑動下,印度加爾各答、孟買等多個地區發生暴力沖突和仇殺,造成上萬人死亡。
而后,穆盟拒絕參加臨時政府的組建。國大黨則在英國的參與下,于9月成立了臨時政府。穆盟最初對此抵制,而后改變了態度,在10月加入了臨時政府,其成員還擔任了財政、商業、交通、衛生以及法律部部長等要職。盡管如此,穆盟依然沒有放棄單獨建國的目標,并與國大黨處處對立。為此,英國還邀請雙方在倫敦進行會談,但并沒有成效。
1947年2月,英國前東南亞盟軍最高統帥蒙巴頓擔任印度總督,與印度各方進行磋商。穆盟未對蒙巴頓提出的統一方案有任何妥協。為盡早實現獨立以及避免更大規模的流血沖突,尼赫魯和帕特爾等國大黨領導人只得接受分治。在印方人員參與下擬出的《蒙巴頓方案》,國大黨和穆盟等最終表示接受。此方案意味著印度以自治領形式接受英方移交政權,并實行印巴分治。
劃分國界之前,阿薩姆等地發生流血沖突。而在隨后的分治過程中,擔任土邦部部長的帕特爾主持制定方案,迅速解決了大多數土邦加入印度的問題。1947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印度獨立法》。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自治領和印度自治領分別宣告成立。在原英屬印度獨立的同時,印巴正式分治。
巴基斯坦因戰爭分裂
印巴分治雖然落下帷幕,但并沒有給兩個自治領帶來和平。
1947年9月,巴基斯坦部族武裝侵入克什米爾,一個月后宣布與當地的穆斯林成立自由克什米爾政府,并加入巴基斯坦。當時信仰印度教的克什米爾王公,隨即宣布克什米爾加入印度。印方應其請求,派兵支援。巴方也對部族武裝和克什米爾地區的穆斯林進行了增援,從而使得印巴陷入第一次戰爭。
印度在12月將克什米爾問題提交聯合國。1948年成立的聯合國印巴委員會提出通過停火、非軍事化、公民投票三步來解決糾紛。雙方在1949年才正式停火。

1999年5月31日,印度士兵從卡吉爾附近的哨所向克什米爾印巴邊界發射炮彈
這次騷亂余波未了,甚至在特朗普今年2月訪印期間還有惡化。
穆斯林在克什米爾地區占大多數,印度考慮公投對其不利,故而拖延執行。在1954年,印度支持克什米爾立憲議會通過了加入印度的議案,隨后宣布在克什米爾實行印度憲法。巴基斯坦對此堅決反對。
雙方在邊境摩擦不斷,第二次印巴戰爭于1965年8月爆發。在聯合國安理會調解和蘇聯的斡旋下,印巴總理于1966年在塔什干會談,簽署了《塔什干宣言》,但這只不過是暫時休戰。
在英屬印度末期,東孟加拉的穆斯林占該地人口大多數,在印巴分治時,東孟加拉被劃歸巴基斯坦,地理上稱為東巴基斯坦。東巴與西巴被印度從地理上隔開,且東巴的孟加拉人政黨一直覺得被伊斯蘭堡欺負,所贏得的全國大選勝利不被承認,于是在1971年3月宣布獨立,并在4月于印度加爾各答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隨后,東巴發生大規模動亂和難民潮。
這期間,巴基斯坦出兵鎮壓動亂。而11月、12月,印度軍隊分別向東巴和西巴發起進攻,導致印巴第三次戰爭全面爆發。這次戰爭使得孟加拉國的獨立成為現實,印巴關系更加緊張。直到1972年12月,印巴才在國際社會斡旋下,簽署協定并完成撤軍。
戰后,印巴斷絕的外交關系直到1976年才恢復,但還是在80年代因克什米爾問題發生多次沖突。1999年,因巴方偷襲印控克什米爾,又引發了持續數月的卡吉爾沖突。最終,印軍擊退了越過實控線的巴軍。
停戰后,兩國領導人通過互訪緩和緊張關系。但好景不長,印度指責2001年印度國會大廈受襲以及2008年在孟買發生的連環恐怖襲擊,兇手均來自巴基斯坦。這對兩國脆弱的關系造成巨大沖擊。盡管兩國在隨后幾年不斷開展外交對話,也實現過領導人互訪,在經濟、金融、邊貿等方面合作成果不斷,但那根深埋的刺仍在不斷刺激著兩國的神經。

伊斯蘭激進分子于2008年11月襲擊孟買的泰姬陵酒店,現場濃煙滾滾
分治并非最優方案
2019年8月,莫迪政府取消了克什米爾地區70多年來享有的憲法特殊地位,又將印巴關系推向了緊張對峙的邊緣。
9月22日,莫迪在特朗普出席的休斯敦集會上,談及針對克什米爾的“廢除憲法第370條”的問題。次日,巴總理伊姆蘭·汗與特朗普會晤,表示了對印度關于克什米爾爭端做法的無奈,稱因印方一直回避與巴方就此展開雙邊對話,希望美國或其他國家能在印巴問題上發揮作用。
歷史上,聯合國以及美國、蘇聯等大國的領導人,都曾介入過印巴問題。而且,印巴開國領導人曾“并肩”為獨立而戰。但這些都無法讓兩國對克什米爾問題,做出帶來最終方案的讓步。
而12月印度議會通過《公民身份修正法案2019》,授予來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國的“受宗教迫害的”印度教、錫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以及天主教信徒“非法移民”以可合法申請印度公民身份的權利,穆斯林未被包含其中。此舉激怒了德里、海德拉巴等地的穆斯林,抗議活動中發生的警民沖突,造成數十人死亡。當時,印度緊急從克什米爾撤出約7000名士兵,以應對嚴重的全國騷亂。
這次騷亂余波未了,甚至在特朗普今年2月訪印期間還有惡化,蔓延到首都新德里的東北部區域。它再一次提醒人們,印穆宗教沖突并沒有因為分治沉寂下來,反而因為這種對身份的強化,以及在巴基斯坦“擁核”、印度經濟崛起后所產生的“改變地緣現狀”沖動,而曠日持久。
世界上“伴生國家”之間的沖突和分歧,多是因關于身份對立的問題而起,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朝鮮和韓國等等。從隨時重現的緊張對峙中,或許可以理解分而治之并不是一個最優方案。通過對話尋求身份利益的實現,雖也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但終歸不似分裂所造成的暴力那樣慘痛。
有著世界影響力的國家的調和,能暫時帶來和平的曙光。但和平對話的進程,還是需要切實的“利益攸關方”中強有力的領導人予以耐心地推進;稍有差池,就會使得和平的大地出現裂痕,而這個裂痕的彌合,則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傷痛和不確定的未來,時刻為人類敲響著警鐘。
(作者張洋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學者、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2015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