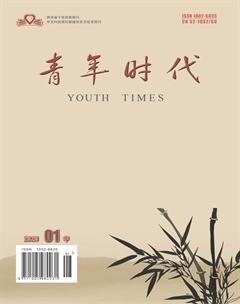方士締造的中醫史詩
哈思為
摘 要:本文試圖以生命哲學觀發展為線索,探索中醫發展歷程。按照《尚書大傳》,三皇為燧人、伏羲和神農。神農為醫藥始祖。至西周有“醫師”和“方士”兩種醫生設置。“醫師”是王室設立的官職,下設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方士”始于姜子牙傳太公孫神農手眼方術。此后,“醫師”不斷豐富醫學理論,以天道駕馭醫道;“方士”技藝(方術)成為中醫實用技術主流,以醫道附和天道。南北朝時期,皇帝出征有御醫隨行,方士已被邀請傳授御醫技藝,醫師與方士技藝融合。此后,中醫學不再有宮廷醫學和民間醫學的分別。唐宋元明清時期,醫藥學家輩出,而天人合一成為醫學各家的共同理念。
關鍵詞:方士;方術;中醫文化;中醫史
一、引言
每一個重大科學突破都從驚人的猜想開始[1]。中醫學的每一次發展都是生命哲學的觀念突破,而后獲得進步。相對于天朝大國,最初把來自方國之士稱為方士,把方士的技術稱為方術。本文從醫學方術入手綜述方士對中醫學的推動。本文談及的方術,特指醫學方術。
二、上古醫學的奠基
燧人氏掌握了鉆木取火的技術,從而使大量原本不能食用的植物、動物和礦物資源,成為可以食用的東西。伏羲氏開始用抽象的陰陽符號標準對整個世界的理解,從而有了對“道”的追求。神農氏以親嘗百草的實踐,開啟了中國人的“醫道”。
這時,中國人的祖先已經開始了對生命的全新理解:自然界有足夠的力量來幫助人戰勝疾病;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超越有形之外的統一。中醫的生命哲學開始建立。
三、有文獻證據的醫學開端
(一)周代官方醫學及醫學制度
現存《黃帝內經》在文字表達方式上看,其中的《素問》應該是戰國時期從師傳口授轉變成文字;其中《靈樞》應該是從春秋早期轉變成文字。周代王室以黃帝后裔自居。在推崇文獻保護、注重禮樂制度的周代,以王室祖先之名成書的《黃帝內經》自然是上古所傳和官方整理的。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為神仙類書籍。這說明在秦漢文化中,神仙和醫學同根同源。
最早無爭議的朝廷醫官設置見于《周禮·天官》的醫師設置:“聚天下毒藥以供醫事”。醫師下設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四個職業。周代注重禮樂制度建設,具有完善的文獻管理制度。所以這些醫生類似于后來的太醫或者御醫。
這是以天道馭醫道的醫學傳承。“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素問·至真要大論》)。周代官方醫學相信,天地變化如同生命存在一樣,具有生、長、壯、老、已的不同階段;具有自我平衡能力;具有自我修復能力。醫生可以從天道運行中得到啟示,來進行健康管理。
(二)周代的軍醫學和軍醫制度
周代軍醫學是姜子牙傳太公孫姜奭醫學技術,做武王統帥部方士,后被康王封城賜姓,又名聶奭。聶奭即歷史上留下姓名的最早軍醫,后世把這套原始技藝稱為神農手眼[2]。醫學內容主要是《神農五臟論》和《神農食品》。最早無爭議中國軍醫設置出現在史料《六韜·龍韜·王翼》對方士的記載:“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這是大約3100年前武王伐紂時期。
這是以醫道附和天道的醫學傳承。這是用觀察自身的變化,推知遠方的變化,改變了殷商之前對神的盲目崇拜,轉向對人類能力的自信。例如,“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荀子·非相》);“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呂氏春秋·察今》)。
四、長桑君與扁鵲傳說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載了長桑君與扁鵲的故事。這個傳說故事的民間傳說版本可見《李醯殺扁鵲故事》[3]:“我有一法,是太公望所傳神農手眼,齊丁公后世孫長桑君所授。”扁鵲留下最重要的醫書《難經》。
《難經》與《黃帝內經》區別很大。《黃帝內經》是眾多獨立成篇的醫學文獻的匯集。《難經》則是通篇一體的,全篇直擊醫學問題,顯示了醫學獨立于古代哲學之外成為一個專門學科。扁鵲所傳醫學不是根源于天道,而是根源于人體,故類屬于太公孫聶奭所傳神農手眼方術。
五、倉公蒙難反映的方士地位
《史記》中記載了兩位醫生扁鵲和倉公,都是方士,都受到御醫陷害。倉公,名淳于意。有傳說倉公學習的是扁鵲醫術[4]。與倉公發生矛盾的醫生,主要是齊王的御醫。也就是方士和官方醫生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倉公蒙難。漢文帝召見倉公,不是因為倉公醫術高明,而是因為倉公有一位孝順的女兒緹縈。因此,漢文帝并沒有留下倉公做御醫,而是赦免了倉公的罪。這個故事已經成為中國古代二十四孝之一。
倉公的故事顯示,在西漢時期方士的社會地位很低,醫術很高,被社會主流所鄙視。方術追求實際應用的技藝,追逐于人體的實際變化,按照當時的觀念屬于形而下的東西。“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周易·系辭上》)。倉公之后,方士的社會地位長期沒有改變。例如,張仲景時期、華佗時期和葛洪時期,方士的地位都很卑微。
張仲景在《傷寒論》自序開篇說:“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此處,張仲景直接把自己的醫學技術表述成方術。東漢末年的華佗對自己的方士身份很自卑,其事跡見于《后漢書·方術列傳下》《三國志·方技傳》。晉代葛洪則以道人身份自居,其醫術實為方術[5]。
六、“山中宰相”顯示的方術影響
《梁書·陶弘景傳》記述了陶弘景與梁武帝之間的關系:“書問不絕,冠蓋相望。”陶弘景作為史上著名的方士,整理了大量的醫學文獻,同時也總結了大量養生方術,如《本草經注》《名醫別錄》《集金丹黃白方》《二牛圖》《華陽陶隱居集》等。陶弘景之后,方士地位經常超越御醫,構成了御醫學習方術的驅動力。這種地位的改變,造成了后來帝王召見或任用道士的局面。隋唐時期的方士孫思邈,先后被隋文帝和唐太宗召見。宋代匯編《局方》時,也有道士馬志等參加。明代龔居中、張景岳等,都因方術影響了當時的醫學。
陶弘景之后,方術和官方醫學不再對立,而是轉向了融合。天人并重,天人合一,成為中醫界的共同理念。在這一理念下,天地被賦予了生命,人體被看成是自然。
七、皇家方術普及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組織編著《救荒本草》《保生余錄》《袖珍方》和《普濟方》等。在這些著作中,方術被大量吸收。朱橚之后明代帝王中多有重視方術者。為普濟天下,大明皇子直接研究方術,公開印刷推廣。清代乾隆御醫吳謙主持編修《醫宗金鑒》,首推張仲景方術《金匱要略》,并將《黃帝內經》中的運氣學說編篡成歌訣,獨立成篇。更顯示了方術與御醫技術融為一體的情況。
八、結語
中醫生命哲學的發展,貫穿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發展歷程,因此對整個社會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人們的普遍觀點是:《周易》影響了中醫發展[6]、理學影響了中醫發展[7]、法家思想影響了中醫發展[8]等。而實際上,中醫學對相關領域的影響更為深刻,并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學觀。
參考文獻:
[1]鞠強.大膽猜想,小心求證[J].科技導報,2016(16).
[2]聶文濤.中醫非遺技術神農手眼的運動和營養[J].飲食保健,2019(18).
[3]史遷夷.李醯殺扁鵲故事[J].小說月刊,2018(8).
[4]衛機.倉公蒙難[J].青年文學家,2019(8).
[5]郭起華,歐陽建軍.葛洪的養生學理論與方術述評[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1993(4).
[6]許偉明,胡鏡清,江麗杰.《周易》哲學觀對中醫辨證論治原則和方法影響芻議[J].環球中醫藥,2017(1).
[7]焦健洋,孫竹青,劉更生.程頤理氣思想對中醫學理論的影響——以《圣濟經》、朱丹溪、黃元御為例[J].醫學與哲學,2019(10).
[8]龔雪敏,朱祝生,黃高.法家論治思想對《黃帝內經》防治理論的滲透和影響[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