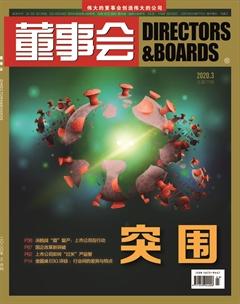“戰略投資者”的未解疑問
楊為喬
2020年2月14日,證監會發布《關于修改<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的決定》《關于修改<創業板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暫行辦法>的決定》《關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的決定》,并自發布之日起施行。這一組規定以“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再融資市場化約束機制,增強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為要旨,從而被人們稱之為《再融資規則》,或冠之以“再融資新政”。從監管機構的角度來看,再融資政策調整的目的在于形成一個公平合理、風險可控、相對穩定、理性的市場化投資體系。假若監管當局的政策調整,或曰“新政”,卻成為另一場政策投機的盛宴,豈不是與市場調控的初心南轅北轍?
其中有關上市公司戰略投資者的規定,則更具有制度性意義。它或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乃至改變現有上市公司融資制度模式,對資本市場產生結構性影響。為此,一方面有諸多投資者躍躍欲試,刀叉齊備,準備享受這場制度套利的盛筵;另一方面,也有市場人士對于其中的風險憂心忡忡,期望監管當局能夠出臺相關規則,明確戰略投資者的定義,規范其投資行為。3月20日,證監會發布《發行監管問答——關于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引入戰略投資者有關事項的監管要求》,進一步明確回應了上市公司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實體和程序兩方面的問題。
明確要件
按照證監會《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第七條表述:戰略投資者是指具有同行業或相關行業較強的重要戰略性資源,與上市公司謀求雙方協調互補的長期共同戰略利益,愿意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較大比例股份,愿意并且有能力認真履行相應職責,委派董事實際參與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幫助上市公司顯著提高公司質量和內在價值,具有良好誠信記錄,最近三年未受到證監會行政處罰或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投資者。
較之于普通投資者,戰略投資者愿意與發行人達成某種長期的戰略合作關系,甘愿承擔特定期限內發行人股票價格波動風險。就此而言,戰略投資者不僅要擁有重要戰略性資源、足夠的資本實力,也必須具備選擇目標發行人的經驗與眼光,更需要能夠承擔市場風險的定力和胸懷。就具體規則而言,“戰略投資者”通常須具備實體與程序兩方面的要件:
從實體要件來看,除滿足《實施細則》第七條的要求外,戰略投資者還應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1.能夠給上市公司帶來國際國內領先的核心技術資源,顯著增強上市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帶動上市公司的產業技術升級,顯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2.能夠給上市公司帶來國際國內領先的市場、渠道、品牌等戰略性資源,大幅促進上市公司市場拓展,推動實現上市公司銷售業績大幅提升。
從程序要件來看,上市公司擬引入戰略投資者須按照《公司法》《證券法》《管理辦法》《創業板管理辦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相應的決策程序。主要包括:1.訂立戰略合作協議,主要內容應當包括:戰略投資者具備的優勢及其與上市公司的協同效應,雙方的合作方式、合作領域、合作目標、合作期限、戰略投資者擬認購股份的數量、定價依據、參與上市公司經營管理的安排、持股期限及未來退出安排、未履行相關義務的違約責任等;2.引入戰略投資者應為單獨議案由董事會審議,并提交股東大會決策,獨立董事、監事會須發表明確意見;3.股東大會應當就每名戰略投資者單獨表決,且必須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中小投資者的表決情況應當單獨計票并披露。
未解之問
深入、全面界定“戰略投資者”概念,或許還需要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戰略投資者的制度定位類別。自20年前“戰略投資者”這一概念進入中國資本市場視野的那一天起,戰略投資者似乎始終充滿著某種不確定的色彩,并伴隨著不同時期再融資市場的需求和規模變化,以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松緊收放程度,而時隱時現。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是,當資本市場需要資金投入時,戰略投資者就會被人們提起、關注;而當資本市場資金充裕時,戰略投資者又往往身形難覓。這種現象的出現是不是市場規律的使然?抑或是受到了某種市場外部力量的影響?至今不甚清晰。同時,對于戰略投資者的來源,也是將目光更多地投放在外資部分,所以最初當人們提到“戰略投資者”的時候,也常常將其等同于“外資戰略投資者”。2005年商務部、中國證監會等機構也曾聯合發布《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規范外資對上市公司的戰略投資行為。此外,近年來也出現了所謂“民間戰略投資者”的提法,以強調這類戰略投資者的資金來源與具有國資背景的戰略投資資金來源的不同。顯然,當我們以“外資”、“民資”等標簽來框定戰略投資者時候,其實已經忽略了戰略投資者們的平等性前提,如果說對外國投資者在國內的戰略投資行為,還可以在入世承諾、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以及各國雙邊投資制度安排下進行適當的、對等限制的話,那么對于同屬國內資本的“民資”或“國資”在戰略投資領域再施以區別對待就不那么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了。
第二,“戰略投資者”概念的出現,實質上對現有上市公司股東進行了一次新的“分類”或者“分層”,即在上市公司原有股東、大股東、控股股東概念之外,添加了所謂“戰略投資者”股東的類別。這些概念之間并不完全對立,甚至時常相互交叉融合,這不僅增添了劃分股東類型的難度,更需要在不同股東類型間進行有效的權益區別。否則提出“戰略投資者”這一概念,便無法理與具體制度安排上的實際意義。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必須明確“戰略投資者”的名分,只有在框定“戰略投資者”概念(最好是“法定”)的前提下,才能建立與戰略投資者有關的制度系統;第二種看法則主張忽略、放下對“戰略投資者”概念的執念,而是以具體的戰略投資行為、投資效果來判定該投資是否屬于“戰略投資”,該投資行為人是否屬于“戰略投資者”,進而對其施以相應的法律規管與約束。其實,上述兩種看法之間亦非絕對的涇渭分明,倒有某種殊途同歸的感覺。
第三,“戰略投資者”與投資風險。整體而言,上市公司引入戰略投資者的長遠目的在于為公司股價長期穩定提供“壓艙石”,但證監會對頒布再融資新規目的表白卻更為直接:“助力上市公司抗擊疫情、恢復生產。”恰恰是這種直白的表達,以及對應的大量政策福利,比如非公開發行的定價由不得低于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均價的9折改為8折;抑或是定價基準日由發行期首日拓寬為董事會決議公告日、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日或者發行期首日;股票鎖定期由36個月和12個月分別縮短至18個月和6個月,且不適用減持規則的相關限制等,在為“戰略投資者”帶來福利的同時,恰恰掩蓋了真正的戰略投資者更宜長期持有的原理。而不得不令人質疑:這種戰略投資者的出現是否能夠符合公司長遠利益?是否能夠起到穩定上市公司股價的作用?或者相反會攪動公司股價,帶來更多的不確定的投資風險?!顯然,戰略投資者這種制度安排是一種長期避險機制,假若它的出現和存在會助長市場投機行為的話,那么它的存在就值得反思。
第四,以戰略合作協議約定、鎖定期限制為代表的實體要件,以及以董事會/股東會決議程序規范、獨立董事/監事會獨立意見等程序性規范的要求,能鎖定戰略投資者嗎?能夠真正鎖定“戰略投資者”的只應是發行人長期和可持續盈利潛力,否則僅以股價差異作為是否進行長期投資的唯一標準。以“鎖定期”為例,再融資新政中鎖定期的縮短,顯然有助于“吸引”戰略投資者的出現,但鎖定期并不能鎖定戰略投資者。同意這樣一種說法:“鎖定期的核心是法律責任、市場風險。”更準確的表述或許是:鎖定期是戰略投資者承擔法律責任、市場風險的最低期間要求,更不是確定戰略投資者的唯一標準。
作者為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