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電技術,我們要向歐洲學習什么
王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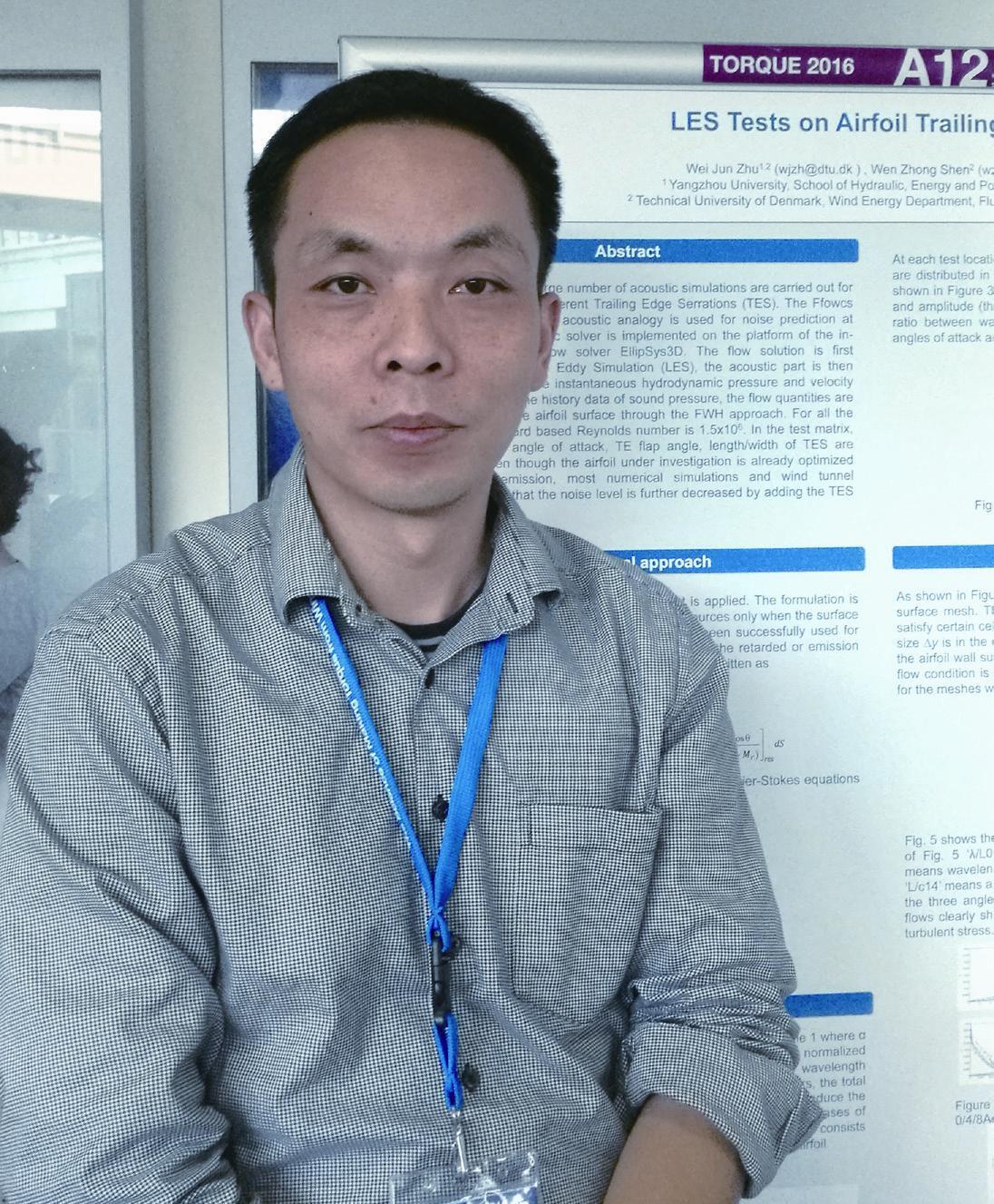
內外并舉,縮小技術差距
Q:在風電技術方面,中歐存在哪些差距?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A:歐洲風電發展較早,一些技術應用成熟度高的國家將提前實現100%可再生能源發電。根據2019年的統計數據,丹麥的風電發電量已經接近總發電量的50%,在國家能源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作為良性循環,成功的能源轉型帶來了風電技術革命,又促進了風電產業的健康發展,進而推動能源轉型。
目前中國的許多企業都非常重視彌補風電技術的短板,歷經多年發展,技術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在技術賽跑中,我們看到了歐洲的背影,當背影逐漸清晰的時候,我們發現剩下的這段距離實難超越。因為前期縮短的差距實際上涉及的都是相對成熟的技術。如今,風電進入設備大型化的發展階段,許多傳統的技術方法已不能適用,主要表現為大功率機組的研發需要考慮更復雜、更極端的風況,機組必須能夠在交替變化的復雜載荷條件下正常運行。以翼型設計為例,據我了解,國產葉片基本沒有敢于嘗試完全自主設計翼型組的;以葉片為例,承載同樣的極端載荷,為什么重量難以降低?以風電場為例,我們所用的WT、WindPro等諸多歐洲開發的軟件,不能解決陡坡、懸崖、凹谷地形條件帶來的設計誤差問題。
Q:如何縮小技術差距?中歐在技術方面可以建立哪些合作機制?
A:上述問題的解決,總體舉措可概括為內外并舉,即加強內部合作,促進內部循環;對外尋求合作,促進外部循環。當前,我國眾多的風電企業正在實施相似的方案。國內不少企業在丹麥設立了研發部門,有的已經歷經10多年時間,通過聘用當地具有豐富經驗的研發人員迅速縮短雙方的差距。誠如前面提到的,風電技術賽跑到現階段,中歐比拼的是關鍵技術領域的先進性和成熟程度,后者是風電設備實現量產和規劃布局的重要保障。
甘坐“冷板凳”,解決軟件“卡脖子”問題
Q:目前,大部分零部件都已經實現國產化,但依據自然條件進行自主設計、研發新機組的能力尚有不足,尤其是軟件開發能力,您認為中國要從哪些方面增強這方面的能力?
A:作為一名科研人員,通過和國內外風電企業的合作,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風電企業存在嚴重的設計軟件“卡脖子”問題。在2020年國際單邊主義、逆全球化趨勢盛行的背景下,我們已經無路可退,可當大家準備背水一戰時,卻發現“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鍵技術攻關需要長期的科研積累,而長期的積累依靠的是行業高端人才堅持不懈的付出。對此,行業內的領導和相關科研工作者都感同身受。曾經有多個風電企業向我咨詢,公司目前開發某一產品,國外同款設計軟件還沒更新,怎么辦?據我所知,這些軟件的更新幾乎是與中國風電發展同步的。
多年來,中國風電企業通過持續的用戶信息反饋,推動了國外軟件的不斷完善,最終導致對國外軟件“吸毒”式的依賴。商場如戰場,等待更新軟件的過程錯失的是提升國際競爭力的良機。
這方面是最需要向國外學習的。在丹麥工作期間,我和同事們幾乎沒用過風電商業軟件,團隊面向的就是行業軟件的開發。十幾年,我們完成了許多專業技術程序的設計和開發,其經費多數來自丹麥的科技部和能源部以及歐盟,我讀博士三年的課題經費就來自于丹麥能源部。例如,EllipSys這個行業知名的程序由丹麥科技大學(DTU)開發,至今經歷了近30年的積累,長期服務于丹麥的風電企業。我耗費了幾年的光陰,參與過其中風力機氣動噪聲模塊的開發,相關成果已經服務于眾多風電企業。
實現突破必須有積累,我們現在較多的重點研發計劃偏重于實際應用,考核的標準多是實現重要的成果轉化。這固然十分重要,但沒有堅實的理論基礎,要想在三至四年項目執行期間實現重大技術突破,壓力是非常大的。我期待包括從事風電業務的一些企業,從長遠出發,高度重視國產軟件的開發,投入專項經費盡快實現關鍵設計軟件的國產化。
愚公移山,理論與應用緊密結合
Q:在基礎理論、應用研究方面,中國風電產業有哪些可以向國外學習的模式和經驗?
A:風電產業鏈包含諸多的關鍵技術,而關鍵領域的長遠規劃和頂層設計是風電行業長遠發展的保障。
相比其他行業,風電還很年輕,攻克一個個技術難關需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在短期內全面實現技術超越是一種過于樂觀的想法。唯一的途徑是重視基礎研究,戮力同心地組織科技攻關,產生一批國際領先的突出成果。
我們經常參加一些科技成果鑒定活動,有不少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是在后續項目指南編寫、項目申請中,我們會有意規避這些研究方向,認為它們實現了國際先進水平,難再有作為。不過,我認為,好的成果更應該加大力度繼續深入研究,科學研究是沒有盡頭的,持續積累并形成技術儲備是極其重要的。
早在10年前和維斯塔斯合作動尾翼葉片項目過程中,我就發現他們十分關注技術儲備,不僅限于服務當前的產品,而且重在規劃未來。我感受比較深的是,丹麥風電產業在基礎理論和應用方面結合,產學研的真正結合,是實現風電科技發展的重要渠道。丹麥風電持續領先國際,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本國幾所大學源源不斷的人才輸出和基礎理論支持,并且從理論到應用幾乎實現無縫連接。以丹麥科技大學為例,我曾經所在的風能學院有250多人,研究方向覆蓋流體、氣彈、材料、氣象、電氣等10余個方向,每個方向都與企業有緊密合作,而且這種合作機制是具有持續性的。
這個模式值得借鑒的有兩點:一是開展真正的產學研合作,高校和企業間相互高度信任,形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目前,我所在的揚州大學也嘗試了這一模式,與上海電氣風電集團有限公司形成戰略合作關系,雙方高度信任、緊密協作。二是集合優勢資源,整合研究團隊。我國風電研究力量過于分散,高校和企業的研究相對脫節,許多研究熱點高度重合,造成一定的資源和人才浪費。國內知名風電企業的研發人員規模從幾十至數百人不等,多數是研究生學歷,其中包括大量的博士研究生。如何整合資源,打造一支風電研究的精英團隊,我認為是當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比如設置國家級風電技術研究中心,涵蓋風電的各個研究方向,培養一支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研究團隊是保障風電長遠發展的可行方法。
十年磨一劍,培養國際化人才
Q:風電技術邁向更高層次,對風電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在人才培養模式方面,歐洲國家的哪些做法值得我們學習?
A:2001年,丹麥科技大學研究生設置了風能方向,我是被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轉眼將近20年過去了,如今我所帶的本科畢業生,有一些又坐到我當年的教室攻讀風能碩士學位。
記得提交碩士畢業論文時,同班同學Andersen對我說,“我的畢業論文幾乎用上了大學選學的所有課程知識。”這一點令我欽佩,這既體現了他對未來的認真規劃,同時,風能專業課程的合理設置又讓我們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知識的融合交叉。他目前已經加入上海電氣風電集團。
如今,丹麥科技大學風能專業分為五個方向,每個方向包含幾門必修課。此外,學生不僅可以在全校內交叉互選所有課程,還可以在荷蘭、德國和挪威的幾所大學選課,并可以在這4個國家選擇畢業論文的導師。
Q:您有在丹麥留學的經歷,現在執教于揚州大學,希望培養出什么樣的人才?
A:我所執教的揚州大學新能源科學與工程專業,其課程模式設置部分參照了丹麥科技大學的培養方式,獨立學習、團隊分工合作訓練;教材、授課和考試全部使用英文;Matlab/ C++/Fortran編程實現風力機空氣動力學建模等,鍛煉了學生的國際化能力。他們在大學三年級時期,所掌握的風電專業知識基本接近丹麥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二年級水平。去國外攻讀風電專業的學生對此都深有感觸。我們一位到丹麥讀研的學生說,國內本科課程的專業性及國際化培養模式,極大地減輕了他在丹麥科技大學的學習負擔,現在的學習游刃有余。
未來風電發展當堅定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的戰略。以全球的視野和開放的模式向新一代風電技術人才傳授復合型知識,培養他們跨文化的溝通能力,接軌國際的專業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