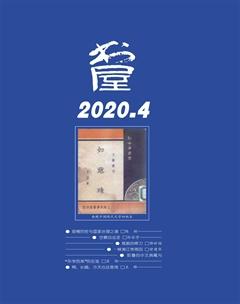流動(dòng)的油畫與極致的孤獨(dú)
陳虹燁
梵·高一個(gè)轉(zhuǎn)身,百年已經(jīng)過去。
我沒有坐在電影院的寬銀幕前,而是捧著手機(jī),在兩年前的一個(gè)平凡的冬夜,懷著一天下來疲累的心情,在宿舍書桌前點(diǎn)開了《至愛梵·高:星空之謎》。那時(shí),水杯里茶葉氤氳,我的思緒也不由自主地飄向了一百多年前的奧威爾小城。作為世界電影史上首部動(dòng)畫電影,影片取材于一百二十幅原作和八百多封信件,通過一百二十五位畫家全手繪的六點(diǎn)五萬幅梵·高風(fēng)格的油畫來詮釋這位偉大的藝術(shù)家。具有肌理、質(zhì)感的油畫藝術(shù)與以動(dòng)態(tài)、立體為追求的電影藝術(shù)之間的內(nèi)在契合,呈現(xiàn)了一場(chǎng)流動(dòng)的視聽盛宴,令我深深陶醉于其中。
油畫形式因素中豐富的色彩和躍動(dòng)的筆觸不斷地給予我直達(dá)心靈的藝術(shù)震撼,每一幀都讓我有想按下暫停鍵的沖動(dòng)。這樣優(yōu)美的單幅油畫以一秒十二幀的速度串聯(lián)播放,形成了流暢的動(dòng)態(tài)畫面,充分展現(xiàn)了色彩、光影、筆觸、質(zhì)感等油畫形式因素的動(dòng)態(tài)變化,這種流動(dòng)的油畫之美令我目不暇接。在影片一開始,我便不得不嘆服立體動(dòng)態(tài)的經(jīng)典之作《星月夜》。與之前靜觀畫作所產(chǎn)生的感受完全不同,空靈的音樂聲響起,月亮在這藍(lán)色的漩渦里閃動(dòng)著別樣的光輝,撥開層層云霧,搖曳著粗壯身軀的參天柏樹似乎要沖破天空,遠(yuǎn)處低矮的小鎮(zhèn)隱隱可見,似乎一場(chǎng)暴風(fēng)雨將要到來,給人以躁動(dòng)不安的情緒體驗(yàn)。隨著故事的展開,絢麗多姿、生機(jī)勃勃的自然風(fēng)光在這部影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早晨,陽光暖暖地灑在麥田里,金色的麥浪不斷翻涌,到處是一片和諧安寧。而到了夜晚,在深藍(lán)色的夜空籠罩下,皎潔的月光傾瀉在大地上,城鎮(zhèn)燈火閃耀。在影片中,伴隨著滴滴答答的雨聲,層層疊疊的短促筆觸給我們下了場(chǎng)油彩雨。而在浩瀚寂靜的星空之下,羅納河上粼粼波光,與之交相輝映。通過動(dòng)畫技術(shù)的充分利用,豐富而又深沉的田園之美躍然于熒幕之上,如同昨日重現(xiàn)般帶給我滿滿的幸福感。
在這樣流動(dòng)的自然風(fēng)光中,梵·高筆下的人物也相繼出場(chǎng)。從他們極其生動(dòng)的神態(tài)表情和連貫完整的肢體動(dòng)作,我感受到了電影技術(shù)與油畫藝術(shù)相融合所達(dá)到的巨大美感。我似乎走進(jìn)了油畫般的世界,而油畫里的他們活了起來,有了自己的喜怒哀樂。如《在彈鋼琴的瑪格麗特·嘉舍》中的瑪格麗特,伴著悠揚(yáng)的鋼琴聲,她就像從靜止的油畫里走了出來一樣,一襲白裙坐于鋼琴前,纖細(xì)修長的手指在琴鍵舞動(dòng)、跳躍,彈奏著一曲優(yōu)美的樂章,一位安靜純潔的少女形象直觀地展現(xiàn)于我的面前,美得如此生動(dòng)。但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動(dòng)態(tài)的人物顯現(xiàn)出美中不足的地方:短促有力的筆觸使得人物的臉部顯得有些怪異,加之人物運(yùn)動(dòng)起來時(shí)閃爍著的光斑會(huì)讓我產(chǎn)生不適感,甚至有點(diǎn)眩暈。但總體而言,人物風(fēng)貌的生動(dòng)豐富給電影增添了別樣的魅力。
伴著對(duì)梵·高風(fēng)格的動(dòng)畫的驚艷感,我逐漸將注意轉(zhuǎn)入到故事情節(jié)之中。故事以梵·高生前好友、郵差的兒子阿爾芒為主人公,開始了一場(chǎng)探尋梵·高死亡之謎的懸疑旅程。在父親的吩咐下,阿爾芒去送梵·高死前寫給弟弟提奧的信,可是當(dāng)他去找唐吉老爹詢問提奧的地址時(shí),才發(fā)現(xiàn)提奧在文森特下葬六個(gè)月之后也去世了。唐吉老爹向阿爾芒講述了梵·高的人生經(jīng)歷,他認(rèn)為梵·高童年時(shí)由于缺乏母愛導(dǎo)致了他悶悶不樂,后來他通過畫畫已經(jīng)變得自信成熟,因此他對(duì)梵·高的死表示非常震驚和奇怪,并向他介紹了梵·高的另外一位朋友加歇醫(yī)生。由于信件沒辦法送給提奧,阿爾芒只好又坐上火車去找加歇醫(yī)生,而去到加歇醫(yī)生家時(shí)他又不在家。因此,在加歇醫(yī)生回來之前,他接觸了加歇醫(yī)生家的管家和女兒、旅店女兒、船夫、警察等,通過他們的描述拼湊起梵·高最后六個(gè)星期的故事。但在這趟追尋梵·高死因的旅途中,阿爾芒逐漸發(fā)現(xiàn),無論是自殺還是他殺,孤獨(dú)的他注定要逃離冷漠無情的人世間。
梵·高的內(nèi)心是極其孤獨(dú)的。他一直渴望著與人接觸,期待有人能夠關(guān)心他,愛護(hù)他。他與弟弟很親密,每天都會(huì)給弟弟寫一封長信向他傾訴。即使不被混混理解,甚至受他們欺辱,但他還是每天叼著煙斗和那些混混兒在一起喝酒。他溫柔地抱起小女孩,輕聲細(xì)語地教她畫畫。他深情地注視姑娘,希望可以互訴衷腸。但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他歷經(jīng)坎坷,飽受孤獨(dú)。在家庭中,他被看作是夭折了的哥哥替代品,從小缺乏母愛的關(guān)懷;在戀愛中,他一廂情愿、不善表達(dá);在藝術(shù)上,他沒有伯樂,一生只賣出了一幅畫;在經(jīng)濟(jì)上,他貧窮落魄,需要依靠弟弟的支持;在生活上,他友善待人,卻受盡欺負(fù)。甚至,有一次他在河邊畫畫時(shí),一只烏鴉偷吃他的食物,他都能停止畫畫很高興地看著烏鴉進(jìn)食,可見其孤獨(dú)之深沉。
我想,梵·高的孤獨(dú)是令人壓抑的,同時(shí)也是美的。他孤獨(dú)的內(nèi)心深處仍然如孩子般純真美麗。盡管他受盡孤獨(dú)的折磨,但他仍然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用內(nèi)心真摯的情感來面對(duì)世界,勇敢無懼地追求自己心中所愛。這種洞悉塵世后依然熾熱的赤子之心為他的孤獨(dú)美增添了更加動(dòng)人的光彩。并且,他懼怕這樣的孤獨(dú),但他又享受著孤獨(dú)。孤獨(dú)是一個(gè)人的狂歡。雖然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他總是孤獨(dú)一人,但他仍然有一片自己的藝術(shù)天地,仍然有能給他帶來生機(jī)和希望的大自然。可以看到,在影片中,他總是一個(gè)人去大自然里享受田園風(fēng)光,用畫筆在藝術(shù)的海洋里盡情抒寫,自得其樂。孤是王者,獨(dú)是自己,面對(duì)真正的自己,他成為自己世界里的王者。他的孤獨(dú)達(dá)到了一種圓融的狀態(tài),呈現(xiàn)出自由、超脫的心境,令我心生向往。
影片首次提出了非自殺論,即吉諾和雷內(nèi)用槍擊中了梵·高,但這只是一種猜測(cè)。實(shí)際上,無盡的孤獨(dú)成為壓垮梵·高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只能選擇用死亡的方式永遠(yuǎn)逃離。而這種悲劇不僅根源于梵·高的生存需要和自我實(shí)現(xiàn)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還產(chǎn)生于“構(gòu)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gè)要求實(shí)際上不可能實(shí)現(xiàn)之間的悲劇性沖突”。在當(dāng)時(shí),他在繪畫中表現(xiàn)自己的主觀情緒的主張并沒有被主流接受,但這一觀點(diǎn)遠(yuǎn)遠(yuǎn)走在了時(shí)代的前面,他最終成為表現(xiàn)主義的先驅(qū),并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jì)的藝術(shù)。而這種“歷史超前性”的行為,正如黑格爾所言:“是一種有價(jià)值而注定要失敗的實(shí)踐。”因而,這樣的結(jié)局是不正當(dāng)?shù)摹⒘钊瞬豢山邮艿模瑫r(shí)又是命中注定的,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
比利時(shí)戲劇家莫里斯·梅特林克曾說過:“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種悲劇因素存在,它遠(yuǎn)比偉大冒險(xiǎn)中的悲劇更真實(shí)、更強(qiáng)烈。”相比于帶有非凡悲劇色彩的自殺論,影片將梵·高的人生悲劇用生活化的方式闡釋,并沒有抹去悲劇的崇高性,反而具有更為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