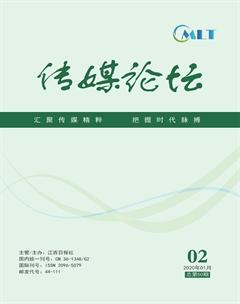職業新聞媒體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何做好“關鍵少數”
賈艷玲
摘 要:正在進行的傳播媒介變革使所有人都能平等發聲在理論上成為可能。2019年,我國網民利用手機上網的比例近乎百分之百,手機成為最主要的傳播渠道。本文通過對傳統新聞媒體在融合過程中對新聞把關作用的分析發現,盡管商業媒體、社交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曾經的信息壟斷,并獲得了多數用戶,但傳統媒體仍然是最主要的信息源,同時正是這“關鍵少數”,擔負著虛假新聞過濾器,輿論引導主力的社會責任。
關鍵詞:社交媒體;關鍵少數;虛假信息;職業新聞媒體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079 (2020) 02-00-03
一、引言
2019年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1.2%,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1%。可見,通過手機收發信息已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另據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的調查,54%的受眾更傾向于通過算法的推送(如搜索引擎、社交媒體、谷歌等)接收新聞,只有44%傾向于依靠新聞編輯和記者,例如通過報社的網站和Email。而且35歲以下的受眾,前者的數字為64%,后者只有34%。[1]那么,移動互聯網時代,大數據真的能取代媒體編輯和總編輯,為用戶型讀者提供真正需要的信息么?
當下,無論是看數據,還是分析海量案例,盡管多數人已經基本不看報紙,電視和廣播的收看收聽率大幅度降低,但人們所消費的新聞信息源頭仍然主要是傳統媒體。這里說傳統媒體似乎不太準確,因為幾乎所有傳統媒體都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發展了新媒體平臺,在這里,說職業新聞媒體可能更準確些,相對那些不是由傳統媒體主辦的新媒體我們稱其為商業媒體。在傳播的另一端,原來的“受眾”已被“用戶”一詞替代。不過,對新聞傳播來說,用讀者型用戶來定義似乎更貼切些。
筆者認為,社交網絡時代,職業新聞媒體雖然相較商業雖尚未發展出當年媒體暴利年代的贏利模式,也缺粉絲,但在信息傳播領域絕對是“關鍵少數”。
二、移動互聯網時代,更需要專業的職業新聞媒體當把關人
細究下來,若沒有職業新聞媒體為商業媒體打工,人們獲得信息的質量、數量與真實性將大打折扣。
第一,互聯網為海量信息提供了傳播平臺,但公眾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了幾近絕望的信息黑洞。選擇什么,不選什么,左右為難。此時,專業的新聞媒體價值便顯現出來,區分不同對象,篩選出讀者應知和必知的信息,是現實需要,也是存在的價值所在。
面對無任何規律可言,紛繁雜亂無法計算的海量信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人們普遍患上了信息強迫癥,手機不離手不離眼的人遍布各個角落(手游等是例外)。信息強迫癥是互聯網時代的必然產物,信息越多,人們越是感覺不確定和不安全,為了不與可能有用的信息擦肩而過,人們強迫自己不斷關注,不停搜集所有信息。這就造成了信息時代的人已經逐漸成了 “食信息動物”[2]。信息泛濫的嚴重社會后果是:在信息之海中沉浮的人們在辨別真假信息上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難。
互聯網同時也是謠言的溫床,在充斥不實信息的社交圈,不乏懷念傳統媒體的人。與社交媒體的公民記者相比,傳統的大眾媒體新聞把關人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并且要對新聞的真實性背負道德乃至法律責任。信息泛濫時代,公眾更需要類似的把關人來理一理思緒。
第二,云計算,大數據雖然已廣泛應用,但尚不能精準劃分使用者,機器的選擇很難真實反映用戶需求。以現有各類頭部客戶端和公號為例,它們在信息劃分方面附帶產生了一種負效應:窄化用戶視野。當下,我們幾乎每個使用手機和電腦的人都體會到了云計算、大數據的力量。只要下載APP(智能手機用戶不用APP的人幾乎不存在),就要接受個人信息被共享的條款。算法主導的媒體邏輯把人們圈禁在自己的“過濾氣泡”中,即搜索引擎給我們的只是它認為我們想要的東西。各種APP的大數據應用愈到位,我們就愈被分配進自己偏好的信息世界里。目前云計算器的智慧只是基于我們既往閱讀經驗和習慣來推薦,這就出現了一個極為吊詭的現象,雖然每個人同一網址打開后頁面顯示都不同,貌似為每個個體量身定做,但我們卻像穿上了緊身衣,因為被規劃所以視野反而越來越窄。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客戶端劃分用戶喜好的數據本來就是不真實的,如用戶只是偶然點開了被嵌進的鏈接便被視為這類信息的消費者。另一方面用戶常會不小心點中一條曖昧信息或強推信息,大數據就此會用這類信息一直糾纏這個偶然手滑者。
從這個意義上講,圈禁的感覺或許因為舒適和方便最初受歡迎,但互聯網標榜的多元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理論上的存在,終有一天,人們會打破這種被劃分,走向自由的世界。
第三,讀者型用戶的選擇有時并不是真實的選擇,媒體要主動形塑他們的需求。媒體設置內容時,需要多大程度考慮讀者的想法?幾乎所有媒體都在說,以讀者為本,做讀者喜歡的新聞。但實際操作中,越是做得好的媒體,反而越不信讀者調研那一套。一方面是因為讀者往往不可靠,另一方面是讀者有時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卡爾·霍夫蘭的“槍彈論”幾十年前就被認為片面了,教育的普及、民智的成長,使讀者不再把媒體當權威,但,讀者真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嗎?在21世紀初的前幾年,中國紙媒最為輝煌的時期,很多賣得非常好的報紙的總編輯公開表示,不要聽讀者說“我喜歡看什么”,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這是一種貌似多么輕視受眾的辦報理論啊!似乎為這個理論做注腳,2002年,筆者在吉林省的《城市晚報》做編輯時,整理過一套回收量一千余份的有獎讀者調查表,最讓編輯部不解的一個問題是:針對選項“你認為最重要的版面”(選項有時政新聞、社會新聞、文娛、體育、國際、副刊等)征求讀者意見時,75%強的讀者選的是時政新聞。而擁有一千多名發行員的發行部門反饋與此截然不同,發行員看到的是:半數以上讀者拿到報紙先看的都是社會新聞類有趣的或聳人聽聞的內容,即便那條好玩的新聞和他毫無關系。那時,正是紙質媒體的黃金時代(1998~2008年),都市報競爭激烈,自辦發行紅紅火火。
事實證明,發行部門的反饋的確是真實的。那么,為什么即便在匿名的讀者調查問卷上,人們也會勾選時政要聞,而他們首選閱讀甚至唯一閱讀的,卻是編輯部投精力最多的硬新聞之外的東西呢?
傳統媒體時代如此,新媒體時代呢?
近五年,新媒體的野蠻生長逼迫傳統媒體必須離開原域尋找新的大陸,但新大陸上,那些生長得最茂盛的新媒體,粘住用戶的也不是硬新聞,八卦娛樂、假新聞、搞笑視頻、樣樣比硬核新聞點擊率高出何止百倍。在大數據、云計算時代,多數APP都針對用戶的需求推送它認為用戶喜歡(或者說需要)的信息。推送最多的,仍然是八卦。我們看到,諸多在紙媒黃金年代風云叱咤的媒體和職業新聞人搞出來的新媒體,不但搞不過非媒公司的新媒體,甚至搞不過很多聽風即下雨,傳謠造謠的個體人經營的自媒體。
再看用戶,少有用戶承認自己最喜歡看的是抖音、快手上那些無聊、搞笑、表演拙劣的小視頻,但看點擊率,你就知道他們在說謊。
第四,娛樂至死的閱讀現狀需要負責任的媒體引導改變。權威數據這樣描述我們的視頻閱讀現狀: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7.59億,占網民整體的88.8%。各大視頻平臺進一步細分內容品類,并對其進行專業化生產和運營,行業的娛樂內容生態逐漸形成;各平臺以電視劇、電影、綜藝、動漫等核心產品類型為基礎,不斷向游戲、電競、音樂等新興產品類型拓展,形成視頻內容與音樂、文學、游戲、電商等領域協同的娛樂內容生態。
娛樂無罪,但只娛樂那就可怕了。雖然高質量的娛樂是主流,可普羅大眾現在主動和被動進入的是另一種娛樂場:無聊的笑話、夸張的惡搞、一本正經地傳謠,所有這些通過手機泛濫的東西已經成為相當多人的常規閱讀。如果沒有手機這種適合展示、傳播這些垃圾的媒介或者說技術,那么人們對于這些垃圾的存在是不知或不欲知的,當然也不會把之納入自己的日常閱讀中,這些垃圾信息刷流量是神物,若當成手機文化培養和傳播則害莫大焉。
媒介如同語言、文字一樣,對人們的思考方式、表達內容規劃了新的定位,并制造出新的話語模式,很難說手機(未來可能單獨存在的手機會變成衣角、發絲、眼鏡、植入體內的芯片或其他什么東西)沒有過錯,進一步說,如果手機沒有遇到移動互聯網,信息垃圾不會這么多被制造出來,也不會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并影響所有人的生活與思考。
早在電視成為生活必需品的時代,美國媒介理論家尼爾·波茲曼就反思批判技術帶來的電子文化,推崇印刷文化。視頻是以畫面和故事來表達的,其本身就天然缺乏文字的思辨性。思考的缺位,使視頻這種信息傳播方式娛樂化和簡單化。誠然,新聞的視頻表達比文字鮮活得多,但,最火的新媒體,有幾個是靠新聞短視頻來圈粉的呢?
新聞的靈魂是真實,這就注定新聞不能主題先行,新聞事件不能導演,在實際操作中,新聞內容更注重引導讀者,而不是迎合讀者。傳播信息、輿論監督、引導輿論原本就是職業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社交媒體時代,不是不需要新聞媒體了,而是媒體的責任更重大了。
三、職業新聞媒體要順勢而為,守正創新,做好把關人
第一,守住新聞真實性的底線,守正創新,不斷追求內容的高質性。新聞當然是反映事實的,還用說嗎?當然。
“新聞=事實”在當下眾聲喧嘩時代似乎只能約束職業新聞媒體,有那么多在社交媒體、商業媒體發酵的新聞,是建立在夸張甚至虛假事實基礎上的。好在,在獲取新聞信息方面,傳統媒體目前仍是公眾的主要獲得渠道,截止到2017年的統計數據,傳統媒體仍然生產著70%的原創新聞。從信任度角度來說,傳統媒體高于新媒體(推特、臉書、兩微一端等)何止以道理計。職業新聞媒體要比以往更為精心地守住這道事實關,才能生存下來,并獲得發展的源動力。
光是守正還不行,還需要創新,主要是在技術上、內容上、展示方式上要借鑒社交媒體的長處。以新聞的展示為例,做有體感的新聞。傳統媒體的產品不是放到手機上就是創新,也不是轉換成語音播報就是創新,還要聚焦到讀者的體驗,特別是情緒體驗上,這就需要不僅是編輯部,還要有技術和運營部門的通力合作。成功的爆款是少數,但建立在無數個不成功爆款基礎上的經驗會拉動傳統媒體組建的融合媒體有效提高質量。
第二,反映事件整體的真實性,以真實為基礎,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努力靠近真理。長期以來,媒體在聽到正面宣傳為主的辦媒要求時,多少會有些無奈。
在社交媒體時代,打開各種“某頭條”頁面,當標題黨讓你頻生被欺騙的憤怒時,當假新聞讓你哀嘆公知商媒們的不負責任時,當低俗下流推送固執地跳出來惡心你時,當用美女屁股和大腿包裝的海量視頻拉低你的品位時,你有沒有覺得這個信息洪流很垃圾?實際上,垃圾并不是主流,只是垃圾無所不在,誤讀難免。新聞所做的,不過是通過自己的選擇,將某些報道置于聚光燈下,而將另一些報道淡出視線,從而創造出選擇性的事實。此間凝聚了一股巨大且未被察覺的力量:拼湊一國公民對彼此印象的能力,操縱我們對“他人”看法的能力;在我們的想象中塑造一個國家的能力。[3]
如果新聞日復一日地告訴我們,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進步讓日本嚇尿了,美國嚇尿了,歐洲嚇尿了,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真的領先世界而不必努力創新。如果新聞水銀瀉地般給我們洗腦,宣揚競爭激烈教育不公,我們就會讓剛會說話的孩子進出各種課外班而剝奪他們的童年。如果新聞暗示權錢交易普遍、暗箱操作橫行,我們就會質疑政府所做的一切而不問緣由。如果新聞告訴我們美國每天都有槍殺案歐洲經濟在衰退,那我們就真的以為這些發達國家治安糟透了經濟已沒落。在各類媒體中展示的我們的社會,其實并非全然就是我們置身其中的真實環境。
所以,報道真實之外,更要傳遞整體的真實,這才會向真理更近一步,讓讀者盡量多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該怎么辦,如何面向未來。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明燈,絕不是枷鎖。
第三,真正融入媒體發展大勢,做強自己,拿到話語權。
一方面,我們有了一種萬能媒介,幾乎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數字印刷媒體,然后對全世界發表意見。[4]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卻發現真實情況并非如人所愿。在某些情況下,公民記者確實可以產生一些影響,但這并沒有從整體上撼動主要新聞機構在網絡空間的主導地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互聯網80%的新聞和信息流向集中在排名前7%的網站上,大多數網站(67%)受互聯網時代之前“遺留下來的”新聞組織控制,另有13%的網站只靠網上運營來生產大多數原生的報道內容。[5]網絡傳播時代,人們的主要信息來源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職業新聞媒體如果看到這個數字覺得很受鼓舞,那就高興得太過糊涂。數據表明,社交媒體時代,多數人追求快節奏與實用性,眾多從頭部客戶端獲取信息的用戶很少關注信息源,付出最多的打工者成了幕后英雄,更不要說還有很多兩微一端靠打碎、整合各類信息源的原材料來賣產品。用戶關心的是得到了什么,并不關心下蛋的母雞是誰。
不要指望商業媒體會把蛋糕公平地分一半給你,對于職業新聞媒體來說,掌握話語權是硬道理。如果話語權旁落,別說關鍵少數做不成,連相對體面活下去都成問題。
四、結語
哈佛商學院五年前的一項調查發現,10%的推特用戶生產了90%的內容,最熱門的10%的博文由名人或CNN之類的主流媒體主導。透過數據看本質,沒人可以否認媒介變革帶來的傳媒革命,在人人可以發聲的社交媒體領域,對全世界發表意見的設想,在技術上是可能的。但是,發聲是一回事,有沒有人聽到并回應是另一回事。在國內,雖然每個人可以平等地接入互聯網并發聲,但看兩微一端等新媒體的運營現狀能看到,真正影響輿論、解決問題的還是少數人、少數媒體,網議洶洶的事件,就算沒人來平息,也會很快被另一個熱點淹沒,人人獲得平等的話語權只是理論,遠非現實。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各類媒體魚龍混雜,海量信息難辨真假的現在,做好關鍵少數,當好過濾器,把好事實關,職業新聞媒體必須把責任扛起來。
參考文獻:
[1]彭增軍.新聞業的救贖——數字時代新聞生產的16個關鍵問題[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142-143頁.
[2] 【德】弗蘭克·施爾瑪赫.網絡至死[M].邱袁煒譯,龍門書局,2011年版,第98頁.
[3]阿蘭·德波頓.新聞的騷動[M].(丁維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22頁.
[4] 【美】丹·吉摩爾.草根媒體[M].陳建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局,2010年版,第10頁.
[5] 【美】詹姆斯·柯蘭,娜塔莉·芬頓/德斯·費里德曼.互聯網的誤讀[M].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