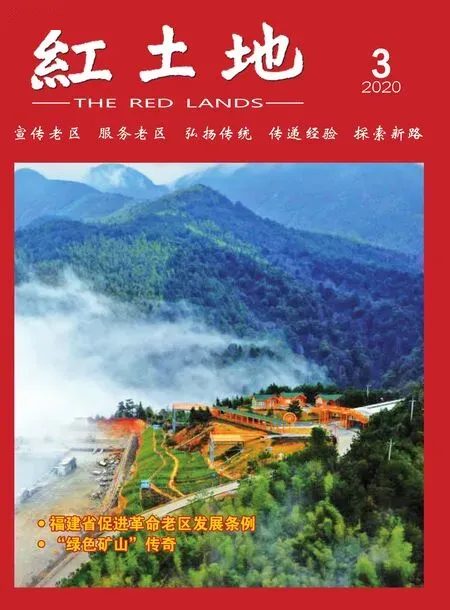東坑1935:鄧子恢脫險通道——關于1935年春鄧子恢脫險經歷的初步考證
◎王堅 文圖

● 當年護送瞿秋白一行的福建軍區保衛隊員嚴碧書
眾所周知,1935 年2 月下旬,時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的鄧子恢,隨同瞿秋白、何叔衡等從江西瑞金向福建永定轉移,途經長汀縣濯田鎮梅逕村一帶時被武平縣鐘紹奎一部及當地反動民團包圍。何叔衡為了不拖累戰友跳崖犧牲,瞿秋白被捕后被押至長汀就義,唯有鄧子恢成功脫險。這是一個久遠的歷史之謎,當后人為閩西革命先驅鄧子恢脫險感到慶幸之時,心中卻不免好奇,想一探史實究竟。
梅逕村與筆者出生地屬同一鄉鎮,長期以來,筆者多次實地采訪親歷者和知情人,查閱相關文獻資料,試圖弄清1935 年春鄧子恢脫險的真相。
一、隨行的保衛隊員嚴碧書生前口述證實鄧子恢從東坑脫險
1996 年正月,筆者在長汀縣濯田鎮梅逕村采訪了原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保衛隊員、護送鄧子恢一行突圍的老紅軍嚴碧書。對于這段“走麥城”的歷史,84 歲高齡的嚴碧書記憶猶新。他15 歲參加紅軍,念過隨營學校,當過號兵、班長、偵察員,接受護送任務時剛滿18歲。嚴碧書回憶——
那天(筆者查實應為陽歷1935 年2 月22日)下午6 點左右,在長汀四都鄉小金村,省政府保衛局偵察部高壽康部長召集我們開會,保衛局廖(漢華)局長講話,要我們30個黨、團員執行一項護送任務。30 個保衛隊員,清一色的棒小伙子,人手一支長槍,一支勃朗寧短槍,子彈也裝得滿滿的。從裝備條件看,就知道這次護送任務不一般。5 位保護對象:一個戴眼鏡穿皮襖,斯斯文文;一個花白胡子,60 歲上下;一個個子較高,兩只眼睛炯炯有神;還有兩位女干部。1949 年后黨中央尋找何叔衡遺骨時才知道,他們是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中央領導干部。廖局長指示要把5 位“工作人員”護送到永定張鼎丞處,宣布由一位中央來的叫“丁頭牌”的保衛隊長帶隊。要求全體保衛隊員一定要服從他的指揮,誰違抗命令就槍斃誰。

● 從牛子仁崠俯瞰,圖中右下角為東坑
我們借著夜色掩護出發。事先偵察得知,白軍宋希濂36 師已經滲透到附近村鎮,在我們將要路過的濯田鎮駐有匪兵正規軍,在水口村駐有民團武裝。所以我們非常小心,曉宿夜行,23 日白天在山深林密的白水寨休息了一天。24 日凌晨走到濯田的露潭村,前面就是汀江河。清晨6 點左右,有些當地的保衛隊員建議在露潭歇腳、吃飯。丁頭牌認為當地的保衛隊員熟人多,容易走漏風聲。下令抓緊時間渡江,到對岸的山村再找地方休息。
走到廟子角(地名)附近,看見一位肩扛鋤頭的中年男子。我是本地人,懂得村里有些勤快的人會早早起來引水灌田,可是心里還是“咯咚”一下。糟糕,30 多人的隊伍,又帶著武器,那個男子不可能不驚奇,這下難保不泄露行蹤。幾個保衛隊員趕在前面先試水深,找了處水淺的灘頭開始過江。到了對岸,大家相互擦干水跡,穿上鞋襪繼續前行。
到了外小逕村,有人提出在此休息做飯。因為剛才遇上了那個扛鋤頭的倒霉鬼,我心里一直不踏實。這里離水口只有五華里,那里駐有民團“義勇隊”,我們應該走出越遠越安全。可我說不上話,隊伍一夜行軍、渡河,饑寒交迫,幾個護送對象更是疲憊不堪。這時丁頭牌說:“填飽了肚子才能行軍打仗,就在這里歇腳吧。”大伙散開,各忙各的去了。事實印證了我的預感。就在端起飯碗剛要扒飯的時候,“啪啪”兩聲槍響,村口負責警戒的哨兵鳴槍示警。大伙扔下飯碗操槍上膛,迅速形成戰斗隊形,邊打邊撤,掩護“工作人員”轉移。哨兵說看見敵人扛了旗,從槍聲判斷,絕對不止當地的“義勇隊”。后來才知道是鐘紹奎的保安團正好運糧到水口,聽到密報就一路追趕包抄過來了。
我們沿著狹長的山谷向南撤退,沖到內小逕時,領導們簡單碰頭,建議兵分三路,瞿秋白一路向東,何叔衡一路向南,鄧子恢一路向東南,保衛隊員分三組掩護,分路突圍。如果按照這個走法,脫險是很有可能的。可是,丁頭牌轉了一個不該轉的彎。他手里的勃朗寧“乒乓”兩槍,剛剛分散沖出的幾路人馬又回到了原地。丁頭牌指著右側一座高山說:“這座山地勢險峻,于我有利,我們可以據守拒敵。”我和一些本地的保衛隊員大叫不妙。這座山叫牛子仁崠。我以前打柴經常來,是一座“獨頭嶺”。背后就是懸崖,追兵一到,那是沒有退路的。我們不敢不聽,廖局長已經有言在先,必須絕對服從丁頭牌的指揮,誰不服從就要執行紀律的。沒辦法,我們只好跟著往牛子仁崠上沖。
戰斗很快打響了,雙方交火近兩個小時,敵人的義勇隊團丁都是當地人,對山勢地形熟。他們偷偷從一條叫蛇峽的山谷繞到了我們的背后。這樣,鐘紹奎的保安團從正面仰攻,“義勇隊”在背后斷了退路。戰斗中,等在山后的反動“義勇隊”看見瞿秋白和兩位女干部沖下山,團丁一窩蜂擁上去搶劫,搶走了瞿秋白身穿的皮襖,搜走了紅軍干部隨身帶的“西紙”(白區用的錢幣)。鐘匪兵追趕而至,把瞿秋白押走了。
何叔衡的體能幾近極限,實在跑不動了。他不愿拖累別人,要我們向他開槍。我們當然不會這樣做,幾個人挾起何叔衡又跑。慢慢地敵人開始往山頂懸崖處壓縮。何叔衡臉色蒼白,乘我們喘息之機,一把奪過警衛的手槍想要自盡。警衛員急忙護住手槍,何叔衡脫開控制,縱身跳落了懸崖,我們失聲大叫。敵兵又逼近,我們匆匆忙忙只留下一塊石頭壓在何叔衡跳崖處。鄧子恢是閩西人,常年在山區活動,慣常看山勢走山路,他在保衛隊員的掩護下,從東坑方向趁機殺出了重圍,向涂坊方向突圍出去了。從小金村出發的30 位保衛隊員,除兩人下落不明外,有28 人陸續返回駐地。丁頭牌由于指揮失誤被處決(詳見拙著《浴血歸龍山——紅軍長征后福建省級機關和部隊在閩西的艱苦抗爭》,解放軍出版社2011年出版)。
嚴碧書居住的梅子壩自然村現在和東坑自然村同屬梅逕建制村。梅子壩距離內小逕只有5 華里左右。在這一帶出生、長大、勞作的嚴碧書熟知這里的地形地貌。接受采訪是在23 年前,當時耄耋之年的嚴碧書身體健康、思路清晰。他在回憶中證實,鄧子恢確實是從東坑村成功突圍。這是筆者目前為止發現的唯一親歷者證詞,是值得史學研究者采信的口述史資料。
二、東坑村成為鄧子恢脫險通道的主要原因
特殊的歷史事件使東坑村成為1935 年鄧子恢的脫險通道,或許有歷史的偶然,但深入探尋,其地理位置和早期革命基礎較好等因素也成為其重要原因。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戰斗態勢使東坑成為鄧子恢脫險的唯一通道。東坑村位于濯田鎮的最東部,東與長汀涂坊鎮丘坑村接壤,北隔劉坊村與長汀三洲鎮義家莊接壤,南與長汀宣成鄉林坑村接壤。當鄧子恢一行受到敵人包圍后,向南有美溪村謝猴子的反動民團從蛇峽方向包抄而來,向北有三洲戴步高的反動民團包圍而來,向西隔著汀江河,已經沒有退路。唯一的“生門”就是東面的東坑村。東坑向東翻越石夫山大仁崠,自古以來就有一條千年古道通往涂坊,當地村民歷來有到涂坊趕圩的傳統,水口渡上岸的谷米、食鹽、布匹等貨物也有一部分經東坑挑運到涂坊。據鄧子恢《我的自傳》記載,鄧子恢于1918 年因病從日本回國,不久就從龍巖東肖家中前往贛南的崇義縣當店員謀生,192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發動領導崇義工農運動。直到1927 年上半年大革命失敗,受到反動政府通緝才秘密潛回家鄉。在長達9 年的漂泊生涯中,一邊謀生一邊尋求革命真理。無數次往返家鄉與贛南之間,而東坑正處于龍巖通往贛南的古道捷徑之間,東坑村距離汀江古渡水口僅5 華里。在當時沒有公路的情況下,無論是步行還是乘船,鄧子恢都可能路經此地,熟悉這一地區的交通情況。
涂坊是張赤男、羅化成領導汀南暴動的核心區域之一,后來被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評為“第二個模范區”,原蘇區長汀縣委、長汀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鄧子恢于1929 年3 月至1930 年7 月間,先后擔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作為閩西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鄧子恢工作作風深入、注重調研、親力親為,從涂坊通往水口古渡的主要路徑應該為其所掌握。
(二) 對革命先驅的尊敬愛戴之情為東坑成為鄧子恢脫險通道打下了鮮明的政治基礎。東坑村距離長汀革命先驅張赤男烈士的家鄉長蘭村僅15華里,全村村民皆為雷姓。張赤男于1926 年參加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1927 年被選送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同年2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他參加過廣州起義,也曾在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農民武裝并肩作戰。1928 年2 月以后,回家鄉組織革命斗爭。據1970 年1 月原長汀縣蘇婦女部長、老蘇區干部鐘玉英的回憶,東坑村的革命骨干雷義洪(乳名樟樹妹)是與張赤男等喝血酒結拜盟誓的7 人之一,曾經在牌樓崠參加張赤男組織的秘密會議,策劃長豐(今長蘭)武裝暴動。1929 年2 月,濯田劉坊、坪嶺的反動民團襲擊東坑,由于事先得知情報,東坑群眾早已上山隱蔽。反動武裝進入東坑村時,暴動的組織人雷義洪手舉紅旗站在山崗上,突然點燃了陣地上的“長龍炮”,炮聲巨響,革命群眾沖殺聲響成一片。梅逕周圍各村的群眾聽到事先預定的炮響,手持鳥銃、梭標、大刀沖到東坑支援。反動民團以為是張赤男的隊伍來了,亂了陣腳,倉皇逃竄。東坑暴動隊伍一直追擊敵人到涼傘橋、劉坊一帶,武裝暴動取得成功(據1970 年《濯田人民革命斗爭史采訪檔案》)。

● 原東坑鄉蘇維埃政府舊址
1929 年3 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首次入閩,攻占長汀城,東坑村以張赤男領導的長汀南部農民暴動與之策應。同年5 月紅四軍在水口“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東坑革命群眾參加張赤男領導的暴動武裝一直沿路策應。1929 年12 月,毛澤東從上杭蘇家坡前往汀州,途經宣成張屋鋪、濯田梅逕,在小逕鐘玉英家住了一夜,曾召集張赤男、雷義洪等人開會研究革命工作(據長汀縣黨史辦1970 年采訪鐘玉英記錄)。1930 年濯田暴動成功后,東坑村也成立了鄉蘇維埃政府,現存有東坑鄉蘇維埃政府舊址雷氏鳴春公祖祠。閩西特委直接領導當時的長汀臨時縣委,鄧子恢與長汀臨時縣委成員之一的張赤男聯系緊密、感情深厚,同時也使東坑村在早期汀南革命斗爭實踐中成為星火燎原之地,黨領導農民運動、武裝暴動、建立紅色政權,喚醒了東坑人民的革命斗爭意識,產生了對革命先驅的尊敬愛戴之情,為東坑成為鄧子恢脫險通道打下了鮮明的政治基礎。
(三)白色恐怖中的“紅色堡壘”為東坑成為鄧子恢脫險通道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據原福建軍區老紅軍、閩粵贛邊縱隊獨立第七團參謀長范云龍生前回憶,1934 年底主力紅軍北上后,東坑、梅逕一帶成為長汀縣委、縣蘇維埃政府領導的游擊武裝活動的主要據點之一。留守的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也曾在此短暫駐扎。1934 年底至1935 年初,長汀游擊隊以東坑為據點,先后攻打三洲義家莊和涂坊扁嶺的反動民團。游擊隊負責人范鴻盛在戰斗中身負重傷,犧牲在東坑,后埋葬在村中的彎子牌上。東坑是一條狹長隱蔽的大峽谷,當年是山深林密、易守難攻的村落。據105 歲的原福建軍區獨立第七師宣傳員邱四嫂(現居長汀縣新橋鎮江坊村)回憶,她曾隨長汀游擊隊在東坑駐扎過一段時間,在此看護治療傷病員。當年作為紅軍游擊隊臨時醫護所的山洞和窩棚舊址依然還保存至今。

在“白色恐怖”年代,東坑人民與紅軍游擊隊保持著血肉相連的軍民關系。許多村民冒著生命危險,利用下地勞動、上山砍柴等時機,暗中為游擊隊傳遞軍事情報,傳送糧食、藥品、電池等物資。為游擊隊長期堅持地下斗爭、保存有生力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為東坑成為鄧子恢脫險通道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三、加強鄧子恢脫險通道挖掘宣傳與開發利用的現實意義
由于各種歷史原因,作為鄧子恢脫險通道的東坑村一直不為人所知。個別知情的東坑及鄰近村民也已辭世,有待進一步挖掘梳理、嚴密論證。當前,全黨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對這一黨史重要事實的挖掘宣傳,有利于豐富地方黨史資料,補充鄧子恢生平事跡。對于后人緬懷革命先輩,吸取紅色文化的營養,煥發奮勇前行的動力,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最近,龍巖市委、市政府提出“傳承紅色基因、建設綠色新龍巖”的決策部署,為閩西老區蘇區的鄉村振興指明了方向。東坑村自然環境優美、物產資源豐富,村境內古宅、古樹、古橋、古道、溪澗、田園相映成趣。東坑村緊鄰何叔衡烈士殉難處,村口現已建設有何叔衡烈士紀念碑和紀念館。該村距離長汀革命先驅、原紅四軍第11 師政委張赤男烈士故居僅15 華里,距離開國上將楊成武將軍故居僅20 華里,距離紅四軍“紅旗躍過汀江”渡口僅5 華里,距離劉坊村毛澤東故居“繼節公祠”也僅5 華里。加大東坑村紅色舊址群(鄧子恢脫險古道、長汀縣委和縣蘇舊址、福建省蘇臨時住址、長汀紅軍游擊隊藏兵山洞、窩棚醫院、范鴻盛烈士墓等)的保護利用,搶救紅色文化遺產,開發紅色教育資源,使之納入“汀南紅色文化大走廊”范疇,成為一個新興的紅色教育培訓基地,吸引紅色旅游和鄉村休閑游的人群,增加當地村民的收入,帶動鄉村產業鏈發展,是一個緊迫而務實的課題。

● 東坑自然村原福建軍區紅軍游擊隊駐扎的山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