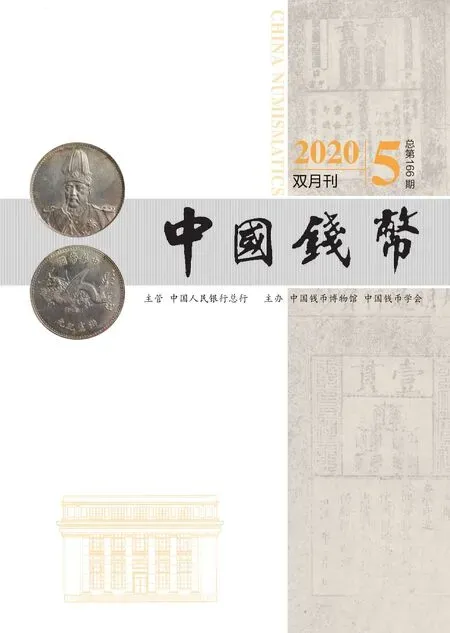16-19 世紀拉美白銀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變遷[1]
中國白銀需求在刺激全球白銀生產、促成第一個全球貿易體系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為世界學者所公認。16-19 世紀,中國的商業蓬勃發展離不開外國進口白銀,起初源自日本,但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在這三個世紀的時間里,拉美白銀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隨中國經濟、全球貿易的節奏發生了巨大變化。本文追溯了這些變化,直至源自西班牙比索的新的貨幣單位“元”的誕生。
一 引言
在中華帝國的晚期,白銀在經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考慮到中國1889 年以前從未發行過官方白銀鑄幣,這一角色就顯得更加重要。即使在缺乏官方白銀鑄幣的情況下,15 世紀,明朝(1368-1644)逐漸采用了以白銀為主要支付手段的財政制度。從16 世紀開始,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市場的白銀需求,并刺激了外國白銀流入,起初源自日本,很快又從西屬美洲進口。直到19 世紀末,白銀仍是中國主要的進口商品,盡管進口規模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1935 年,在世界其他地區早已采用金本位制后,中華民國政府推行貨幣改革,用法幣取代了銀元。此前,中國一直實行銀本位制。
中國和日本學者早就認識到,從日本和拉丁美洲大量流入的白銀是明末商業繁榮發展的重要力量。西方學者承認外國白銀對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但更強調中國因進口白銀而融入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過度依賴外國白銀被認為是1644 年明朝滅亡的一個關鍵因素。這種觀點認為,17 世紀中葉全球白銀生產和貿易的中斷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使明朝無法抵御國內叛亂和外敵入侵。類似的,有學者認為19 世紀上半葉因進口鴉片導致的白銀外流引發了鴉片戰爭,使中國屈服于歐洲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
這些關于中國對外國白銀的依賴和供給沖擊脆弱性的描述,忽視了中國國內經濟的動態變化和白銀在其中的地位。上述“危機”理論的前提是,中國對白銀的需求在過去三個世紀保持不變,而忽視了白銀作為貿易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國白銀需求的波動。1670 年以后,中國進口白銀的規模隨時間不斷變化,但幾乎完全來自拉丁美洲。要理解這些波動以及白銀流入對中國的重要性,必須考慮中國國內經濟走勢、貨幣供應結構的變化以及國際資本流動。
二 中國的白銀世紀(1550-1650)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1368-1398)決心徹底推翻此前蒙古對中國的統治。為恢復儒家經典中所記載的農耕社會制度和價值觀,他否定了宋、元兩朝持續繁榮的市場經濟,制定了包括實物賦稅、招募流民、建立衛所等一系列政策,并以實物而非貨幣支付官員和士兵的俸祿。明朝實行寶鈔制度,禁止民間使用金銀甚至銅錢。但到1425 年,寶鈔制度已徹底失敗。由于缺乏足夠的銅原料,明朝在1434 年停鑄了這種自秦朝建立以來政府發行的標準貨幣,導致民間以白銀交易。然而,15 世紀上半葉國內銀礦開采熱潮曇花一現,貨幣不足阻礙了商業的發展。
為實施反市場化的財政政策,洪武帝還禁止私人海上貿易,試圖將海外聯系限制在高度管制的朝貢體系中,在政府的密切監督下少量貿易。但這根本無法壓制沿海的民間貿易,明朝建立的朝貢體系在1530 年后隨日本銀礦的快速開發而宣告失敗。至1540 年,中國商人爭相涌向日本港口獲取白銀。日本的“銀礦熱”恰逢葡萄牙人到達東亞海域。起初,葡萄牙人試圖通過與明朝政府談判獲得貿易特權,但很快無功而返。隨后,他們與國內走私者聯手繞過海禁制度,將日本白銀運往中國。1548 年,明朝政府采取行動,從東南沿海的離岸島嶼鏟除“倭寇”(盡管其大多數實際上是中國人)。雖搗毀了據點,但仍無法禁絕。為切斷葡萄牙人和“倭寇”間的同盟,明朝在1557 年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貿易站,并通過廣州進入中國市場。1567 年,因無力承擔維持海上治安的高額費用,明朝廢除了海禁。海外貿易雖仍受管制,且禁止中日之間的直接貿易,但私人貿易的恢復促進了繁榮。
向中國運送白銀獲利豐厚的消息很快在伊比利亞商人間傳開。英國人Ralph Fitch 在1583-1591 年間游歷了印度洋的葡萄牙殖民地,他寫道:“當葡萄牙人從澳門前往日本時攜帶了大量絲綢、黃金、麝香和瓷器;而返程時則只帶回銀子。他們有一艘大帆船,每年都要從那邊帶回來約六十萬葡元。這些來自日本的白銀,以及每年從印度帶回的20 多萬葡元,在中國得到了極大的利用”。在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中將香料群島割讓給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試圖派遣探險隊前往菲律賓群島,打破葡萄牙對日本和中國市場的壟斷。馬尼拉灣長期以來一直是中日商人用絲綢、瓷器和金屬制品交換黃金、蜂蠟和木材的貿易站。1571 年,西班牙占領馬尼拉后即開始與中國進行貿易。這開辟了一條通過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獲取美洲白銀的新航線。中國商人很快抓住了這個機遇。1575 年,超過12 艘中國帆船在馬尼拉靠岸;到1584 年,每年大約有25-30 艘中國帆船抵達馬尼拉。1593 年,由于擔心美洲殖民地的白銀大量流到中國,西班牙王室開始限制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爾科之間的帆船貿易,設定了每年兩艘船、運載不超過50 萬比索的限額。但是,馬尼拉的殖民者、墨西哥商人和殖民當局等既得利益者,最終說服皇室打消了禁絕帆船貿易的主意。
拉丁美洲的白銀出口,包括通過跨太平洋的帆船貿易和從歐洲跨越印度洋的再出口,部分是由于歐洲消費者對來自中國的手工制品如瓷器和絲綢的需求越來越大。但正如Fitch和其他歐洲商人很快意識到的那樣,將白銀運往中國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在中國,白銀相對于黃金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價格遠高于歐洲和美洲。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在中國和印度)幾乎沒有任何商品能帶來更好的價格,或與它在歐洲所耗費的勞動力和商品的數量成比例,它將(在亞洲)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和商品”。因為貿易對亞洲和歐洲商人都有利可圖,“新大陸的白銀成為兩個遙遠地方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通過它很大程度上將那些遙遠的世界各地彼此相連”。因此,將白銀運往中國的套利利潤是建立第一個真正的全球貿易體系的主要動力。
在中國白銀需求的刺激下,東亞海上貿易蓬勃發展,促使除明朝外整個地區的統治者鼓勵有利于其本國經濟的對外貿易。在1602 年獲得對日本的統一控制后,德川幕府開始允許外國貿易,并與歐洲商人和東南亞統治者開展貿易談判。17 世紀頭十年,荷蘭人在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個新的機構—特許貿易公司,這對葡萄牙人構成了挑戰,并很快在東亞海上貿易中取代了他們。與葡萄牙人一樣,荷蘭人也專注于將日本白銀運往中國市場。
由于缺乏明代中國的貿易或海關檔案資料,衡量中國白銀進口的規模是相當困難的。學者們在確定白銀貿易規模時所采用的主流方法是,估算向中國市場輸送白銀地區的白銀出口量。從表1 可以看出,這種方法得到的估計量變動范圍很大。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在1540-1640 年的白銀世紀,中國從日本進口的白銀數量遠大于西屬美洲。而據萬志英估算,在此期間來自日本和西屬美洲的白銀總量大致相當(未完全包括走私量,其規模難以計算)。從馬尼拉海關收入看,白銀從菲律賓出口到中國的高峰發生在1595-1616 年。這一時期的出口量占菲律賓1645 年之前白銀出口總量的70%。而1620 年后,中國迅速增長的進口白銀主要來自日本,而非西屬美洲。

表1 1550-1645 年中國進口白銀總量估計 (單位:噸)
1615 年后,馬尼拉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趨于下降,根源一致,即彼此獨立開展貿易。一位曾在東印度工作30 余年的西班牙官員Pedro de Baeza,在1609 年建議西班牙王室充分利用將新大陸的白銀運往中國購買包括黃金在內的各類物資的寶貴機會:“因為在中國有數量巨大的、超過22k 的高純度金,如果運到新西班牙或卡斯提爾,可以獲得75%或80%的利潤”。Baeza 認為,通過向中國出口白銀獲得的利潤,將完全彌補西班牙在跨太平洋貿易中的長期赤字。墨西哥和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都將每年多達500 萬比索(約128 噸,數字肯定有所夸大)的白銀流出歸因于中國,并試圖進行阻止。此外,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伊比利亞人手中爭奪中國市場的激進行動,嚴重擾亂了馬尼拉與中國之間的商業交通。1622 年,荷蘭占領澳門失敗,但翌年在臺灣建立熱蘭遮城后,荷蘭東印度公司取代葡萄牙人成為中日貿易的主要歐洲中間人。更重要的是,西屬美洲白銀開始與日本出口的白銀競爭,并在1610 年后數量陡增。
雖然明朝的一些政治家擔心對外貿易的不穩定影響,但另一些人認為,外國白銀對中國經濟有巨大價值。1630 年,在短暫恢復海禁政策的一段時間,福建人何喬遠在《請開海事疏》中督促當局對利潤豐厚的對外貿易敞開國門:
“東洋則呂宋,其夷佛朗機也。其國有銀山出銀,夷人鑄作銀錢獨盛。我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所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而已。是兩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國綾段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為用。湖絲到彼,亦自能精好段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悉得價可二三百兩。而江西之瓷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
盡管他錯誤地認為從馬尼拉運來的銀元是在菲律賓開采和鑄造的,但有關進口白銀對福建乃至整個中國實際經濟效益的論述卻正確無疑。外國市場需求確保了紡織工、陶工和商人的就業,提高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事實上,當局很快就撤銷了海禁令。到1640 年,中國白銀進口已達頂峰。德川家康的繼任者們已鞏固了對日本的統治,認為海外貿易不再有利可圖,尤其是隨商人而來的傳教士在勸說日本民眾皈依天主教方面成就驚人。1636 年起,幕府出臺“隔離政策”,包括限制民眾與歐洲人接觸、撤回日本商人海外貿易特權、驅逐葡萄牙人和傳教士、將中國和荷蘭人限制在長崎港活動等。西屬美洲方面,1640 年,葡西聯盟的瓦解斷絕了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殖民當局對1639 年馬尼拉華僑起義的血腥鎮壓,疊加荷蘭的掠奪,導致菲律賓與中國的貿易大幅減少。
如前所述,一些學者認為,從1630 年后開始的進口白銀急劇下降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種“危機”理論源自Chaunu 對西屬菲律賓貿易的開創性研究。他認為中國與歐洲的商業聯系將中國帶入了由大西洋區域主導的全球經濟軌道中。中國的歷史學家,受到這種世界經濟一體化概念的不當影響,接受了明朝要不斷輸入外國白銀以維持其經濟繁榮的假設。這個觀點最鐵桿的支持者Atwell 認為明朝末年白銀進口下滑是17 世紀危機至關重要的因素,最終導致明朝在1644 年滅亡。
然而,明朝最后幾年,中國的白銀進口量只是相對于1635-1639 年的高位有所下降。據估算,白銀年均進口量從1636-1640 年的115 噸下降到1641-1645 年的50 噸。而1626-1635 年白銀年均進口量約70 噸,與1641-1645 年間相近。即便我們以1636-1640年間的年均進口量為標準,由此計算1641-1645 年間白銀進口量下降了325 噸,但這也僅占此前一個世紀白銀進口總量7500 噸的約4.3%。如果按照表1 中更高白銀進口總量估計值計算,比例還將更低。這對當時中國的貨幣供給僅會造成有限的影響,不會產生危機理論所指的嚴重后果。
李隆生的研究為質疑白銀進口下降對明末經濟帶來災難性影響的觀點提供了新的證據。根據對中國出口貨物價值(尤其是生絲和絲綢)和船運數據的計算,認為明朝末年中國自日本進口的白銀數量處于很高的水平。直至1641 年,中國的白銀進口一直維持高位,此后則下降了三分之一。與此類似,李認為中國自菲律賓進口的白銀數量從1643 年才開始大幅度下降。李的結論與我一致,白銀進口量的下降主要是由國內社會和經濟動蕩導致的—廣泛爆發的農民起義以及1630 年間在多地爆發、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的疫病,而非全球經濟動蕩導致的貨幣供應中斷。
Atwell 沒有定量估計中國白銀進口總量,他的分析是基于貨幣數量論的簡單運用,存在一定缺陷。他認為,白銀進口量的下降疊加稅收因素,造成流通中的貨幣總量急劇緊縮,抑制了明朝的商業增長。由此導致的銀價上漲致使商品價格下跌,侵蝕了商業和農業收入。但價格走勢實際并未遵循這條軌跡。由于農業歉收以及由此引發的嚴重饑荒,大米價格在1638-1642 年間飆升。在這幾年中,原棉和棉布的價格確實下降了,但在1640 年后迅速恢復。而作為中國最重要出口產品的絲綢,其出口價格在整個17 世紀40 年代保持穩定。以白銀計價的大米價格大幅上升與流通中白銀短缺的觀點并不一致。
有關白銀短缺的爭論也與明末觀察到的另一種趨勢相矛盾,即白銀黃金比價的下降。以黃金計價的白銀價格在17 世紀上半葉穩步下降,并在明朝覆滅時下降到國際通行水平,因此,按照危機理論理應達到峰值的白銀價格,實際卻觸及了最低點。金銀比價的變化,一如糧食價格的通脹走勢,同中國國內白銀短缺的觀點并不一致。
三 裂縫:康熙蕭條(1660-1690)
中國進口外國白銀的真正轉折發生在明朝滅亡后的17 世紀最后三十年。有關馬尼拉帆船貿易的定量數據非常有限,但1640 年后,馬尼拉和中國之間的船舶運量大幅下降。根據海關記錄推斷,1640-1690 年的半個世紀間,只有約140 噸白銀從馬尼拉出口到中國。通過查閱日本對外貿易記錄中1648-1672 年間白銀出口數據可見,自日本出口至中國、主要用于進口絲綢的白銀在1648-1657 年間較為穩定,每年不到40 噸;然后在1658-1666年間飆升至每年75 噸。為應對白銀外流,德川幕府在1668 年禁止了白銀出口。盡管禁令在1672 年放寬,但幕府仍對國際貿易實施管制,包括迫使外國商人與政府背景的壟斷商行談判,以抑制白銀出口。1672-1683 年間,日本白銀出口量降至每年23 噸。1683 年追加實施的限制性舉措和1695 年實施的日本銀元減重使白銀出口幾乎停滯。
中國白銀進口受阻的另一個原因是清朝1661-1683 年間實行的海禁政策。該禁令是為顛覆鄭氏家族而采取的眾多舉措之一,彼時鄭家已在臺灣建立了政權。但是,這一禁令的執行一如明朝早期的禁令,時斷時續。更重要的是,從1660 年左右開始,一場歷史學家稱為“康熙蕭條”的曠日持久的經濟停滯,使得“白銀世紀”以來一直維持高位的白銀進口大幅下降。明末毀滅性戰亂導致的人口驟減、經濟動蕩影響深遠。從1655 年開始,價格、租金和土地價值普遍下降并一直持續到1690 年。大米和棉花價格幾乎同步下跌,表明大蕭條對農業和制造業的影響相近。
從時人的角度看,經濟蕭條是對外貿易中斷的直接結果,尤其是1661 年清朝海禁政策實施后導致白銀進口中斷。1680 年,江蘇布政使慕天顏將當時的經濟蕭條同1650 年的繁榮進行了對比:“猶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見市井貿易,咸有外國貨物;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銀錢,絕跡不見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財源之明驗也。”大約在同一時期,另一位著名官員靳輔向朝廷警告海禁的有害影響:“申嚴海禁,將沿海之民遷之內地,不許片板入海,經今二十年矣。流通之銀日銷,而壅滯之貨莫售。”他斷言:“天下賴以流通往來不絕者惟白銀為最”,他告誡朝廷解除對外貿易禁令,恢復王朝初期的繁榮。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認為“康熙蕭條”完全是由中國市場白銀供應中斷造成的。價格暴跌始于1655 年左右,較白銀進口中斷整整提前了十年。1655-1665 年間,白銀進口較前十年有顯著增長[2]。此外,1683 年海禁的結束并沒有立即緩解經濟蕭條的狀況。經濟持續低迷,價格和利率在1700 年之后才開始上升,由此開啟了長達一個世紀的通脹趨勢。18 世紀的經濟繁榮是由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所支撐的,主要是銅錢鑄造量的急劇增加,而非進口白銀的增長。
“康熙蕭條”時期漫長的通貨緊縮應從商品需求減少的角度解釋,而不能認為是白銀進口下降的結果。勞動力/土地比率的下降使得工資上升、租金降低,農業和土地投資吸引力下降。隨著人們繁榮預期的減弱,生產投資進一步減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勞動力短缺,手工業和制造業的失業率卻上升了。這進一步削弱了消費者需求,導致價格進一步下跌。通貨緊縮抑制了消費,而貨幣窖藏導致銅錢的價值與白銀同步上升,且上升幅度更大。
四 18 世紀白銀進口的復蘇
1683 年清政府征服臺灣、解除海禁后,中國自菲律賓進口的白銀逐漸增加。清政府一改長期以來對外隔絕的做法,允許民間對外貿易,取消了朝貢貿易。除了在1717-1727 年間出于國家安全考慮,對東南亞海上貿易實行短暫封鎖外,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整個18 世紀蓬勃發展。1751 年在倫敦出版的一本商業百科全書這樣描述中國的對外貿易:
“目前,通過與其他國家開展貿易,中國增加了致富的手段。它現在鼓勵而非阻礙不同國家前來通商,為它帶來最貴重的商品。同時,允許它的人民到外國眾多地方去,不論他們攜帶絲綢、瓷器、其他有趣的制成品,或是茶葉、草藥、糖和其他農產品。他們與東印度大部分地區進行貿易,抵達巴達維亞、馬拉卡、阿什、暹羅等。與全球各地貿易促成了它的繁榮和強大。”[3]
1760 年,英國來使請求更多自由貿易條件,惹怒了乾隆皇帝。此后,清朝將歐洲商人限定在廣州港活動,且必須通過政府指定的商行(十三行)進行貿易。盡管有這些限制,歐洲與中國的貿易在18 世紀下半葉依然蓬勃發展。中歐貿易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不是清政府的阻撓,而是歐洲國家以“東印度群島”特許貿易公司形式強加的壟斷商行。
18 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白銀進口也穩步增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放棄了打破荷蘭對東南亞香料壟斷的努力,在歐洲與中國的貿易中取得了主導地位。EIC 同時成為歐洲向中國市場出口白銀的主要供應者。1785 年以前,中國從歐洲進口的白銀隨英國對外貿易的起伏而波動,在“七年戰爭”和“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明顯下降。總的來說,外國白銀流入在整個18 世紀呈現穩定的大幅增長,從1719-1726 年間每年近100 萬比索,到1785-1791 年間每年近90 噸、350 萬比索。1785 年是外國白銀流入的重要轉折點。在廣州,不僅西方貿易總量在短短幾年翻了一番,當美國獨立后,美國商人繞過EIC 的壟斷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美國商人在獲取墨西哥白銀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同時,一些繞過EIC 壟斷從事亞洲貿易的英國商人也開始與EIC 爭奪中國貿易份額。此時,由于出口中國的棉花和鴉片數額急劇上升,EIC 轉而向倫敦采購以維持與中國的貿易,而放棄中國出口白銀。因此,18 世紀末到19 世紀初,中國白銀進口的驚人增長幾乎完全是由中美貿易的指數級增長推動的。
這些數據尚不包括通過帆船貿易和走私活動帶來的跨太平洋白銀流動,帆船貿易和走私活動在18 世紀也有所增加。清政府解除海禁后,馬尼拉和中國之間的船運量急劇增加(尤以福建廈門港為甚),在1720-1740 年間達到峰值。然而,我們缺乏18 世紀從菲律賓出口中國的白銀的定量數據,特別是大部分墨西哥白銀都是秘密運輸的。新西班牙和菲律賓之間商業往來在1712 年之前每年約200 萬比索,在1720 年后升至每年400 萬比索,均超過60 萬比索的皇家限額。同期,中國自歐洲進口的白銀年均僅100 萬比索。馬尼拉和墨西哥的皇家總督報告說,每年違禁品貿易通常超過200 萬比索。然而,在英國占領馬尼拉(1762-1764) 之后,菲律賓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突然下降。1785 年菲律賓皇家公司成立,1789 年馬尼拉港向歐洲開放。隨著馬尼拉與西班牙加的斯之間直航路線的建立,馬尼拉的海外貿易復蘇了。其結果是,跨太平洋帆船貿易早在1813 年正式暫停之前就已萎縮。1785 年以后,在帆船貿易幾近絕跡的同時,從拉丁美洲運送白銀到中國的熱潮開始了。
中國白銀進口的增長主要歸因于拉美尤其是墨西哥銀礦產量的飆升。18 世紀,墨西哥生產了全世界80%的白銀,在墨西哥鑄造的比索是國際貿易中最普遍的貨幣。墨西哥的白銀產量從1700 年的每年440 萬上升到1790 年的每年2100 萬比索。墨西哥造幣產量的峰值出現在卡洛斯三世(1759-1788 年)統治的后半期和他的繼任者卡洛斯四世(1788-1808年)統治期間,在1810 年伊達爾戈叛亂前夕達到了年產2400 萬比索。中國白銀進口量與墨西哥及秘魯礦山的產量同步上升。
如前所述,中國在18 世紀經歷了強勁的經濟增長。1700 年左右開始的人口復蘇在該世紀中葉急劇加速,到1800 年,中國人口比17 世紀末增長了近兩倍。同時,土地價格也隨著大米價格同步上漲[4]。農業和工業產量的增加促進了市場一體化和長途貿易。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8 世紀的中國,長途貿易的效率高于歐洲大多數國家。盡管長三角地區在整體市場效率方面落后于英國,但其市場效率水平與西歐大陸相當甚至有所超越。
拉美白銀的大量流入,無疑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并維持長期的經濟擴張。與此同時,清朝政府開發了中國西南部的銅礦,將銅錢的產量提高到17 世紀末的近10 倍。在1740-1785 年,年產銅錢的費用相當于125 噸白銀,同期白銀年均進口量為50 噸。也正是在此時,與貨幣數量理論預測截然相反,銅錢相對于白銀升值。大量鑄造的銅錢非但沒有降低其價值,反而增強了其作為交換和價值儲存手段的可靠性。銅錢的需求在高度商業化的地區最為強烈,如在18 世紀中期的長三角地區,銅錢取代白銀成為當地的本位貨幣。銅錢不僅在日常交易中較未鑄造的白銀更為方便,在耕地和房產等大額交易中也受到人們的偏愛。
五 銀元貨幣本位的建立
除了在18 世紀私人貿易中重新出現了銅錢本位(國家繼續在其財政收支中使用未鑄造的銀兩作為計價單位),中國人開始使用西班牙銀元作為交換媒介。此前,進口銀元會熔化后重鑄成銀錠。由于重鑄是由私人銀鋪而非政府當局進行的,中國遼闊的疆域上涌現出成色不同的銀錠。1792 年出版的《商賈便覽》詳細介紹了大大小小幾十個城市不同的銀兩標準。重量和成色高度統一的西班牙卡洛斯比索,即卡洛斯三世、四世統治時期發行的比索,開始充斥中國市場,逐漸成為交換媒介。
由于不熟悉比索銀元上的符號和銘文,老百姓摸索出一套自己的辨識方法。1772 年之前,卡洛斯三世比索采用可追溯至16 世紀哈布斯堡王朝的設計元素,正面為皇家徽章和西班牙皇冠,背面皇冠之下是代表新舊世界的兩個球形圖案,左右兩側豎立海格拉斯柱。在中國,這些硬幣被稱為“雙柱”銀元。1772 年,卡洛斯三世改變了比索的設計,正面為國王半身像,背面為波旁王朝徽章,左右兩側豎立海格拉斯柱,卡洛斯四世沿用這一設計。在中國,這些卡洛斯比索被稱為“佛頭”銀元。這并非因幣面人像與佛祖有任何相似之處,而是為凸顯人像的外國人身份。
18 世紀中期,西班牙銀元首先在外貿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廣東、福建成為本位貨幣。泉州的土地銷售和貸款合同清楚地展現了這種支付方式的變化。1730 年起,外國銀元開始在泉州取代紋銀。早在“佛頭”銀元首次發行的1788 年,它就已在泉州的民間合同中出現。當時,外國銀元在超過四分之三的土地交易中充當支付手段。1810 年以后紋銀在支付中逐漸消失,絕大多數交易以“佛頭”銀元支付。從1830 年起,中國經歷了幾個世紀以來的首次白銀凈流出,銅錢再次作為一種支付手段出現,但超過三分之二的合同仍以外國銀元計價。到1860 年間,外國銀元尤其是“佛頭”銀元重新獲得近乎完全的統治地位,直至1889 年中國首次發行官方銀元。
1800 年,卡洛斯比索成為長三角市場的本位貨幣。時人鄭光祖將外國銀元的優勢歸因于其支付中的實用性:
“乾隆初,始聞有洋錢通用,至四十年后,洋錢用至蘇杭。其時,我邑廣用錢票,兼用元絲銀。后銀價稍昂,乃漸用洋錢。中有馬劍者,重九錢四分,兌錢九百余文,雙柱佛頭并重七錢三分,兌錢七百余文。五十年后,但用佛頭一種,后以攜帶便易,故相率通用,價亦漸增。蘇城一切貨物漸以洋錢定價矣。”
許多學者證實了鄭光祖所言,即外國銀元已經成為市場交易的主要支付手段。然而,此時在長三角地區農村土地銷售合同中,仍如18 世紀中葉一般繼續使用銅錢,而在蘇州和上海城區房產銷售中則幾乎都用紋銀。因此,盡管外國銀元在交易中具有多種優勢,國內貨幣仍在土地買賣這種數額巨大但不頻繁的交易中占主導地位,凸顯出其價值貯藏功能。外國銀元的流通僅限于商業化程度較高的東南沿海省份,內陸地區較為少見。
最終,卡洛斯比索,以及此后的墨西哥共和國比索,在日常支付中應用的越來越普遍,逐漸取代銀兩成為事實上的本位貨幣。它的單位是“元”,代表圓形實心硬幣,與圓形方孔錢相對。今天,人民幣仍然以“元”為單位,而它最初是指墨西哥銀圓。
六 十九世紀白銀流向的逆轉
中國從西屬美洲進口銀元在19 世紀初大幅上升,每年約100 噸、400 萬比索。然而,1827 年后,持續流入幾個世紀的外國白銀流向逆轉,此后三十年,中國白銀持續外流。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白銀外流導致了中國1820-1850 年間的嚴重經濟危機,史稱“道光蕭條”。時人和一大批現代學者將白銀外流歸因于19 世紀上半葉鴉片進口的急劇增加,然而1827-1855 年間鴉片進口量只占到白銀外流數量一多半。林滿紅提出了一種不同的分析,強調全球貴金屬產量危機和經濟蕭條侵蝕了中國茶葉等產品的出口需求。以上兩種觀點都不能較好地解釋白銀流動的逆轉。相反,我們應更加關注中國和全球市場對特定類型貨幣需求的變化。
林認為,中國的白銀危機是由全球白銀產量顯著下降引發的。這一觀點源于Pierre Vilar 的重金主義分析,認為經濟周期與金屬貨幣的流動緊密相連。但Irigoin 的研究表明,中國白銀流入量的減少不能由墨西哥白銀產量或鑄幣量的下降來解釋。1810 年爆發的伊達爾戈叛亂,起初導致墨西哥鑄幣量大幅下降。1810-1819 年,墨西哥鑄幣量下降到此前的40%左右,但每年仍有800 萬比索。1821 年,墨西哥共和國建國后,鑄幣量逐漸從20 年代的每年900 萬比索升至30 年代的每年近1500 萬,并在40 年代達到每年1700 萬比索水平。1830 至1840 年,當中國的白銀外流達到頂峰時,墨西哥白銀產量和鑄幣量早已恢復到之前的水平。但是,相較于卡洛斯比索等西班牙銀元穩定的質量,墨西哥共和國鑄造的銀元質量千差萬別。資金短缺的政府和私人鑄幣者通常會在鑄造的銀元中摻假。在1857 年前鑄造了絕大多數銀元的墨西哥省級鑄幣廠,因鑄幣質量低劣而臭名昭著。
1810 年以后,拉美銀元質量和統一性的下降在銀元不規則的設計圖案上表現得尤為明顯。1820 及以后出版的中國商人手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仔細甄別。墨西哥產量最大的省級造幣廠Guanajuato 和Zacatecas 鑄造的銀元被中國人稱為魚鉤銀元,因為銀元上的造幣廠標識“G”和“Z”與“勾”字類似。中國商人手冊記載,魚鉤銀元最初質量較好,但隨時間推移,工藝和含銀量急劇下降。此外,這些銀元在中國被大量偽造,因此行用中存在大幅折價。
當時中國白銀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進口、出口貨幣循環存在顯著差異。進口幾乎全是西屬美洲銀元特別是卡洛斯比索,而出口則是以銀錠的形式運往英屬印度。其中一些銀錠在印度被仿鑄成卡洛斯比索,然后再運回中國。卡洛斯比索在1808 年后的停鑄,以及其它銀元的大幅折價,無疑是中國對外國銀元需求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1827-1857年間白銀進口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道光蕭條。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國內經濟危機,其特征是價格、實際工資、土地價值和貿易的持續下降。
可以肯定的是,供應方面的變化也導致了白銀流向的逆轉。1800 年后美國商人成為中國市場銀元的主要供應者,占中國白銀進口總量的83%。1810 年間,EIC 停止向中國出口白銀。但無論在西屬美洲殖民地獨立前、后,與之保持巨大貿易順差的美國商人都將大量的墨西哥銀元運往中國。1792 年,美國將白銀鑄幣價格提升到國際水平之上(白銀與黃金的兌換比率為15:1,而歐洲為15.6:1),以鼓勵墨西哥銀元流入美國。充足的墨西哥銀元供應促使美國在1806 年停鑄本國銀元,并宣布卡洛斯比索為法定貨幣。然而,這些流入的銀元大部分被重新出口到中國。1805-1834 年,美國向中國出口了1.3 億比索,占同期墨西哥鑄幣總量的三分之一。但1834 年,美國改變了貨幣政策,將白銀價格降低到國際水平以下,以吸引黃金流入。美國商人不再有充足白銀與中國進行貿易,對中國的白銀出口大幅減少。然而,盡管白銀貶值,墨西哥銀元繼續涌入美國市場。雖然美國政府試圖阻止質量低劣的銀元流通,人口激增和西部擴張還是刺激了對墨西哥銀元的需求。19 世紀50年代,加州的淘金熱緩解了對硬通貨的需求,美國終于在1857 年淘汰了質量低劣的墨西哥銀元,將其從流通中移除。巧合的是,同年中國也再次實現白銀凈流入。
卡洛斯比索于1808 年卡洛斯四世倒臺后停鑄,但中國市場對這類銀元的偏好延續了下來,它們相對于銅錢大幅升值。在中國的市場中心蘇州,卡洛斯比索對銅錢的兌換比率在1800 年左右穩定在1:850 左右,1840 年上升到1:1100-1200,并保持在1:1300-1400。與此同時,卡洛斯比索相對銀兩升值。18 世紀晚期,1 卡洛斯比索值白銀0.72 兩,較其含銀量0.684 兩高5%。到1840 年,卡洛斯比索值0.81-0.82 兩。在1855 年的頂峰,卡洛斯比索在長三角地區價格超過0.90 銀兩,即升水30%。
1864 年,清政府剿滅太平天國運動后,中國進入了經濟復蘇和重建的新階段。全球貿易一體化極大地增加了對中國出口商品如茶葉和絲綢的需求,同時國產鴉片一定程度上替代印度進口鴉片,使得對外貿易恢復順差。墨西哥銀元進口再次激增。和過去一樣,墨西哥鑄造的絕大多數銀元都出口到中國,這一趨勢在1873 年美國采用金本位制后加速發展。
19 世紀下半葉,墨西哥共和國銀元大量涌入,最終取代了卡洛斯比索,成為中國主要商業化地區的貨幣標準。1842 年,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采用墨西哥共和國銀元作為貨幣標準,但在進口銀元復興之前,這種貨幣在中國市場上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雖然上海的中外商人在1857 年采用了虛銀“九八規元”作為貨幣標準,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銀元仍然是當地商業的命脈。從1867 年開始,墨西哥銀元的匯率比以九八規元計算的官方價格高出約5%,在某些經濟困難的年份(1872 年、1876 年、1911-1912 年),其溢價升至12%或更高。1889 年,卡洛斯比索變得稀缺,商人們做生意無一例外地使用墨西哥銀元作為本位貨幣。然而,即便是在墨西哥銀元確立其主導地位后,卡洛斯比索和它的中國仿制品仍在零售貿易中頻繁使用。直至20 世紀初,卡洛斯比索在內陸商業中心,如安徽省會蕪湖,茶葉貿易的主要中心,仍保持溢價交易。
直到1889 年,中國政府,更確切地說是廣東省政府才開始發行銀元作為法定貨幣。廣東銀元是按照墨西哥共和國銀元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鑄造的。然而,由于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法定貨幣試驗的慘痛失敗,清朝政府拒絕了重新引入紙幣的呼吁。外國和國內的銀行都發行自己的紙幣,但這些紙幣的流通基本上僅限于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清朝末期,中國仍然嚴重依賴銀元作為其主要貨幣,而流通中各類紙幣只占貨幣供應總量的12%。拉丁美洲進口銀元占貨幣供應總量的近一半,并在中國貨幣體系中保持重要地位,直至1935 年白銀非貨幣化和法幣啟用。
七 結論
歷史學家非常重視中國對外國白銀的需求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本文反駁了早期研究關于“中國屈服于單一的國際貿易體系且高度依賴白銀進口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觀點。這種觀點僅從總量出發考察中國白銀的流入流出,未區分白銀的種類、用作何種商品貿易,因而未將白銀同其他多種流通中的貨幣分割開來。貨幣的多樣性和需求的異質性是中華帝國貨幣體系的持久特征,這提醒我們警惕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是一種無差異的總量概念的傾向。黑田明伸引發了人們對前現代世界中貨幣媒介“不對稱性”的注意,即協調貨幣的不同需求和不平衡的貨幣供應的難題。黑田特別關注帝國晚期中國貨幣使用空間范圍的變化,將本地市場的貨幣需求與長途商人對流動性強得多的貨幣媒介的需求進行了對比。銅錢往往會分散在本地市場,大部分時間處于閑置。相反,白銀的流動性更強,通過更高級別的貨幣流通渠道流轉,很少在本地市場停留。然而,從18 世紀中國存在的數十種不同的銀兩標準和19 世紀卡洛斯比索的緩慢進展中可以看出,白銀也受到強烈的地區偏好的影響。當我們認識到中國經濟中存在不同類型的貨幣需求,一個更微妙的貨幣流通格局出現。這給將白銀簡化為貨幣單位,將白銀流動僅僅作為與商品流動向對應的、用以維持貿易平衡的分析模型帶來新的挑戰。
自15 世紀白銀作為主要貨幣形式在中國興起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依賴外國進口白銀為貨幣供給提供彈性,促進商業增長。事實上,中國的貨幣體系與國際貨幣交換體系之間的聯系有著更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2 世紀。但是,認為1540 年以后外國白銀的流入使直至1800 年仍占世界經濟總量五分之一的中國經濟屈從于歐洲主宰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從16 世紀到19 世紀,國際白銀流動經歷了反復而重大的變化,外國白銀對中國經濟的意義以及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只有密切關注中國經濟對白銀的需求,以及更一般的貨幣需求,才能客觀認識全球白銀貿易對中國和拉美經濟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如何隨時間變化。
(限于篇幅,發表時刪除了部分表格與注釋,讀者可查看原文)
注釋:
[1]原稿見Glahn R V .THE CHANGING SIGNIFICANCE OF LATIN AMERICAN SILVER IN THE CHINESE ECONOMY,16TH–19TH CENTURIES[J].Revista De Historia Economica Journal of Iberian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2019:1-33.
[2]最近的研究表明,利率在清朝建立的頭20 年大幅上升,而1665-1680 年間則陡然下降,并維持歷史低位直至18 世紀頭10 年。在我看來,這表明康熙蕭條時期資本需求的下降。
[3]這段文字由英文版作者添加,并未出現在30 年前出版的法文原著中。
[4]利率在康熙蕭條后反彈,國內經濟動蕩導致利率在1740 年代-1750 年代再次上升(糧食歉收時期)。1765 年后直至18 世紀末,利率在遠高于17 世紀末期利率低點的水平上保持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