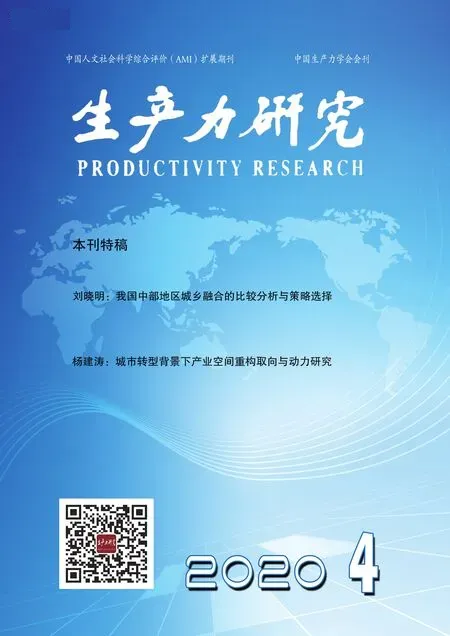補貼政策對中國企業專利行為的影響
——基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微觀證據
王 俊
(寧波廣播電視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浙江 寧波 315016)
作為創新產出的重要指標,近年來我國發明專利的申請量和授權量均出現了激增趨勢。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企業創新問題,并通過各種財政激勵政策,包括政府補貼、稅收返還等,鼓勵我國企業加快專利創新以增強市場核心競爭力。我國專利的“爆炸性”增長與政府補貼政策的扶持不無關系。但是,也有研究指出,我國政府補貼無效的現象時有發生,大量生產效率低的企業過度依賴政府“輸血”而缺乏創新動力(朱治理等,2016)[1]。許多企業獲得政府補貼后并未開展研發活動,而用于改善企業的經營狀況(徐保昌和謝建國,2015)[2];近年來新能源汽車企業的“騙補”風波,更使得關于補貼政策要不要繼續進行的爭論成為輿論熱點。當創新驅動戰略正如火如荼地開展時,有必要從微觀企業專利申請動機的角度,揭示補貼政策對企業創新的具體效用和作用機制,為補貼政策更“精”更“準”和如何更好促進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思路和建議。
一、文獻回顧
一些學者認為,補貼政策有利于企業專利產出的增加。Hewitt-Dundas 和Roper(2009)[3]的研究發現,財政補貼顯著促進了企業加大研發創新力度和開發重大新產品;Koeller(1995)[4]則基于制造業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補貼對創新績效有正向作用。熊維勤(2011)[5]論證了補貼政策對激發企業創新動力的積極影響。
另一些學者認為,政府補貼不利于企業創新。Wallsten(2000)[6]認為政府在遴選補貼對象時,往往更傾向于風險小、回報快的項目,而忽視對社會長期有益但短期回報率低的創新項目。余明桂等(2001)[7]指出,在中國的現實制度背景下,還會出現企業以尋租的方式“騙取”政府補貼的情況。王俊(2010)[8]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財政補貼對專利產出的激勵作用不顯著。
還有學者將以上兩種觀點結合起來,提出了“適度補貼”的理論。林州鈺等(2015)[9]以工業企業數據庫為研究對象,得出了政府對研發補貼和企業專利產出之間呈現“倒U 型”的結論,指出政府補貼對企業新產品創新的影響具有臨界值,低于臨界值時具有促進作用,反之則會產生抑制作用。毛其淋和許家云(2015)[10]則通過評估,發現只有適度補貼才能激勵企業的新產品產出,過高額度的補貼則會對企業新產品的生產起阻礙作用。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政府補貼能否促進企業專利產出仍有爭議。但是,在相關研究中,只是籠統地將專利數目作為衡量標準,少有文獻從創新動機的視角對補貼政策的有效性進行分類分析。事實上,除了以推動技術進步為目的的實質創新外,還存在著以其他利益為目的的創新活動,即“策略性創新”(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11]。本文即從動機角度,將專利產出分為發明專利產出和非發明產出,據此將專利行為劃分為“實質性創新”和“策略性創新”兩類;利用2014—2018 年A 股創業板的上市公司數據,考察補貼政策對企業專利行為的影響及內部機理,力圖為我國政府提高補貼政策的有效性,促進企業創新能力提升提供借鑒。
二、研究假設
雖然一些學者對我國補貼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但是隨著我國補貼政策的力度加大,我國專利出現大幅度的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設1:
H1:政府補貼與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專利申請數呈正相關關系。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以專利申請作為衡量標準的企業創新可能表現為策略性行為(Tan 等,2014)[12],意味著企業的“創新”僅僅是對政府政策的迎合,并沒有通過政府補貼來追求技術進步。Tong 等(2014)[13]的研究發現,在中國專利法第二次修訂后,政府鼓勵企業申請專利,結果是企業的實用新型和外觀專利顯著增加,而發明專利卻無明顯變化。一些地方官員為了政績發起“清零工程”,即通過政府補貼,促使曾經沒有申請專利的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在短期內迅速增加專利申請數,這就導致一些低質量甚至毫無價值的專利數增加,而發明專利申請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朱新力和張釵園,2012)[14]。鑒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設2 和假設3:
H2:政府補貼與創業板上市公司的非發明專利申請數呈正相關關系。
H3:政府補貼與創業板上市公司發明專利申請數的關系不顯著。
三、樣本選擇與模型設計
(一)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來自于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創業板企業,樣本跨度為2014—2018 年。在數據選取時,剔除了重要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選取了252家企業的1 041 個樣本。樣本分布如表1 所示。

表1 樣本年份分布
企業專利申請數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數據庫,政府補貼及其他變量來源于Wind 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通過查詢上市公司年報手工整理得出。
(二)變量定義
各變量的具體定義如表2 所示。其中,在對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申請數、非發明專利申請數進行1%的Winsorize 處理后,加1 取自然對數。

表2 主要變量定義
(三)模型設計
根據研究假設以及對以上變量的界定,且由于被解釋變量是0 為下限的拖尾變量,因此需采用Tobit 模型進行估計,模型設定為:

其中,α0為截距,α1為解釋變量的系數,α2、α3、α4、α5、α6、α7為控制變量的系數,β 為虛擬變量的系數,μ 為隨機干擾項。所有的分析都對公司代碼進行聚類分析,并采用Robust 調整標準誤差。在模型設定中,考慮到創新產出的滯后性,所有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均選取前一年的相關數據。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3 的結果看,政府補貼強度的均值為0.67%,這說明政府對我國創業板企業的補貼水平還不高,占企業資產的比例還比較低。專利產出的均值為2.406 6,標準差為0.989 7,說明創業板企業的專利申請數差異不是很大;對于策略性創新產出和實質性創新產出而言,以非發明專利為代表的策略性創新產出無論是在均值、中位數,還是在最大值方面,都大于以發明專利為代表的實質性創新產出,這說明我國創業板的企業實質性創新與策略性創新相比仍有不足,企業的專利申請大多體現在外觀和實用性上,發明專利申請不足,缺乏技術性的實質創新。

表3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全樣本回歸分析結果
利用統計軟件stata15.0 對Lnpatent、Lnpatentud和Lnpatenti 三個被解釋變量分別做Tobit 估計,表4為全樣本回歸分析的結果。

表4 全樣本回歸分析結果
從表4 的結果看,無論是擬合優度還是F 值,回歸模型的各參數估計都較好地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因此估計結果是比較可信的。模型的具體分析如下:
在模型(1)中,政府補貼Subsidies 的系數估計值為16.042 8,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說明在政府補貼的激勵下,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專利申請總數增加,即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支持了假設1 的結論。此外,企業規模、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和成長能力與專利申請均存在正相關關系,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強,創新的效果越好,且高成長性的企業往往有著較強創新能力;企業負債率對創新具有阻礙作用,負債越多,越不利于創新;值得一提的是,企業年齡與專利申請無關,這可能是由于創業板企業大多處在創業初期的特征所決定的。在模型(2)中,政府補貼對非發明專利申請數的影響系數為26.015 0,且在1%的水平顯著,說明每當政府補貼上升1%,創業板上市公司發明專利的申請數就會提高26 個百分點,政府補貼對企業非發明專利的申請具有較強的促進和激勵作用。對假設2 的結論做了驗證。此外,各控制變量對企業非發明專利申請數的影響與模型(1)一致。模型(3)驗證了政府補貼與企業發明專利之間的關系,系數為2.378 0,但是缺乏顯著性,這說明在政府的補貼激勵政策下,企業的發明專利申請沒有受到顯著的影響,這與假設(3)的結論有著高度的一致性。而從其他控制變量看,與模型(1)不同的是,企業流動比率對企業發明專利申請的影響不顯著;企業規模對發明專利的申請具有負向作用。從模型(1)-模型(3)的結論看,政府補貼激勵所致的企業專利申請數的增加,根本上是企業非發明專利申請的顯著增加,而并未對企業發明專利申請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對于創業板企業而言,我國政府補貼政策所激勵的只是非發明專利,而最能體現創新能力的發明專利激勵作用不大。
(三)分區域回歸
由于我國的區域發展存在一定差異,各地區政府對創新的重視程度和創新補貼的投入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對企業專利申請行為的影響也各不相同。因此,按照創業板企業所在的區域,劃分為東部和非東部兩類地區,其中,東部地區由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以及海南等11 個省級行政區域構成,其余的省級區域為非東部地區。
表5 顯示了東部和非東部地區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具體效應。與全樣本的回歸結果一樣,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非東部地區,政府補貼對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專利申請總數和非發明專利增加都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在影響系數方面,東部地區政府補貼的激勵效應要大于非東部地區。而對于發明專利的申請數而言,東部地區政府補貼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非東部地區則不顯著。這說明,東部地區在產業升級的壓力下,各級政府對企業創新都較為看重,政府補貼也有著較大投入。在政府補貼的激勵下,企業很容易產生通過“策略性創新”增加非發明專利而獲取補貼的行為,補貼的增加反而會對發明專利的申請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企業真正意義上創新能力的提高。而非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政府還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商引資和產業轉移上,對企業的創新的扶持力度不如東部地區,因而政府補貼的激勵效應較小,但是也存在著無法對發明專利申請產生有效促進的情況。

表5 分區域回歸分析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我國現行補貼政策所激勵的企業創新更多的是一種策略性創新而非實質性創新,在政府補貼的作用下,企業的專利申請數顯著增加,但卻是非發明專利的大幅上升,發明專利的申請數卻并未有明顯的提高。第二,東部地區各級政府已經將產業升級和企業創新作為重要的發展任務,政府補貼對企業專利總數和非發明專利的增加產生了較強的激勵作用,但是對發明專利的申請卻產生了“擠出”效應;而非東部地區則效果不顯著。第三,從深層次看,現行補貼政策導致一些企業為了獲取補貼而“創新”,即企業申請專利的目標是為了“獲補貼”“尋扶持”,而非真正提高創新能力,實現市場價值;因此補貼政策雖然引導企業創新,但卻未帶來企業“高質量”、實質性創新能力的提升,甚至在某些地區對企業發明專利的申請產生了“擠出”效應,給企業創新帶來了不利影響。
因此,結合本文的研究結果和我國政府補貼的現狀,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1.優化補貼形式,完善補貼機制。在補貼機制和方式的設計方面,關鍵要使政府和企業實現“激勵相容”。因此,鑒于我國企業的創新現狀,政府在制定補貼政策時,可以提高事后獎勵補貼的比例,根據企業申請專利的質量來進行補貼發放,逐漸減少事前的一次性R&D 補貼。
2.嚴格審核制度,做好成果甄別。在后期進行補助時,政府需要對企業的創新成果進行甄別,調高補貼的獲得標準,使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行為獲得獎勵。同時,中央政府可制定由第三方機構進行創新績效評價的機制,避免地方政府在發放補貼時與企業發生的“雙向尋租”活動,提高企業創新的整體質量。
3.注重市場機制,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重視創新,但也要采取合適的方式,不然就會如我國東部地區一樣,造成補貼對發明專利申請的“擠出”作用。市場是選擇企業行為的最好手段,政府應該逐漸轉變職能,不再單純通過政府判斷而是利用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來進行選擇,對市場篩選出的企業進行補貼,引導其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中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