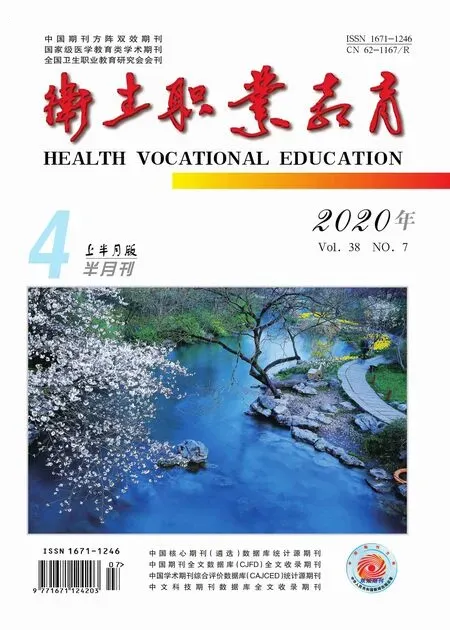抑郁情緒對(duì)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
章 琴,劉家僖,陳楚文,李雨欣
(湖南中醫(yī)藥大學(xué)人文與管理學(xué)院,湖南 長(zhǎng)沙 410208)
世界衛(wèi)生組織數(shù)據(jù)顯示,2017年全球有超過(guò)3億人罹患抑郁癥,抑郁癥已成為最常見(jiàn)的致殘因素[1]。抑郁癥狀作為評(píng)估個(gè)體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biāo)之一,表現(xiàn)了個(gè)體的心理應(yīng)激水平。研究顯示,大學(xué)生是抑郁癥的高發(fā)群體[2-3],其正處于從學(xué)校到社會(huì)的過(guò)渡階段,需要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面對(duì)來(lái)自家庭、學(xué)校、社會(huì)等多方面的壓力。大量研究表明,抑郁會(huì)對(duì)人際交往、生活質(zhì)量、社會(huì)功能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甚至誘發(fā)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等[4-5]。另有研究顯示,抑郁會(huì)對(duì)個(gè)體感知到的幸福感產(chǎn)生影響,較高的抑郁水平與較低的主觀幸福感顯著相關(guān)[6]。
隨著積極心理學(xué)的興起,心理學(xué)研究從以往的對(duì)病理性的研究逐漸過(guò)渡到對(duì)積極品質(zhì)如主觀幸福感、心理彈性等的研究。主觀幸福感是指?jìng)€(gè)體對(duì)自己的生活質(zhì)量和情緒感受做出的總體評(píng)價(jià)[7]。近年來(lái),在心理學(xué)、醫(yī)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公共衛(wèi)生政策等學(xué)科中,主觀幸福感扮演著越來(lái)越重要的角色[8-10]。與傳統(tǒng)的關(guān)注適應(yīng)不良行為、壓力和疾病等相關(guān)因素的心理健康模型相比,主觀幸福感是新型心理模型的組成部分,更關(guān)注適應(yīng)行為和健康[11-12]。研究發(fā)現(xiàn),主觀幸福感與身心健康存在密切關(guān)聯(lián),長(zhǎng)期處于抑郁狀態(tài)會(huì)影響其主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越強(qiáng)的人受到抑郁的影響越小,同時(shí)其生理狀況更好,經(jīng)濟(jì)水平更高,人際關(guān)系更好,工作滿(mǎn)意度更高[13]。
心理彈性是指在經(jīng)歷逆境后,個(gè)體具有的恢復(fù)并保持良好適應(yīng)系統(tǒng)功能的能力[14]。心理彈性在時(shí)間和同時(shí)代的網(wǎng)絡(luò)模型中占有中心地位,與抑郁、主觀幸福感密切相關(guān)[15-16]。研究表明,在臨床診斷為抑郁癥的成年人中,心理彈性存在很大差異[17]。一項(xiàng)Meta分析顯示,大約53%的抑郁癥患者在一年內(nèi)體驗(yàn)自發(fā)性緩解,表明許多抑郁癥患者具有持久的心理彈性[18]。良好的心理彈性能夠減少負(fù)性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較好地預(yù)測(cè)機(jī)體的心理復(fù)原能力,是有效緩解抑郁癥狀的重要保護(hù)性因素[19]。Lu等[20]發(fā)現(xiàn),抑郁與心理彈性呈負(fù)相關(guān)。Laird等[21]發(fā)現(xiàn),抑郁水平是顯著解釋心理彈性變異的因素。提升大學(xué)生心理彈性水平是預(yù)防抑郁的重要手段。心理彈性作為積極心理學(xué)領(lǐng)域的一個(gè)重要概念,亦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2-24]。研究發(fā)現(xiàn),工作心理彈性有助于增強(qiáng)員工的主觀幸福感[25]。高心理彈性的個(gè)體感受到的心理困擾更少,壓力更小,表現(xiàn)出更好的心理健康狀況,從而主觀幸福感更強(qiáng),低心理彈性水平的個(gè)體由于難以達(dá)到適應(yīng),其主觀幸福感偏低[26]。
既往研究表明,前人對(duì)于抑郁、心理彈性和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已經(jīng)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成果,然而關(guān)于三者的關(guān)聯(lián)還缺乏足夠的調(diào)查。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抑郁、心理彈性及主觀幸福感之間的具體關(guān)系,探究個(gè)體心理變化的具體過(guò)程,以期為日后抑郁個(gè)體的干預(yù)提供一定參考,從而提高大學(xué)生心理健康水平。
1 對(duì)象與方法
1.1 對(duì)象
2018年10—12月,以湖南省高校大學(xué)生為調(diào)查對(duì)象,共發(fā)放紙質(zhì)問(wèn)卷1 250份,剔除空白問(wèn)卷以及規(guī)律作答的問(wèn)卷后,回收有效問(wèn)卷1 157份;線(xiàn)上使用問(wèn)卷星收集問(wèn)卷444份,最后所得有效問(wèn)卷為1 452份。研究對(duì)象均知情同意。其中男生454人(31.3%),女生 998人(68.7%);大一 744人(51.2%),大二 250人(17.2%),大三236人(16.3%),大四222人(15.3%)。
1.2 研究工具
1.2.1 抑郁-焦慮-壓力自評(píng)量表簡(jiǎn)版(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DASS-21) 該量表分為抑郁、焦慮、壓力3個(gè)分量表,用于測(cè)量個(gè)體對(duì)抑郁、焦慮以及壓力等負(fù)性情緒的體驗(yàn)程度。本研究選取抑郁分量表來(lái)測(cè)量大學(xué)生抑郁程度,共7個(gè)題目。量表采用Likert 4級(jí)計(jì)分,0~3分分別表示不符合、有點(diǎn)符合、常常符合、完全符合,分?jǐn)?shù)越高表示個(gè)體抑郁程度越高。該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7]。
1.2.2 總體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GWB) 該量表共18個(gè)條目,包含對(duì)健康的擔(dān)心、精力、對(duì)生活的滿(mǎn)足和興趣、憂(yōu)郁或愉快的心境、對(duì)情感和行為的控制以及松弛與緊張6個(gè)因子。各因子所得分?jǐn)?shù)之和即為主觀幸福感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個(gè)體主觀幸福感越強(qiáng)。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8]。
1.2.3 Connor-Davidson心理彈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該量表共25個(gè)條目,包含堅(jiān)韌、力量和樂(lè)觀3個(gè)因子,用于描述個(gè)體過(guò)去一個(gè)月的感受。采用Likert 5級(jí)評(píng)分,0~4分表示從來(lái)不、很少、有時(shí)、經(jīng)常、一直如此。量表總分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個(gè)體心理彈性水平越高。中文版的心理彈性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9]。
1.3 統(tǒng)計(jì)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Amos 18.0統(tǒng)計(jì)軟件對(duì)所得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處理與分析。
2 結(jié)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yàn)
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Harman單因子檢驗(yàn),未旋轉(zhuǎn)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結(jié)果表明,共有9個(gè)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第一個(gè)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2.97%,小于40%的臨界標(biāo)準(zhǔn),故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抑郁、心理彈性及主觀幸福感得分在性別和年級(jí)上的差異
采用獨(dú)立樣本t檢驗(yàn)和方差分析及事后檢驗(yàn)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結(jié)果表明,抑郁得分在性別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男生抑郁得分顯著高于女生(P<0.01)。抑郁、心理彈性、主觀幸福感得分在年級(jí)上均存在差異,大一、大二學(xué)生抑郁得分顯著低于大三、大四,大一心理彈性得分顯著低于大三、大四,大二心理彈性得分顯著低于大三,大一主觀幸福感得分顯著高于大三、大四,見(jiàn)表1。
表1 不同性別和年級(jí)學(xué)生抑郁、心理彈性及主觀幸福感得分比較(±s,分)

表1 不同性別和年級(jí)學(xué)生抑郁、心理彈性及主觀幸福感得分比較(±s,分)
注:*P<0.05,**P<0.01,***P<0.001
性別年級(jí)項(xiàng)目男t值女大一大二大三大四F值LSD抑郁心理彈性主觀幸福感2.84**1.74 0.14 4.98±4.43 63.80±14.38 77.40±11.52 4.30±4.10 62.40±13.71 77.30±11.74 3.69±3.68 61.60±13.82 78.61±11.39 4.13±3.97 62.80±13.93 77.26±11.17 6.35±4.84 65.60±13.32 75.77±12.31 5.72±4.58 64.10±14.47 75.18±11.92 33.17***5.78**7.02***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一<大三、大四,大二<大三大一>大三、大四
2.3 抑郁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各因子得分的相關(guān)分析
采用皮爾遜積差相關(guān)對(duì)抑郁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guān)性進(jìn)行分析。結(jié)果表明,抑郁得分與主觀幸福感得分及對(duì)生活的滿(mǎn)足和興趣、精力、憂(yōu)郁或愉快的心境、對(duì)情感和行為的控制、松弛與緊張因子得分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r=-0.48~-0.35,P<0.05),與對(duì)健康的擔(dān)心因子得分未見(jiàn)顯著相關(guān),見(jiàn)表2。

表2 抑郁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各因子得分的相關(guān)分析(r)
2.4 抑郁與心理彈性總分及各因子得分的相關(guān)分析
積差相關(guān)分析結(jié)果表明,抑郁與心理彈性得分及堅(jiān)韌、力量、樂(lè)觀因子得分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r=-0.24~-0.13,P<0.01,見(jiàn)表3)。

表3 抑郁與心理彈性總分及各因子得分的相關(guān)分析(r)
2.5 心理彈性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各因子得分的相關(guān)分析
積差相關(guān)結(jié)果顯示,心理彈性總分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呈顯著正相關(guān)(r=0.36,P<0.01),除心理彈性各因子與對(duì)健康的擔(dān)心因子得分呈負(fù)相關(guān)以外,主觀幸福感其余各因子得分與心理彈性各因子得分均呈顯著正相關(guān),見(jiàn)表4。

表4 心理彈性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各因子得分的相關(guān)分析(r)
2.6 中介效應(yīng)檢驗(yàn)
中介作用分析以抑郁為預(yù)測(cè)變量,以心理彈性為中介變量,以主觀幸福感為結(jié)果變量,采用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進(jìn)行理論假設(shè)驗(yàn)證分析。結(jié)果表明,抑郁對(duì)主觀幸福感的負(fù)向預(yù)測(cè)作用顯著,心理彈性對(duì)主觀幸福感的正向預(yù)測(cè)作用顯著,抑郁對(duì)心理彈性的負(fù)向預(yù)測(cè)作用顯著,心理彈性在抑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yīng)顯著,見(jiàn)圖1。其中,中介效應(yīng)為0.023 4,總效應(yīng)為0.152,中介效應(yīng)占總效應(yīng)的比值為15.4%。模型擬合結(jié)果:χ2/df=8.93,RMSEA=0.074,NFI=0.95,CFI=0.96,IFI=0.96,TLI=0.93。

圖1 抑郁、心理彈性和主觀幸福感的中介模型
3 討論
3.1 男生和較高年級(jí)學(xué)生需要被給予更多抑郁方面的關(guān)注
本研究主要探討了抑郁、心理彈性及主觀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獨(dú)立樣本t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抑郁在性別上存在顯著性差異,男生抑郁得分顯著高于女生,說(shuō)明男生抑郁程度高于女生,這與前人的研究結(jié)果相符[30]。
方差分析及事后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不同年級(jí)學(xué)生抑郁、心理彈性、主觀幸福感總分均存在顯著性差異。關(guān)于抑郁和心理彈性,較低年級(jí)(如大一、大二)學(xué)生得分低于較高年級(jí)(如大三、大四);關(guān)于主觀幸福感,較低年級(jí)學(xué)生得分高于較高年級(jí),差異有顯著性。這可能是因?yàn)榇笕⒋笏膶W(xué)生即將面臨人生的重大選擇——升學(xué)和工作等,于是可能會(huì)更多地受抑郁情緒影響;不過(guò)與此同時(shí)高年級(jí)學(xué)生豐富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如社會(huì)實(shí)踐、項(xiàng)目實(shí)踐等)也有助于其提高心理彈性水平[31]。與高年級(jí)學(xué)生相比,大一新生相對(duì)較輕松,較易體驗(yàn)到主觀幸福感,其正走向獨(dú)立階段,需要逐步適應(yīng)大學(xué)生活,提高心理彈性水平。
3.2 抑郁、主觀幸福感與心理彈性三者密切相關(guān)
積差相關(guān)分析結(jié)果表明,除對(duì)健康的擔(dān)心外,抑郁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其他因子得分均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與心理彈性總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這可能是因?yàn)榇髮W(xué)生未經(jīng)歷太多病痛,對(duì)健康問(wèn)題不太重視。心理彈性總分及各因子得分與對(duì)健康的擔(dān)心因子得分呈負(fù)相關(guān),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及其他各因子得分均呈顯著正相關(guān)。也就是說(shuō)抑郁水平越高的個(gè)體心理彈性水平、主觀幸福感越低,心理彈性水平越高的個(gè)體體驗(yàn)到的主觀幸福感越強(qiáng),與以往研究結(jié)果一致[32-33]。
3.3 心理彈性在抑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起中介作用,提示應(yīng)加強(qiáng)心理彈性方面的干預(yù)
中介模型分析結(jié)果表明,心理彈性在抑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抑郁可以顯著負(fù)向預(yù)測(cè)主觀幸福感,表明抑郁程度不同的個(gè)體所體驗(yàn)到的主觀幸福感程度不同。抑郁是影響大學(xué)生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二者關(guān)系密切,在美國(guó)、德國(guó)、日本、韓國(guó)也發(fā)現(xiàn)了類(lèi)似的關(guān)系,具有跨文化性[34-36]。另一方面,個(gè)體抑郁對(duì)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也可以通過(guò)心理彈性來(lái)實(shí)現(xiàn)。低抑郁程度的個(gè)體具有良好的心理彈性,能夠從容面對(duì)生活事件,適應(yīng)良好,進(jìn)而在認(rèn)知和情感上對(duì)生活質(zhì)量有較好的評(píng)價(jià),具有更強(qiáng)的主觀幸福感。Manji認(rèn)為心理彈性是一種潛在的治療途徑[37]。Kong等發(fā)現(xiàn),心理彈性在眶額皮質(zhì)低頻波動(dòng)幅度與主觀幸福感得分之間起中介作用,在控制灰質(zhì)體積和區(qū)域均勻性的影響后,結(jié)果仍然顯著,這可能與功能性神經(jīng)腦活動(dòng)有關(guān),心理彈性介導(dǎo)自發(fā)性腦活動(dòng),從而對(duì)主觀幸福感產(chǎn)生潛在影響[38]。一項(xiàng)Meta分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積極心理學(xué)的干預(yù)能夠顯著增強(qiáng)幸福感[39]。Hendriks等發(fā)現(xiàn),在文化適應(yīng)方面的積極心理學(xué)可能是一個(gè)有效的干預(yù)措施,可以提高健康成年人的心理彈性水平,增強(qiáng)幸福感[40]。這就提示在對(duì)大學(xué)生進(jìn)行心理干預(yù)時(shí),應(yīng)注重提高個(gè)體心理彈性水平,可以通過(guò)認(rèn)知重評(píng)等改變大學(xué)生的消極認(rèn)知,從而預(yù)防或緩解抑郁癥狀,增強(qiáng)主觀幸福感。
- 衛(wèi)生職業(yè)教育的其它文章
- 特色心理育人工作的探索與實(shí)踐
——以北京衛(wèi)生職業(yè)學(xué)院為例 - 貧困地區(qū)鄉(xiāng)村醫(yī)生培訓(xùn)存在的問(wèn)題與對(duì)策建議
——以甘肅省隴南市鄉(xiāng)村醫(yī)生培訓(xùn)為例 - 高等醫(yī)學(xué)院校實(shí)驗(yàn)教學(xué)改革的思考與探索
- 多元數(shù)字化教學(xué)平臺(tái)在病理學(xué)實(shí)驗(yàn)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
- 淺談如何發(fā)揮模擬訓(xùn)練在診斷學(xué)教學(xué)中的優(yōu)勢(shì)
- 中職護(hù)理專(zhuān)業(yè)基礎(chǔ)課程中PBL案例的設(shè)計(jì)與撰寫(xiě)
——以中職基礎(chǔ)護(hù)理學(xué)PBL案例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