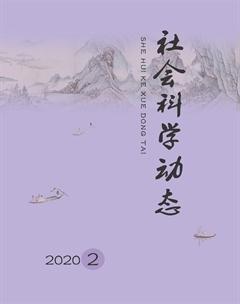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及碳交易市場機制探討
胡婉玲 王紅玲 張杲
摘要:“氣候智慧型農業”強調運用氣候適應性(智慧型)農業技術應對糧食安全、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三重挑戰。在我國以發電行業為突破口已經啟動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基礎上,探討建立中國農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用市場的手段推動我國氣候智慧型農業的快速發展,以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危機、環境污染以及糧食安全等問題,將是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重大創新。針對農業碳交易市場的建設及推廣過程中面臨諸多現實問題,本文提出了構建全國農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初步構想及建議,通過“一套政策體系、一組示范項目、一個共享平臺、一個交易中心、一個碳匯基金”搭建農業碳交易市場體系,以期對我國農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提供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氣候智慧型農業;農業碳減排;農業碳交易;市場機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及碳交易市場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9ZDA08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評價的實證研究——基于世界銀行在中國的示范項目”(項目編號:71871086)
中圖分類號:F30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0)02-0046-05
世界正處在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時代,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環境和氣候變化風險正在顯現,為經濟增長的長期前景投下了陰影。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2014)強調指出,人為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引起當前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全球二氧化碳濃度的升高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燒的排放和土地利用變化的排放所引起。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達席爾瓦在波恩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3次締約方大會時(2017年11月6日—7日)講話指出,農業不僅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也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至少有五分之一來自農業部門。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低碳綠色發展,控制和減少碳排放,許多國家都建立了碳排放權交易市場。2011年我國正式批準北京、上海、湖北等七省市啟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各試點單位在碳排放權交易軟硬件設施平臺建設與維護、重點工業企業配額分配方案、碳核查和交易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17年12月,國家宣布以發電行業為突破口啟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并由湖北省牽頭承建全國碳交易注冊登記系統、由上海市承建全國碳交易系統平臺。
相比之下,農業碳交易尚處于探索與起步階段,是國際碳交易領域的一個薄弱環節,目前只有新西蘭正在推行農業碳排放納入碳市場的方案。我國應結合財政政策、科技計劃,通過稅費減免、財政扶持、引入社會資本等方式,增加對農業碳減排碳交易的公共投入。相關部門應支持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關鍵技術的研發、示范和推廣工作,推動農業碳匯項目的開展;借鑒清潔發展機制,設立農業碳基金,發展農業碳交易機制,并通過規范自愿減排的流程、評定機構、規則限定等內容,搭建農業碳交易市場平臺,完善農業碳交易市場機制。
一、農業碳排放與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
ACIL Tasman Pty Ltd(2009)測算了美國、加拿大、歐盟、新西蘭、印度等國的農業碳排放,發現農業碳排放占碳排放總量的比重在不同國家差異較大,原因可能是各國的農業生產方式不盡相同。王劼等(2018)測度32個國家(含中國)的農業碳排放效率并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碳排放效率多為無效率狀態,市場規模、人力資本和機械化程度三個變量對樣本國家的農業碳排放效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①。
董紅敏等(2008)通過對文獻資料和大量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得出中國農業活動產生的甲烷和氧化亞氮分別占全國甲烷和氧化亞氮排放量的50.15%和92.47%,農業源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7%②。李波等(2011)基于農業生產中六個主要的碳源,測算了我國1993—2008年農業碳排放量,研究發現,1993年以來我國農業碳排放處于階段性的上升態勢;農業碳排放總量較高地區主要集中在農業大省,農業碳排放強度較高地區主要集中在發達城市、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和中部農業大省③。黃燕等(2018)測算了中國2000—2015年農業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結果表明,中國農業碳排放量總體呈波動上升態勢,農業碳排放強度呈上升發展態勢;中國農業碳排放影響因素由大到小依次為產業結構、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受災程度、農業勞動力規模、人均耕地面積、勞動力文化水平④。姚成勝等(2017)測度了我國31個省區的畜牧業碳排放,結果表明,2000—2014年,我國畜牧業碳排放總量由12669.899萬噸增長到13189.955萬噸,年均增速0.288%,其中畜禽胃腸發酵和糞便管理系統產生的碳排放是其主要來源,兩者共占畜牧業碳排放總量比重達74.48%—79.5%⑤。劉晃等(2010)研究表明,中國水產養殖的CO2排放總量約為988.6×104t,占全國CO2排放總量的0.17%;水產養殖CO2排放強度為0.253kg·美元-1。⑥ 李晨等(2018)研究表明,中國漁業碳排放效率總體上不斷上升但整體水平不高,高效率省份呈現出由分散布局向東部沿海和長江流域集聚的顯著趨勢,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漁業碳排放效率依次遞減且差距逐步減小;漁業碳排放效率與漁業節能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對外開放程度和漁業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與資源稟賦呈負相關關系⑦ 。
為應對日趨嚴峻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歐美國家于本世紀初提出發展“低碳經濟”,“低碳農業”是“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糧農組織進而提出“氣候智慧型農業(Climate-Smart Agriculture,CSA)”概念(FAO,2010),這種全新的農業發展理念強調運用氣候適應性(智慧型)農業技術應對糧食安全、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三重挑戰,實現作物產量更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更強、農業碳排放量更低等涵蓋經濟和環境的多重綜合性目標⑧,是對“生態農業”、“綠色農業”、“循環農業”、“低碳農業”等發展理念的融合、創新和超越。氣候智慧型農業的本質(或基礎)是氣候智慧型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氣候智慧型農業的“作物產量更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更強、農業碳排放量更低”三個方面,也主要是通過氣候智慧型農業技術的應用才體現出來⑨。
中國近年來開展了一系列氣候智慧型農業項目實踐,并進行推廣示范。作物輪作模式、農藥化肥“一控兩減”、稻鴨共作、稻蝦共作、畜禽養殖優化技術、畜禽糞有機肥資源利用等方面的農業碳減排實踐成效明顯。Yang Xiaolin et al(2014)對5種種植模式的碳足跡進行評價,結果均顯示為:麥玉模式>糧油模式>糧棉油模式>糧棉薯模式≈棉花連作模式;研究結果還表明,在華北平原發展多樣化的種植制度是該地區節能減排的最主要途徑⑩。姜雨林等(2018)研究小麥—玉米、春玉米連作、小麥—豆科、小麥—玉米—春玉米、小麥—玉米—大豆5種輪作模式,結果表明,禾豆科輪作相較于傳統禾本科輪作具有更好的固碳減排效益,其中麥豆輪作固碳減排效益最高{11}。Zhanbiao Wang et al(2017)分析了我國1993—2012年作物生產溫室氣體排放及其構成,發現我國作物生產中化肥為第一大排放源;在不考慮作物對不同化肥類型吸收利用差異的情況下,如果采用最低排放類型化肥的施肥策略,中國作物生產平均每年將減少1.27億噸二氧化碳當量{12}。展茗等(2009)研究結果表明,相對于常規稻作, 稻田養鴨能有效降低甲烷的溫室效應, 說明在中國南部稻鴨共作是一個減緩全球溫室效應的可行措施{13}。徐祥玉等(2017)發現,稻蝦共作可大幅度降低CH4排放,特別是降低因秸稈還田帶來的溫室效應增強的影響{14}。
二、運用市場機制推進農業碳減排的重要意義及面臨的問題
大力發展氣候智慧型農業,通過農業碳交易的手段促進減少碳排放,促進解決氣候變暖等相關問題,是新時代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運用市場機制推進農業碳減排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農業碳減排事關我國兌現碳減排國際承諾。當前,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全球溫室氣體的重要排放源之一,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至少有五分之一來自農業部門。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快速提升,碳排放量越來越大,對世界氣候和國內自然環境的影響不斷加大。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我國向全世界作出了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承諾。目前我國碳減排活動主要聚焦在工業行業,實際上,農業碳減排潛力也十分巨大。其中,農業中畜牧養殖以及化肥所排放的甲烷和二氧化氮分別占全國總量的50%和92%。因此,有效地減少農業溫室氣體排放,有助于實現我國碳減排的國際承諾。
二是農業碳減排事關我國農業可持續性發展。目前我國農產品產出量低,品質無法保障,究其原因主要是土壤地力下降、肥料利用率低、病蟲害嚴重、水資源短缺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低碳農業、尤其是氣候智慧型農業的發展,農業已開始由化學肥料、化學農藥等的高投入和高能耗的農業生產模式,向生態化、有機化、低投入、低能耗、高效益的農業生產模式轉變,通過成本控制,低投入、高產出,不僅實現了農業發展的經濟效益,同時由于農業生產中化學元素的投入的減小,不僅有效緩解了化學試劑對農產品的污染,也保護了生態環境,實現了農業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轉變,保障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15}。
三是建立市場化的農業碳減排機制是加快構建農業生態經濟體系的重要探索。2018年5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要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其中包括加快建立健全“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2018年7月3日,國家發改委發布規范性意見指出,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中最靈敏、最有效的調節機制。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完善資源環境價格機制,是大勢所趨。近些年來,我國促進綠色發展的價格政策不斷出臺,對節能環保、優化產業結構等發揮了重要作用{16}。然而,目前我國以低碳農業為代表的農業生態體系的環境效應、經濟效應不足,氣候智慧型農業實踐示范還處于初級階段,推廣成效不顯著,單純運用財政資金補貼或轉移支付形式的生態補償等方案的可持續性較弱。為此,建立中國農業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用市場的手段推動我國氣候智慧型農業的快速發展,以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危機、環境污染以及糧食安全等問題,將是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重大創新,為我國農業碳減排和低碳農業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路徑。
當然,農業碳交易市場的建設及推廣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推行過程中還面臨諸多現實問題。
一是支持農業碳減排交易的配套政策缺位。目前,國家農業主管部門主要是參與和支持農業碳減排項目方法學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化市場管理思路和配套政策支持,難以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在地方層面,僅有湖北試點碳市場以精準扶貧的名義支持農業碳減排項目通過抵消機制進入市場交易,其實際用于履約抵消的農業碳減排量(CCER)約為107萬噸,實現經濟收益超過1600萬元{17}。反觀林業碳匯交易方面,國家林業局先后設立了碳匯管理辦公室,建立了林業碳匯計量實驗室,出臺了《關于推進林業碳匯交易工作的指導意見》(林造發〔2014〕55號),支持設立了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先后募集境內外資金4億元,在中國20多個省(區、市)資助實施和參與管理的碳匯造林項目達120萬畝,一大批林業項目得以開發并進入試點碳市場和自愿碳市場獲利{18}。
二是我國農業碳減排交易市場尚未形成。目前,我國不論是全國碳市場還是試點碳市場都主要對工業企業進行碳排放管控,未將農業納入強制控排體系,農業碳減排項目(目前主要是林業碳匯項目)僅以抵消工業排放的形式參與交易,分散在全國7大試點碳市場(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深圳)和若干個自愿碳市場(湖北、貴州、北京等)中交易,且因為價格和開發成本等因素交易量相對極少(占比不足0.5%)。與此同時,由于上述7個試點市場相對獨立,同一類型農業碳減排項目交易的價格差異較大,未能形成統一的市場價格,導致我國農業碳交易呈現出極度分散的市場格局。
三是我國農業碳交易缺乏“中國本土基因”。目前,我國農業畜禽飼養、農田種植等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因子的統計與研究工作非常薄弱,相關領域的研究統計基本參考國外溫室氣體排放因子數據進行估算,而未形成具有公信力的中國本地化“農業排放因子數據庫”,導致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基礎數據薄弱、測算質量不高,這也是我國未能將農業納入強制控排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我國農業碳減排項目方法學覆蓋不全面。目前,已在國家主管部門備案的農業碳減排項目僅為25個,主要分為甲烷回收類型(污水或糞便、沼氣、堆肥以及廢水處理等)、生物質類型(廢棄物、不可再生生物質等)、及能效和燃料轉換措施等。例如,湖北省農業廳主推技術指南中推廣的秸稈還田、測土配方施肥、化肥深施、水稻少耕免耕等技術具有提高土壤固碳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作用,但現有的方法學涉及面窄、研發能力不足,不能完全覆蓋現有低碳農業領域,導致無法發展成碳減排產品交易。
另外,我國農業碳減排項目較分散、年均減排量較少等特點,導致高昂的開發成本及交易成本也阻礙了農業碳交易市場發展{19}。
三、構建全國農業碳交易市場的初步構想及建議
借鑒新西蘭農業碳交易的模式,結合我國農業特點和實際情況,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業碳交易市場體系,運用市場手段合理分配農業政策資源,通過農業碳金融工具進一步支持農業減排項目的推廣和示范。初步構想如下:
一是納入控排范圍。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則,初期將有一定數據基礎且排放和污染較大的規模以上畜禽飼養業(生豬、雞、牛、羊等)納入強制控排體系進行溫室氣體管控。逐步將農田種植等其他農業碳排放領域納入強制控排體系。
二是交易主體。初期建議將強制控排的畜禽飼養主體和碳減排項目業主方納入市場主體,并引入專業化投資機構參與市場。待條件成熟后,可以適時考慮將合格投資人納入市場主體。
三是交易產品。初期可以上市“農業碳排放配額”和“農業碳減排項目”兩個現貨交易產品。待市場足夠成熟后,可以考慮開展上述產品的期貨交易。
四是交易市場。初期可依托現有基礎較好的碳交易試點地區建立試點農業碳市場,試點成熟后過渡成為全國性農業碳市場,力爭將全國性農業碳市場逐步發展成為包括強制碳市場、自愿碳市場、金融市場等在內的多層次市場體系。同時,探索設立“國家農業碳匯基金”,進一步支持農業碳減排項目的實施,進一步激活市場流動性。
五是分配方式。根據強制控排農業項目的排放數據基礎和條件,可以設計“基準線法”和“歷史法”兩種“農業碳排放配額”分配方式。其中,“基準線法”根據同一類型農業項目的單位產品強度值,設定這一類型農業項目的年度先進“基準值”,同一類型農業項目根據年度產量和“基準值”確定其分配配額;“歷史法”根據畜禽飼養業主體的歷史排放數據,結合該類型的年度減排下降系數確定其分配配額{20}。
六是履約和抵消機制。每個自然年度結束后,農業主管部門委托第三方機構對所有強制控排農業項目進行排放數據核查,確定其實際碳排放量并按這一數據繳還相等數量的“農業碳排放配額”,履行其減排義務。同時,參考歐盟碳市場和中國試點碳市場的抵消機制,將現有25個農業碳減排方法學開發的項目納入農業碳市場抵消機制,逐步探索將有害投入品減量(化肥、農藥、農用薄膜等)、節水灌溉(農作物噴灌、微噴灌、滴溉等技術)、農魚共生(稻蝦、蓮鱉、茭鰍、菱蟹共生等)、種養廢棄物再利用(秸稈還田、秸稈飼料、秸稈建材、畜禽糞便制肥等)這四類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減排項目納入抵消機制。具體抵消比例,可以根據農業減排項目的經濟性、減排貢獻或生態價值等因素設定不同權重。
為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碳市場建設,具體建議如下:
首先,強化頂層設計和機制建設(一套政策體系)。農業農村部應抓緊將農業碳交易納入農業發展戰略規劃中,探索出臺農業碳交易支持政策,協調各部委統籌各類資源支持農業碳交易市場發展,建立農業碳減排技術交流與碳市場對接國際合作機制,進一步提升我國農業碳減排技術和碳市場管理水平。
其次,鼓勵推廣各類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示范項目(一組示范項目)。利用國際合作資金、國家和地方相關資金,廣泛開展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相關項目示范。鼓勵地方先行探索開展具備中國特色的農業碳減排項目方法學的研究,開發“便捷、低成本”的農業碳減排核證方法學。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創新支持農業碳減排項目。
第三,搭建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成果共享平臺(一個共享平臺)。農業是碳減排和固碳增匯的重要領域,培育和搭建氣候智慧型農業碳減排研究成果共享平臺,鼓勵更多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和企業參與到這個平臺中,制定成果共享的工作機制和工作規范,促進農業碳減排領域技術和成果的開發與共享{21}。
第四,設立全國農業碳交易中心和國家農業碳匯基金(一個交易中心、一個碳匯基金)。國家和湖北省應共同支持前期具備較好農業碳交易基礎的湖北碳排放權交易中心設立“全國農業碳交易中心”、設立規模不少于5億元的“國家農業碳匯基金”,形成全國統一的農業碳交易價格和市場{22}。
注釋:
① 王劼、朱朝枝:《農業部門碳排放效率的國際比較及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32個國家1995—2011年的數據研究》,《生態經濟》2018年第7期。
② 董紅敏等:《中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與減排技術對策》,《 農業工程學報》2008年第10期。
③ 李波等:《中國農業碳排放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分解》,《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年第8期。
④ 黃燕等:《中國與巴西農業碳排放動態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世界農業》2018年第6期。
⑤ 姚成勝等:《中國省際畜牧業碳排放測度及時空演化機制》,《資源科學》2017年第4期。
⑥ 劉晃、車軒:《中國水產養殖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的初步研究》,《南方水產》2010年第4期。
⑦ 李晨等:《中國省域漁業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時空分異》,《經濟地理》2018年第5期。
⑧ 王一杰等:《氣候智慧型農業在我國的實踐探索》,《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8年第10期;胡婉玲、任然、王紅玲、柏振忠:《氣候智慧型農業在中國的實踐、問題與對策》,《湖北農業科學》2018年第20期。
⑨ 索榮:《“氣候智慧型農業”的嘗試》,《農資導報》2014年11月14日;ICF International, Charting a Pathto Carbon Neutral Agriculture: Mitigation Potential for Crop Based Strategies, 2016, pp.8-30.
⑩ Yang Xiaolin, Gao Wangsheng et al., Reducing Agricultural Carbon Footprint Through Diversified Crop Rotation System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4, 76(3), pp.131-139.
{11} 姜雨林等:《華北平原不同輪作模式固碳減排模擬研究》,《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12} Zhan-biao Wang, Comparis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Types in Chinas Crop Produc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141, pp.1267-1274.
{13} 展茗等:《稻鴨復合系統的溫室氣體排放及其溫室效應》,《環境科學學報》2009年第2期。
{14} 徐祥玉等:《稻蝦共作對秸稈還田后稻田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7年第11期。
{15} 丁啟坤:《基于可持續發展視角的低碳農業發展探究》,《南方農業》2015年第27期。
{16} 陸婭楠:《國家發改委發布規范性意見 以價格改革促進綠色發展》,《人民日報》2018年7月3日。
{17}{22} 何紅衛、樂明凱:《湖北設立“全國農業碳交易中心”正當其時——訪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王紅玲》,《農民日報》2019年3月8日。
{18} 張興國:《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躋身全國先進》,《中國綠色時報》2015年12月25日。
{19} 孫芳、林而達:《中國農業溫室氣體減排交易的機遇與挑戰》,《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12年第1期。
{20} 齊紹洲等:《低碳經濟轉型下的中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經濟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頁。
{21} 劉月仙:《全球農業碳排放趨勢及中國的應對措施》,《世界農業》2013年第1期。
作者簡介:胡婉玲,湖北省宏泰國有資本投資運營集團有限公司,湖北武漢,430077;王紅玲,湖北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62;張杲,湖北碳排放權交易中心,湖北武漢,430064。
(責任編輯? 辰?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