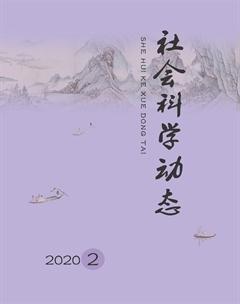芻議《司馬法》“禮戰”理念及其精神價值
摘要:《司馬法》是一部發軔于三代時期的法典型軍事典籍,其豐富的思想內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對先秦兵家思想的發展乃至我國傳統軍事思想的構建,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將《司馬法》置于先秦“兵儒合流”思想史視域來看,其“禮戰”理念及價值立場貫穿于先秦時期的軍事戰爭實踐,構成其重要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考量的依據。梳理和把握《司馬法》的“禮戰”理念及先秦軍事實踐,對于我們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深刻理解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質,回應新時代加強我軍思想政治工作建設的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司馬法》;禮戰;政治工作
中圖分類號:B82-0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0)02-0098-05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十余次引用過“國雖大,好戰必亡”這句意蘊深遠的古語,在談及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時也反復強調“能戰方能止戰”,而“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也屢被權威媒體引用以警示“和平積習”之危害。這些思想和語句都源于《司馬法》。《司馬法》作為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兵書之一,保存了大量古樸雋永的先秦軍事禮法思想,特別是其獨樹一幟的“禮戰”理念,深刻影響了后世兵學的發展。如果說“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根與‘魂”①,那么也可以說,以《司馬法》為代表的先秦兵家典籍構成了中華傳統軍事思想的“根”和“魂”。對于這樣一部被歷史所證明、被今人所認可的上古兵書,理應引起我們足夠重視和深入探究。
一、《司馬法》“禮戰”理念的形成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幾乎等同于戰爭史,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里,絕大多數諸侯國都卷入了戰爭的泥潭,現存的文獻中記載了該時期共發生了762次戰爭②,爆發之頻繁,規模之慘烈,在中國歷史上無出其右。孟子對此描述道:“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離婁上》)戰爭的慘景躍然紙上。特別是春秋中期以后,周王室的日漸衰微使得作為社會穩定基石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逐步土崩瓦解,而建構其上的禮法制度和道德規范也自然隨之沒落。擺脫了價值束縛的戰爭猶如脫籠野獸,其規模和殘酷程度與日俱增,動輒上萬人的坑卒、斬首屢見不鮮。根據《史記·秦本記》所載,僅秦國獲勝后所進行的斬首坑殺就有15次,共計150余萬人,而秦國失利、其余六國間互相攻伐所帶來的人員傷亡可想而知。戰爭形勢的劇變促使兵家思想也隨之轉變,《孫子兵法》中“兵者,詭道”(《孫子兵法·計篇第一》)、“兵以詐立”(《孫子兵法·軍爭篇第七》)等就是這一時期兵家思想“狂狡有作”的最好寫照。與此不同的是,《司馬法》并未趨同于時代的變更,而是堅奉“古禮”為圭臬、“仁義”為根本,重視戰爭中的道德因素,遵奉名目繁多的古代戰爭制度,使戰爭呈現出高度儀式化的“禮戰”特質。
“禮戰”,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一種矛盾交織融合的產物。先秦時期的“禮”承自上古三代之遺風,是當時社會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而戰爭則始終是人類社會矛盾斗爭的最高表現形式。“禮戰”就是將“禮儀”的精神投射至戰場,用以規范限制戰爭行為。《司馬法》中記載的諸多這一時期繁瑣而考究的禮儀規范,使得戰爭頻率及規模在總體上得到遏制。但很明顯,在戰爭實踐中,“禮”與“戰”終歸還是一對矛盾范疇,“仁愛”與“殺人”、“愛民”與“滅國”、“忠義”與“詭詐”等等一系列互為抵牾的概念,其本質上的沖突無法消解,歸根結底在于“禮”所追求的“崇禮尚義”和“戰”所直面的“生死存亡”間的巨大溝壑。可以想見,在刺刀見紅的沙場上恰如其分地把握好“禮”之原則,在奮勇爭勝的同時做到“揖讓而升”,其難度可想而知。這無疑是“禮戰”所直面的困境。
《司馬法》對于戰爭的理念,勾勒出了“禮戰”的理想形態,在“禮”與“戰”間做出了富有智慧的權衡取舍。從戰爭過程來看,《司馬法》講道:“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論述了三皇五帝以來,對待潰敗之敵不可深追,跟蹤敵人不能尾隨過近的基本戰術原則。一方面,從戰爭視角來看,這樣的戰術原則是基于實戰角度考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就是為了避免被敵人埋伏包圍的危險情況發生。另一方面,從道德視角審視,給潰退之敵留以生路,彰顯了王道之師的仁義風范,也側面反映出當時戰爭的首要目標依然是為達成政治目的,而非對敵趕盡殺絕,這是“禮制”在戰場上的生動實踐。對此,《司馬法》用“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進行總結:“禮”,是用禮法去管理教育部隊,約束戰爭行為,遵守交戰秩序③;“仁”是戰爭勝利的前提條件,通過彰顯“仁”才能得到百姓的真正擁護,甚至敵國軍民的認可,即“仁者無敵”。“禮”與“仁”二者密不可分,“仁”是“禮”的價值內核,“禮”是“仁”的外在表現。這樣的軍事倫理思想貫穿全書。如在“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亂”(《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這段話中,從“禮”的角度來看,這樣做的目的在于通過較為緩慢的行軍節奏,保證交戰時陣型的穩固,以期獲得戰爭主動;從“仁”的角度來看,較為舒緩的行軍速度亦體現了對士卒的體恤仁愛。在戰后問題處理上,《司馬法》并非從功利角度去破國毀城,謀求一時私利。相反,它倡導獲勝方要嚴格約束部隊,積極協助戰后重建工作,幫助敵國修明內政,使之重新回歸禮樂文化規制內——“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司馬法·仁本第一》)。這樣的行為,與孔子所倡導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論語·堯曰篇第二十》)思想不謀而合,彰顯了“討不義”戰爭的本質所在。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抱以這樣近乎毫無私心的戰爭初衷,其實也有更為深遠的戰略考慮:滅一國,萬國怨,會破壞歷代相傳的禮制法規,動搖統治根基,若引起負面示范效應則必定天下大亂;存一國,萬國喜,在政治上、道義上占領絕對制高點,起著正面的示范效應,利大于弊。
二、《司馬法》“禮戰”理念的價值內涵
康德曾經說過:“一個出于義務的行動,其道德價值不在于它所應當借此來實現的意圖……而僅僅取決于行動無關乎欲求能力的任何對象而據以發生的意愿的原則。”④ “禮戰”同樣如此,在激烈交鋒的戰場中依舊能夠保持禮讓克制、彬彬有禮,行為背后流露出的是對“人”的高度觀照。先秦時期,統治階層構筑了以禮樂文化為載體的上層建筑,規范了每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應扮演的不同“角色”——從天子到平民,士農工商各居其位,各司其職,“不逾矩”(《論語·為政篇第二》)即是此時的社會道德規范。此時的“人”涵括了人的現實生命和道德品行雙重指向,這也是“禮戰”的戰爭邏輯得以成立的關鍵所在,最為直觀的體現便是對生命與人格尊嚴的高度關切。
《司馬法》所記載的各類“軍禮”內容駁雜、條目繁多,對生命與人格尊嚴高度關切的主旨始終貫穿全文,即便在戰時,《司馬法》也將這份關切無差別地投射到敵我雙方軍民,體現出了強烈的人本精神。《司馬法》規定:“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司馬法·仁本第一》)在交戰中,既考慮到本國人民民生:不在疫病流行時興兵,防止征兵、行軍等過程中疫病蔓延;同時還考慮到敵國人民利益:不乘敵國國喪、饑荒期間發起進攻,避免敵國在匆忙應戰中蒙受更大損失;甚至通盤兼顧了敵我雙方人民利益:在冬夏大寒大暑的季節中,一般不興兵,因為此時行軍打仗必定給敵我雙方軍民造成更大苦難。如果說對于我方軍民的關懷尚屬愛惜民生,是仁義治軍的體現,那么在近乎零和博弈、有你無我的戰場中,不從收益最大化的功利角度去考慮戰事,仍對敵國軍民安危有所顧慮,彰顯的便是一種超越敵我界限的道德考慮,是“兼愛民”思想的集中展現。在《司馬法》交戰禮中,對此也有生動展現:“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司馬法·仁本第一》)通過不過度追擊敵人、不圍困失去戰斗力的敵軍、給予傷病敵軍人道關懷等一系列行為主張,以此彰顯王道之師的道德風范。在戰勝敵人后,《司馬法》規定:“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司馬法·仁本第一》)通過禮法約束部隊,特別是大戰勝利之后,必須防止驕兵悍將肆掠敵國,同時對敵人給予軍事人道主義關懷。在戰事平息之后,《司馬法》對己方軍民也充分彰顯了恤民之情:“古者戍兵三年不興,睹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答民之勞,示休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對鎮守邊疆的將士,上級由于看到了他們的辛勞付出,規定三年不再服徭役,上下之間互相關心理解,這就是和之至的境界。戰爭勝利之后,演奏凱歌,表達喜悅之情,修筑靈臺,感恩民眾的勞動,以示休養生息。這樣一副恰如孟子所描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離婁下》)的上下精誠團結之景象,正是人本精神作用于軍中的鮮活寫照。
這一時期的戰爭,雖然戰場上仍是敵我的對立廝殺,但往往雙方都將“禮樂制度”置于“戰爭勝負”之上,這與戰國時期動輒“弒其君”、“伐大國”、“拔其城”、“隳其國”等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當然,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歷史邏輯,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從時代特征來說,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期,影響涉及政治制度、社會生產、軍事實踐等方方面面。在春秋中期以前,周王朝雖山河日下,但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中,仍具備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交戰時也須恪守禮制,否則會引起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此時的社會生產力也制約了戰爭規模,軍事行動一般投入兵力不多,主要依靠戰車在陣地戰中交戰,因此短時間內即能分出勝負。戰爭形式除了戰場上的廝殺,更多的是采取會盟、“行成”等和平手段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到了戰國時期,受到禮樂制度形同虛設、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諸侯國國力增強、兵家思想的轉型發展等諸多因素影響,此時的戰爭場景日趨激烈殘酷,“禮戰”逐漸消失在歷史的舞臺上。另一方面,從參戰主體來說,春秋時代士兵主要由士族構成,換言之,可以說是貴族階級軍隊。春秋時期的士族,普遍自幼習武,視參軍打仗為榮譽,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從軍并非鄙賤之事,而是享有尊崇的社會地位⑤。在《國語》《左傳》中,俯拾皆是的是各國國君戰場親征的戰例,甚至連貴為天子之尊的周桓王也曾在戰場中中箭受傷,士族階級的尚武之風可見一斑。同時,士族階級也極為重“禮”,這一是源于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長期受到“崇禮尚義”的禮樂文化熏陶,自然也將這種“君子風度”帶入戰場;二是周王朝統治之初分封的各路諸侯,不少都有沾親帶故的血緣關系,士族階層在戰場中所面對的對手往往都有親緣關系,那么點到為止的戰爭進程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到了戰國時期,平民階層逐步登上了戰爭舞臺,以上因素自然冰消瓦解,戰爭溫情的面紗被徹底摘下,露出了猙獰本貌。
三、《司馬法》“禮戰”理念的倫理溯源
縱觀整部《司馬法》,其所尊奉的“禮戰”理念,究其根本都是圍繞“以仁為本”這一核心而展開的。“仁”是自三代時期就已有之的傳統觀念。根據最新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研究結果表明,古時的“仁”,即“從身從心”,凸顯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傳遞出的是一種出于人類本能的體恤關愛之情。特別是在周朝禮樂文化的熏陶之下,“仁”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道德內涵,通過禮樂文化的輻射,逐漸成為社會倡導的主流價值。
到了春秋時期,孔子將“仁”提升至空前的道德高度,視為最高的道德境界,構筑了以“仁”為核心,囊括“孝、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的倫理思想體系。其中,“禮”是“仁”的外在制度形式,“仁”是“禮”的內在精神實質。《禮記》中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記·曲禮上》)正是由于有了“仁”作為最核心的價值內涵,“仁禮”互構這一體系才在理論上得以自洽⑥。若離開“仁”,“禮”便失去了內在支撐,只剩徒具其表的外在樣式,此時的“禮”也無法稱其為“禮”,已質變為“儀”;若離開“禮”,“仁”則淪為虛無縹緲的道德說教,難以在現實中落地生根。“禮”所代表的恭行踐履是內在仁德的修證之途,所以,當孔子面對弟子顏淵問仁時,回答道:“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篇第十二》)這就將象征儒家最高道德追求的“仁”,通過“復禮”這一途徑成功引入現世生活。反觀《司馬法》中言兵論戰的具體主張,無論是“以仁為本”還是“以禮為固”,無不具有鮮明的儒家印記,彰顯出對于儒家價值理念的高度認可和不遺余力的揄揚,體現了這一時期“兵儒合流”的文化特征。
先秦時期,伴隨諸子百家學術思想不斷向前發展,各家各派在對峙攻訐的表面下,相互之間悄然進行著吸納與融合,形成一種兼容互補的趨勢。“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各家正是在這種兼容并蓄中取長補短,不斷完善己方思想體系,恰如莊子所言:“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莊子·天下》)就兵家而言,其在與秉持“道德至上主義”的儒家所進行的合流過程中,自身也深受影響。一方面,從理論建構來說,兵家注重從實踐層面研究戰場上的克敵制勝之道,但對超越具體作戰之上涉及戰爭源起、性質及意義等形而上的問題,則缺乏相應觀照。儒家則不然,它從道德視角審視現世生活中萬事萬物,以禮樂制度為載體,設計了古代中國最為完善精密的安邦治國之道,一直以來都以顯學身份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二者的有機結合,是社會發展的現實所需:儒學統領兵學,賦予了超越具體戰爭之上的仁義道德理想;兵學服務儒學,提供了實現道德理想撥亂反正的方法途徑。克敵制勝之道與安邦治國之道至此達成了和諧統一。另一方面,從價值內涵來說,儒家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廣博精深的思想體系,樹立了權威的道德評判標準。司馬遷曾高度評價道:“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史記·孔子世家》)“兵儒合流”使得儒家的政治理想與尚武精神建立了新的聯系,進而促成了先秦時期正義戰爭觀逐步形成并深入人心,成為民族普遍共識。《司馬法》中“殺人安人”“以戰止戰”正是“兵儒合流”的具體產物。同時,儒家思想中飽含“尚和”傾向,“和為貴”正是其核心價值。儒家的“和”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涵蓋了人倫關系、國家交往乃至天人合一等方方面面,樹立了“和諧統一”的思維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儒家雖有其自身價值主張,但卻不同于西方宗教式的強制灌輸乃至暴力輸出,始終以“和而不同”的觀念寬容面對世間百態。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篇第十二》),儒家思想始終以一種相對淡然卻又潤物無聲的方式散發著自己的強大影響力。這樣的價值傾向作用于兵家之后,使中華民族對待戰爭多了一分克制與理性,避免了走上窮兵黷武、恃強凌弱的戰爭之路。英國哲學家羅素就此曾說過:“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以禮待人。”⑦ 這正是“兵儒合流”帶給我們民族性格的最大影響,同時也是百姓民生最大的福祉。
四、《司馬法》“禮戰”理念與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質
習近平指出:“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⑧ 《司馬法》對先秦時期動蕩的政治軍事形勢有著洞若觀火般的明見,特別是其所構筑的“禮戰”理念,具有深邃的思想內涵,其重要意義在于,首次將道德屬性引入戰場之中,在“利”與“禮”之間做出了抉擇,將人文關懷無差別地投射到敵我雙方,為本應殘酷的死生之地提供了基本的制度遵循,守住了人類的道德底線,這不得不說是軍事倫理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鑒諸往而知來者,在國防和軍隊建設進入了新時代的當下,當我們再次審視這部兩千多年前的兵家古籍,對于深刻理解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本質,努力推進新時代我軍政治工作提質增效,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鑒。
掩卷反思,《司馬法》的“禮戰”理念之所以能夠在殘酷的戰爭實踐中得以踐行,根本前提在于己方將士對所恪守之“禮”的發自內心的高度認同。今日,“禮戰”的具體作戰樣式早已被歷史所淘汰,但“禮戰”精神卻在中華大地傳承了下來,我軍自身的發展史就是對此最好的詮釋。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宣告了我軍的誕生。彼時,正值各路軍閥割據混戰,全國上下一片硝煙之際,誰也沒把這支弱小的力量放在眼里。面對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狀況,我軍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并以星火燎原之勢逐步發展壯大。一路走來,我軍所面對的每一個敵人幾乎都是兵多將廣、裝備精良,所進行的每一場戰斗也幾乎都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那么,原因何在?我想,我軍獨具的思想政治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善于在實踐中總結摸索,三灣改編、古田會議、遵義會議……一次次重要的歷史時刻見證了我軍的成長蛻變,逐漸明確了這支軍隊的性質、宗旨和任務,通過深入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廣大官兵,不僅使其明白“為誰而戰”這個最基本的道理,也極大地凝聚起官兵共識。一切為了人民,這是我黨我軍永不褪色的赤子情懷;一切依靠人民,這是我黨我軍發展壯大的牢固根基。櫛風沐雨,薪火相傳;篳路藍縷,玉汝于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條令”“五統四性”這一部部條令法規的形成,體現了我們這支軍隊軍紀如鐵的優良作風。從戰爭年代“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借東西要還”“買賣公平”“不損壞莊稼”……這些樸實卻又細致入微的規定,再到解放上海后的“百萬雄師,秋毫無犯”,一幕幕場景彰顯著人們軍隊血脈里流淌著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紅色基因。在對待投誠敵軍方面,我軍也有著優待俘虜的政策,充分給予了人道主義關懷,既動搖敵方軍心,又進一步凝聚己方力量。這不正是《司馬法》在二千多年前所提出的“不加喪,不因兇”“冬夏不興師”“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等“禮戰”精神在今日的現實演繹嗎?我軍所恪守的“禮”,是自身過硬的作風紀律,是一條條嚴明細致的法規制度,展現出的是我軍“正義之師、文明之師、威武之師”的光輝形象,而在“禮戰”背后所承載的正是“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憑借于此,我軍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擁戴,形成了“人民軍隊人民愛,人民軍隊愛人民”血肉聯系。“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也是我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關鍵所在。這不正是“禮戰”強大戰斗力的現實彰顯嗎?當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軍政治工作無論在職能任務、開展方式、編制體制等諸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唯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保持一顆紅心干事業謀發展,方能激發出新時代政治工作的內生動力和向上活力。
注釋:
①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2月24日。
② 見于“春秋戰國時期國家間戰爭數據庫”。參見王日華:《歷史主義與國際關系理論:先秦中國體系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 《司馬法》中“軍禮”與“軍法”近乎可看作是對等概念,但相較于“軍法”的強制性,“軍禮”更加注重道德上的規約。參見王聯斌:《中華傳統武德發展史略》,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頁。
④ [德]伊曼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楊云飛譯,鄧曉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⑤ 雷海宗指出,春秋時代的貴族階級軍隊被貴族所特有的“俠義”精神所支配,貴族普遍視上陣殺敵為榮,視不能當兵為恥。參見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
⑥ 孔子所致力于構建的“以仁安禮”,是通過闡明人們自覺守禮的內在價值依據——“仁”,最終達成倡導社會群體自覺樹立“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目標。另外,僅就“仁”“禮”來說,二者是互相包含、同構互動的動態關系。參見賴志凌、王江武:《從〈論語〉中仁對禮的建構看孔子的仁禮關系思想》,《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
⑦ [英]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注,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頁。
⑧ 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上的講話》,《解放軍報》2014年9月25日。
作者簡介:王浩宇,廣東陸軍預備役高射炮兵師第四團,廣東汕頭,515000。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