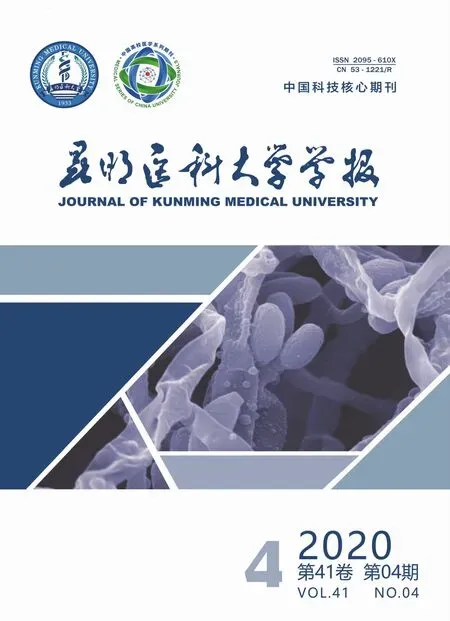內界膜剝除術治療特發性黃斑裂孔的臨床療效
劉 麗,肖麗波,徐文榮,劉曉晨,趙聯玖
(昆明醫科大學第四附屬醫院/ 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眼科/ 云南省眼科研究所/ 云南省眼部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云南省眼科疾病臨床醫學中心/ 云南省眼科疾病防治研究重點實驗室/ 云南省姚克專家工作站,云南昆明 650021)
特發性黃斑裂孔(idiopathic macular hole,IMH)是指黃斑中心凹區無明顯病因發生的視網膜神經上皮層的全層組織缺損。IMH通常影響50~70歲患者,其中約三分之二是女性[1],約3%~27%的患者為雙眼發病[2],每年發病率約為7.8人/100 000人[3]。在治療方面,有Meta分析顯示,與未剝除內界膜的IMH患者相比,行內界膜剝除術的患者有較高MH閉合率且較低的復發率[4]。因此玻璃體切除(pars plana vitrectomy,PPV)聯合內界膜剝除(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ILMP)術已成為治療IMH的標準術式。即使是大型IMH,其解剖閉合率也可達90%~95%[5]。目前視網膜各層微觀結構及厚度能夠在SD-OCT上直觀地顯示且準確測量。為此,筆者采用SD-OCT研究25G PPV聯合ILMP術治療IMH,分析手術前后黃斑區視網膜及GCC厚度變化情況并探究其與MH大小的相關性,旨在探討ILMP術后的臨床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在昆明醫科大學第四附屬醫院確診并行25G PPV聯合ILMP術的30例(30眼)IMH患者臨床資料。其中男性9例(9眼),女性21例(21眼);年齡51~72歲,平均(62.25±4.82)歲;病程1~24月,平均(4.31±6.01)月。本研究患者中2期MH12眼,3期13眼,4期5眼。本研究排除青光眼、高度近視、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視網膜脫離及既往眼部手術史病例。患致密性白內障的病例也被排除,以消除術后視力的改善是由白內障摘除引起。
1.2 測量方法
測量術前最佳矯正視力(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BCBA),且將BCVA轉換為logMAR視力進行記錄;測量人工晶體度數;采用SD-OCT系統(德國Heidelberg)的3D模式進行掃描。測量所有患者術前MH最小直徑及最大底徑;ETDRS將6 mm直徑的視網膜區域分為九個部分,將黃斑裂孔中心與九分區中心重合,用OCT自帶軟件測量術前及術后3月復診時中心凹(centrals,C)、黃斑內環上方及下方(inner superior,IS;innerinferior,II)、鼻 側(inner nasal,IN)及顳側(innertemporal,IT)的全層視網膜厚度及GCC厚度;測量由同一經驗豐富的技師完成,重復測量3次取其平均值。既往有研究表明在IMH患者中,由于MH的原因導致自動分層可能出現錯誤[6]。因此筆者在使用OCT測量相關數據時,手動調整錯誤分層的視網膜層。
1.3 手術方法
術前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且簽署知情同意書,手術由同一位經驗豐富的醫師采用25G玻璃體切除手術系統完成。患者行白內障超聲乳化后,采用標準三通道經睫狀體平坦部行玻璃體切除及人工玻璃體后脫離后,注入0.1%的吲哚菁綠0.2 mL染色,吸除染色劑后用44G眼內鑷從顳側開始環形剝除血管弓以內的ILM;植入相應度數的人工晶體;氣液交換后消毒空氣填充。術后囑所有患者保持面朝下俯臥位姿勢1周。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數據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手術前后BCVA、視網膜厚度及GCC厚度的變化采用配對的t檢驗;術后視網膜及GCC厚度值與MH直徑之間的相關性采用Pearson相關系數法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術后裂孔閉合情況及最佳矯正視力變化
術后28例MH閉合,初次閉合率為93.33%。MH未閉合的2例患者均在術后1月再次接受擴大內界膜剝除+內界膜移植術,術后MH均閉合。術后3月時,平均logMAR BCVA為(1.011±0.25),較術前(1.337±0.31)顯著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2.2 手術前后視網膜及GCC厚度變化情況
術后3月時,C區視網膜厚度較術前相比明顯變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C區GCC厚度較術前變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53);IS、II、IN、IT視網膜及GCC厚度較術前均明顯變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IT象限變薄更明顯,見表1、圖1。
表1 手術前后視網膜及GCC厚度值比較()Tab.1 Comparisons of retinal and GCC thickness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表1 手術前后視網膜及GCC厚度值比較()Tab.1 Comparisons of retinal and GCC thickness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注:C:中心凹;IS:黃斑內環上方;II:黃斑內環下方;IN:黃斑內環鼻側;IT:黃斑內環顳側。

圖1 手術前后視網膜及GCC厚度值比較Fig.1 Comparisons of retinal and GCC thickness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2.3 術后視網膜及GCC厚度與術前黃斑裂孔大小的相關性
術后3月時,黃斑C、IS、II、IN、IT視網膜及GCC厚度值與術前MH最小直徑及最大底徑均無明顯相關性,見表2。

表2 術后視網膜及GCC厚度值與黃斑裂孔大小的關系Tab.2 Relationship among postoperative retinal,GCC thickness values and macular hole size
3 討論
IMH起病通常比較隱匿,早期可無明顯癥狀,隨著病情進展,會嚴重影響患者的中心視力。其確切的發病機制至今未完全明確,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是Gass[7]于1988年提出的假說:造成IMH的主要原因是黃斑區視網膜表面切線方向的牽拉。隨后,Kelly和Wendel等[8]在1991年首次報道使用PPV術成功治療IMH,并使患者視力得到改善,同時驗證了Gass的假說。
目前,SD-OCT可以高分辨顯示視網膜橫截面圖像并能夠定量測量視網膜厚度值,已被廣泛用于研究黃斑疾病[9]。此外借助先進的圖像處理技術,對視網膜的每一層結構進行自動分層,從而可以定量評估手術前后視網膜各層厚度的變化。近期研究指出MH手術成功后,明顯改善的視覺功能和視力相關生活質量(VR-QOL)的波動歸因于晶狀體混濁的發展,所以PPV結合白內障手術可以幫助MH患者保持穩定的VR-QOL[10]。有研究指出ILMP術后,觀察到總鼻側視網膜增厚,總顳部視網膜變薄[11]。另外的研究發現ILMP術后,內部視網膜的長期形態變化是明顯的,黃斑GCC厚度變薄[12]。研究表明對于ILMP術后仍未閉合的MH,可施行自體內界膜移植術[13]。在本研究中,MH未閉合的2例患者再次接受內界膜移植術后MH均閉合,2例患者最小直徑均>600μm,筆者分析第一次手術失敗可能與裂孔直徑較大有關。本研究中所有患者術后BCVA較術前顯著提高;黃斑C區視網膜厚度較術前明顯變薄,且在所有區域中最顯著,筆者將其明顯變薄主要歸因于裂孔導致的黃斑水腫的吸收。IS、II、IN、IT象限視網膜及GCC厚度較術前均明顯變薄,且顳側較其他象限變薄更明顯。為什么顳側變薄更顯著?有研究顯示,ILMP術成功封閉MH后,發現黃斑中心向視盤移位[14]。Imamura的研究中除了發現視網膜向視盤移位外,還發現顳側視網膜向視盤的移位距離大于鼻側[15]。目前視網膜移位的生物學機制尚未明確。在Pak的研究中發現,通過手術關閉MH后,黃斑存在向心性、鼻側和輕微下方移位現象。他們解釋黃斑移位可能是裂孔的閉合、視網膜神經纖維層(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RNFL)的收縮和重力的多重作用導致的[16]。另一項研究則認為MH術后視網膜向視盤移位是由于ILM剝除導致微管結構改變從而引起RNFL收縮導致的[15]。本研究中,筆者考慮到RNFL在鼻象限比顳象限更密集,為了減少對RNFL的損傷,ILMP術通常從顳側開始,從而導致對顳側視網膜的機械損傷重于其他象限,且較薄的RNFL可能受到ILM剝離時更大影響,從而加重底層視網膜層的機械損傷。另外筆者在顳下方放置維持眼內壓的灌注管,在氣液交換過程中,對顳下方視網膜作用力較大,可能會對視網膜造成一定的損傷。以上這些因素可能是導致顳側術后變薄更顯著的部分原因。在Yoshihiro等[17]的研究中,發現MH大小與術后中央區視網膜厚度(CRT)呈負相關。另一項研究也發現視網膜厚度變化與MH的基底直徑及最小直徑顯著相關[18]。在本研究中,術后各象限視網膜及GCC厚度與術前黃斑裂孔的最小直徑及最大底徑均無明顯相關性,這可能與筆者的樣本量少及觀察時間過短有關。
綜上所述,應用25G PPV聯合ILMP術治療IMH具有較高的裂孔閉合率及較好的視力恢復。本研究屬于回顧性研究,樣本量少,觀察時間短。今后筆者將收集更多樣本,進行前瞻性、多中心的臨床研究,對視網膜厚度與MH大小之間的相關性及與術后BCVA的關系進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