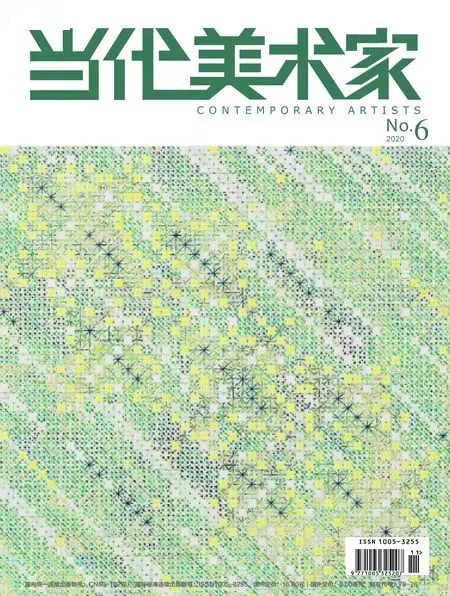詩意水墨表達未來與遠方
——澳門藝術家吳少英創作風格淺析
高潔 Gao Jie

1吳少英光01光影裝置作品2018
中國水墨根植于東方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在無數文人墨客數千年間的傳承和發展之下,演化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藝術語言和審美體系。作為中國當代水墨領域的重要藝術家,出生于澳門的吳少英于27歲時,也就是1993年即在澳門葡文書局畫廊舉辦了首場展覽,她的水墨作品一經亮相就引起了業內的關注并獲得了廣泛好評,她也由此確立了自己在創作上的方向和風格。經過20多年的藝術實踐和探索,通過每一次水墨創作和每一次藝術突破,現今的她已經完成了個人藝術語言框架性的搭建。
云自無心水自閑
在藝術家眼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成為創作的材料。吳少英對藝術創作的執著最初來源于其對家鄉澳門云海的視覺記憶。記憶里漫無邊際的云,如臨于大海之濱,波起峰涌,浪花飛濺。它與海水的動態呼應深深地印在了藝術家最初的視覺經驗里。舒卷意何窮,縈流復帶空。有形不累物,無跡去隨風。一如水墨的隨性淡雅,意蘊無窮。以風云為創作對象,以水墨為創作語言,成為吳少英本初的藝術向往。
兩岸四地——不斷求索創新
吳少英的人生經歷豐富且多彩,1966年生于澳門,從小在香港和澳門兩地長大,20世紀90年代初曾游學倫敦,1996年移居臺灣繼續研究當代水墨,2008年至今在北京生活和創作。 這種經歷讓她成為一位“兩岸四地藝術家”。
在游學倫敦的經歷中,吳少英遇到了她的指路人——倫敦大學理斯藝術學院版畫系主任勃度羅教授。“我在澳門做完了第一個展覽就去了英國,我問勃度羅老師,我到你學校去讀大學好不好?可是勃度羅老師看到我的畫后說,你都畫到這個樣了,還學新西洋藝術干什么呢?你應該學你自己的東西。”這番話對于一個二十幾歲懵懵懂懂的年輕人來說可謂是當頭棒喝。之后勃度羅教授便寫了一封信推薦吳少英去倫敦大英博物館的中國書畫藏品館研究室修讀館內的中國藏畫。也正是在這里吳少英開始尋找自己的根。
自此吳少英在英國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博物館里面度過的。館藏豐富的研究室里滿滿當當地放了很多柜子,每個柜子里整整齊齊地碼著標好編碼的藏畫資料活頁夾。吳少英告訴館員想看哪幅藏畫,第二天館員就會把那張畫拿出來供她賞析。這一經歷讓她能夠近距離地感受古人的繪畫哲學以及他們對于墨的理解,深入了解并學習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
吳少英在研讀中國畫的同時,也大量觀摩西方繪畫。唐人街附近的國家美術館長期展出從幾世紀到19世紀的西方繪畫,吳少英反復觀察、探究、研讀,這種學習就是在和不同的藝術大師對話。“站在真跡面前,你會驚艷那些畫的色彩、筆觸,是如此的讓人感動。梵高那幅著名的《向日葵》就陳列在一個有天窗的展廳內,早上、中午和晚上不同的時間去看,感覺都是不一樣的。那種筆觸和色彩的魅力,不是通過一張印刷品可以感受得到的。”吳少英在看到藝術品真跡之后就全面尋找相關藝術家的資料研讀。通過在倫敦的兩年學習,吳少英領會到了兩個系統,一個是西方的,一個是東方的,正是這段學習的經歷使得吳少英對顏色、筆觸,以及對西方繪畫的結構有了進一步的深層理解。在美術館的學習讓吳少英發現了尋找藝術道路的一種方式,學習到的大量新知識、新思想,也促使她重新思考自己的創作,并深遠地影響了之后的創作方向。
臺灣到北京——抽象水墨的藝術表達
1996年,吳少英獲邀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了“冥游”個展。展覽展出了她厚積薄發所創作的60幅作品。本是到臺灣舉辦一場展覽,可深厚的人文氣息卻吸引她留在了臺北。
吳少英接受了臺灣新北市聯合醫院三重院區的公共藝術創作的委托,創作了《生命詩篇》《寧靜海》和《曙暮光》,用水墨意境的形式表達生命的真諦。這些在玻璃上色彩斑斕的創作,產生出山水意蘊的影像,以錄像方式被拍攝下來,經過藝術微噴的手法再次回到玻璃上,永恒地保存那瞬間之美。在此之前,吳少英的作品還僅限于黑白和一些淡雅的顏色,直到如今,才真正將一些更濃烈的顏色注入作品的表現中來。
2003年是吳少英創作生涯的一個轉折點,她將自己已經相當成熟的抽象水墨,轉而以另外幾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媒介進行表現。“每一種新的媒介都會讓墨產生更多的可能性,每一種媒介對于墨的表現也是不同的。”于是我們看到了她的水墨攝影和水墨行為作品。

2吳少英詩意水墨水墨帆布150cm×150cm2014
2004、2005年開始,吳少英又開始用錄像記錄動態的水墨,她認為錄像水墨更能展現自然流動的能量和意境。“之前我的宣紙、畫布和攝影作品大都是‘完成時’,是作品在創作過程中某一個時間的停留。但水墨在進行創作中更是一個美妙的過程,在進行水墨自身的探索時,我也想將這個過程記錄下來,錄像媒介可以很直觀地表現這個過程。”吳少英的影像作品看起來都是一鏡到底的真實記錄,實際上在后期剪輯時,也運用到各種剪輯方式來控制作品各時間段水墨流動的速度和層次,甚至有些還用倒放的形式讓時間回到初始階段,這樣看起來,她鏡頭下的水墨似乎在慢慢從中抽離。“從有到無,這種對于墨之時空的把控也是之前從未有過的體驗,對于墨在不同媒介上所展現出來的具有東方哲學的表達方式一直是我的創作主線。”她的這一大膽創新獲得了國際獎項的認可,其中錄像作品《混沌》入選2005年葡萄牙第二屆黑白影音藝術節“最佳實驗錄像獎”,她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澳門藝術家。2006年錄像作品《無界》入選日本第10屆新媒體藝術節評審委員會推薦作品。
2008年之后,吳少英來到了機遇與挑戰共存的北京,她知道,藝術家的精湛作品往往在復雜的情緒下產生。在這里,她的創作愈發奔放與超前,她嘗試將光影的變化及不同材料的折射引入創作實踐,試圖進一步打破基于水墨的文化邊界。2018年,吳少英推出個展“天宇”,此次個展呈現吳少英的繪畫、影像以及光影裝置作品。她的創作很好地詮釋了“跨媒介”的本質,對于“水墨”“氣韻”的理解貫穿在她的作品中。吳少英對于墨汁在水中彌散的現象情有獨鐘,那是一種脫離控制的無定狀態,她選擇了用繪畫和新媒體表達這種狀態的多個面向。作品《光01》尤為獨特,水波一般的光,在空間中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狀態流淌,波紋既在橫向的區間里蕩漾,也在向中心處回旋,而處在中心的“發光體”雖然不斷地顫動,卻永遠被隱沒在模糊中。作品的視覺形式,似乎是對某種“暗流”的隱喻。事物之所以復雜,是因為表象和內部的波動總是存在隱秘的聯系。達成平衡和歸于秩序的表象,時常被下方的“暗流”攪動,暗流的中心如同作品中的“發光體”,雖被永恒地封存于深處,卻時時刻刻發揮著關鍵的作用。
2019年,她在北京舉辦了“視覺遷徙”個展,展覽呈現她的光影裝置作品,作品程序與家鄉澳門的實時天氣數據相連接,通過數字技術模擬與陰、晴、多云以及風暴等情境相關的變化。她不斷將視覺經驗在不同媒介間進行遷徙,在控制與相對的失控之間尋求動態的平衡。區別于以往用傳統介質創作基于圖像的視覺轉化,此次吳少英將視覺經驗進行數字形式的轉化,通過軟件建立起多個邏輯通道,將物理世界、藝術家及其創造的虛擬世界聯結起來,把觀者帶入到一個墨影流光的平行世界。ELEMENTS科技團隊與吳少英的這次合作通過計算機用流體運動方程式計算出流動詩意的畫面,作品即使不間斷播放一百年的時間畫面也不會重復。為此有的觀眾可以在展廳整整待上幾個小時乃至一天。水墨藝術讓人們沉淀下來思考人生。這些作品是吳少英前后探索了十年之久,花費了5個月的時間和程序員來進行深度的合作,所產生的水墨虛擬世界。2019年1月吳少英為了這次展覽專門寫了一首獨具韻味的小詩:
編程虛擬流動的云,
跟現實世界的時間一樣,
一分一秒地在身邊流逝。
從小愛看澳門的云,
云端給我無限水墨的想像,
想不到今天在展廳看編程的云,
讓我有說不出的感動,
沉淀此中,
仿佛躺在清晨的湖邊,
在云端里的山上……
水墨意境與東方意蘊
水墨不只是一種媒介,它是一種符號系統,可以被稱為一種語言學。語言的表達,是整個世界觀的輸出,所以“水墨”是中國現代以前的包括儒、道、釋等在內的歷史、文化、哲學、世界觀。水墨語言本身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文化觀,是自然和社會的關系。水墨藝術家如何進入其中,并產生新的概念是水墨藝術家需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顯然,吳少英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在多年的創作實踐中,吳少英一直嘗試通過不同的介質來表現水墨變化豐富的質感。從早期用傳統水墨的表現方式進行藝術創作的探索并著迷于墨汁在宣紙上暈染開來的偶發性,繼而發展到在畫布上帶有克制地流淌,再到使用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觸到的液體材料創作影像和光影裝置作品,不同顏色、不同質感和不同效果的液體在她有意識的控制之下相互交融,呈現出一種控制與失控之間的微妙平衡關系,亦是一種文化對抗社會裂變的隱喻。吳少英以水墨為根本,通過繪畫、攝影、影像、裝置等不同媒材,賦予水墨以復雜的性格。除了媒介上的多元,她的作品也在探討水墨與光影、空間的微妙關系。她在靜態與動態之間,創造的是一個開放式的話題和空間。她對于水墨的嘗試,解放了材料與工具的使用范圍,她在藝術表達路徑上的變化,某種程度上正是基于物質為歷史提供了更多選擇。吳少英逐步將水墨從畫筆的從屬地位和其長期與修辭、圖像關系的局限中解放出來,并不斷地去拓展水墨藝術的邊界,使得水墨的可能性不斷延伸。吳少英曾說 “‘水墨’強調意境概念始于宋,盛于元,古人相信繪畫的目的亦非畫得形體之相似,而在哲學、理學的基礎上捕捉描繪物件的神韻,領悟生命的意義,墨分五色,最適合用于表述其內在的意境,影響深遠至明清及現代亦包括我的創作。”
觀賞吳少英的畫,腦中莫名會出現“和諧”二字,她的作品有著一種予取予求神奇的魅力,似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其中尋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因此她也時常說自己的作品“是一面鏡子”。縱觀她多年來的藝術創作可以得知,她的主要創作承襲宋朝美學,淡雅極簡的禪意風格之下保留了傳統水墨的深厚底蘊,在形式上不斷突破的同時始終保持著對于自我文化根源的探索,在多年的行空奇想下她大膽創造,作品持續關注與探討人與世界、城市與自然、科技與社會的關系。她堅持以當代的思維、現代的媒介來表現其作品中所蘊含的水墨意境。這不僅成為了吳少英藝術表現的特征,更是其內在精神價值所在。
“東方的藝術在本質上是關于生活態度的表達,與旨在抒發反叛的西方藝術不同,東方藝術是關于人如何與世界相處,尤其是與自然融合的哲學。” 她的作品本身即具有強烈的詩意性與文人神髓,“我把我的想象表現出來,再交給觀眾去徜徉其中。”已故臺灣藝評家倪再沁多年前曾評論少英的錄像作品,寫了一篇名為《流動的詩意——吳少英的水墨錄像》的文章,他說:“從水墨繪畫到水墨錄像,吳少英的轉變和進步清晰可見,她在水墨流動的過程中所展現的能量、意境和格局皆令人激賞,像她這樣的富有理想性格的創作者,當能打造出屬于當代的、屬于華人的藝術新境,值得期待。”
在中西交匯、文化共融的社會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澳門當代藝術具有多元視角。而在澳門的生活經歷和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一直深刻地影響著吳少英的藝術創作。學習了解東西藝術文化之后,種種經歷與不同的概念引發了她多樣的思考,她在創作中運用多種不同媒介的作品顯示跨文化的水墨表現方式,充分證明了墨有其自身的獨特個性,進一步顯現了東方美學的當代精神。在時光中積淀的新的感悟和不期而遇的新的想法,她對于中華文化中傳統哲學、藝術實踐、文學思想等的強烈興趣,和她對于水墨和未來一以貫之的好奇心促使她在摸索和嘗試中前行,將傳統和現代結合在一起。
水墨藝術未來的發展趨勢將是對于我們中華傳統文化更廣義的解讀。水墨創作仍有多重可能性,如何在東方意蘊和當代觀念間求得和諧統一,如何在當代語境下進行傳承與創新,吳少英的探索與創作給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