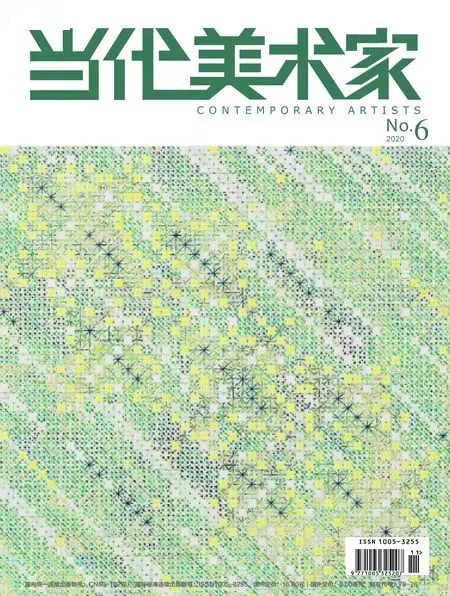加速主義邏輯下的陳述
沈樺 Shen Hua

1沈樺游牧——拉美現(xiàn)代主義200cm×100cm

2比爾·維奧拉小道影像
加速主義
“加速”指“近年來(lái)接連發(fā)生在政治、科學(xué)尤其是技術(shù)領(lǐng)域的各種轉(zhuǎn)向,并特別強(qiáng)調(diào)這些轉(zhuǎn)向的節(jié)律。其次,它往往帶有某種彌賽亞色彩,將這些轉(zhuǎn)向視作某種關(guān)于歷史的技術(shù)性終結(jié)的征兆。”1這個(gè)概念逐漸擴(kuò)張到了整個(gè)政治領(lǐng)域,也隨之觸及到社會(huì)的各個(gè)方面。加速主義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技術(shù)科學(xué)的發(fā)展:今天,技術(shù)的推動(dòng)可以使社會(huì)各個(gè)領(lǐng)域在短暫的積累之后呈現(xiàn)爆炸式的突進(jìn),進(jìn)而推動(dòng)社會(huì)“進(jìn)化”。
在羅賓·麥凱(Robin Mackay)和阿爾曼·阿瓦尼斯安(Armen Avanessian)合編的《加速:加速主義文集》中,尼克·蘭德(Nick Land)的文章《目的的螺旋:關(guān)于加速主義和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的21條筆記》收錄了尼克關(guān)于加速的一些思考。其中關(guān)于“目的螺旋”與加速的關(guān)系,他是這樣判斷的“目的螺旋”,指的是一個(gè)超信實(shí)體,是一個(gè)“自我強(qiáng)化的控制論增強(qiáng)”,“形容的是機(jī)器的波長(zhǎng),在宇宙射線中,沿著終極紫外線逃逸。它和復(fù)雜性、關(guān)聯(lián)性、機(jī)器壓縮、負(fù)熵、自由能量耗盡、效率、智能以及運(yùn)行能力相關(guān)聯(lián),定義著一個(gè)絕對(duì)的但難以捉摸的增長(zhǎng)斜率。”2在控制論中,反饋機(jī)制的實(shí)施可以使機(jī)器的運(yùn)轉(zhuǎn)更加合理、持續(xù)和流暢,“目的螺旋”是反饋機(jī)制的運(yùn)作方式,能在直接的機(jī)械目的的引導(dǎo)下實(shí)現(xiàn)機(jī)械運(yùn)轉(zhuǎn)的更加高效化。同時(shí),我們也可以在他的筆記中看到“加速主義”的概念被歸納在在“異化”的范疇之中:從資本主義誕生之日起,人類社會(huì)就不再追求“實(shí)在”,轉(zhuǎn)向以“價(jià)值自身”作為追求的目的。尼克·斯?fàn)柲崛耍∟ick Srnicek)也曾經(jīng)指出“馬克思也是最典型的加速主義思想家”——“通過(guò)加速”來(lái)“超越資本主義價(jià)值形式的限制”。波德里亞在他的《象征交換與死亡》中也提到了當(dāng)價(jià)值規(guī)律和符號(hào)結(jié)構(gòu)結(jié)合在一起,逐漸讓代碼統(tǒng)治了整個(gè)社會(huì)的時(shí)候,社會(huì)便出現(xiàn)了模式自身的交換:它們不再與實(shí)在交換,只與自己交換。這個(gè)世界變成了各種模式之間的演繹,脫離實(shí)在,也跟(人文主義范疇的)“人類”沒有了關(guān)系。
《重復(fù)與差異》中的“加速”
在德勒茲的哲學(xué)語(yǔ)境里,“加速”一詞與強(qiáng)度,與“重復(fù)和差異”相關(guān)。在對(duì)技術(shù)的理解之中,不同于康德的同一性重復(fù),德勒茲將他的重復(fù)建立在差異性和積累性上:康德和黑格爾將一般的規(guī)律和概念局限在它們自我的“實(shí)驗(yàn)室”里運(yùn)作,外在事物呈現(xiàn)的只是對(duì)概念和規(guī)律進(jìn)行復(fù)制的表象,而概念本身是恒定不變的,事物也被認(rèn)為沒有變化,同一概念生發(fā)的多個(gè)事物也只是無(wú)差別的復(fù)制。德勒茲則是“把重復(fù)變成新的東西:將其與一種檢驗(yàn)、一種選擇或選擇性檢驗(yàn)聯(lián)系起來(lái)……把重復(fù)變成這樣一種新生事物的問(wèn)題。”3他用“重復(fù)”的新方式建立起了一套認(rèn)知體系:比如,節(jié)日的慶典不是簡(jiǎn)單的儀式重復(fù),而是節(jié)日概念中相同和差異性不斷實(shí)踐和疊加。技術(shù)也是一樣,當(dāng)技術(shù)每一次實(shí)施——與主體接觸、改變客體對(duì)象——的時(shí)候,它并不是技術(shù)簡(jiǎn)單的重復(fù)使用,它也在逐漸改變自身,疊加相同與差異,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的積累,就可以實(shí)現(xiàn)“范式”的變化。同樣,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是在固定的規(guī)律中尋找事件背后的潛意識(shí),他沒有考慮到的是潛意識(shí)和事件本身并不一定對(duì)等,這種錯(cuò)位可以不斷地添加到規(guī)律(對(duì)潛意識(shí)的規(guī)律化認(rèn)知)之中,也可以使之不斷變化;同時(shí)當(dāng)弗洛伊德試圖以不斷地返回過(guò)去來(lái)試圖阻止重復(fù)的時(shí)候,他忽略了精神病癥里的同一因素的轉(zhuǎn)移,在此,德勒茲認(rèn)為這種“轉(zhuǎn)移仍然也是重復(fù)”,也就是不斷地返回也是帶有差異的重復(fù)。所以,差異式的重復(fù)是將規(guī)律或者“節(jié)日的慶典”“第一次發(fā)展到n次冪。就這個(gè)n次冪而言,重復(fù)將自己內(nèi)化,并據(jù)此顛倒自身。”4德勒茲認(rèn)為:“在每一方面,重復(fù)都是一種僭越。”5每一種重復(fù)都有差異,每一次重復(fù)都是積累、超越。加速主義視角下的技術(shù)就是這樣的規(guī)律下建立起來(lái)的:技術(shù)不斷重復(fù),不斷積累,以至于不斷超越自身,也不斷建立新的技術(shù)體系,進(jìn)而“徹底打亂社會(huì)體系的平衡。”6尼克·斯?fàn)柲崛苏J(rèn)為,“這些技術(shù)能力能夠且應(yīng)當(dāng)?shù)玫结尫拧保梢浴白呦蚝筚Y本主義”,實(shí)現(xiàn)對(d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超越。
技術(shù)與語(yǔ)言體系
對(duì)于物體,亞里士多德是這樣闡釋的:“每一個(gè)自然物體自身都具有其運(yùn)動(dòng)和靜止的法則,有些和位置相關(guān),有些和增加或減少相關(guān),還有的則和性質(zhì)變異相關(guān)。任何被制造之物自身都不具備其制造的法則。”這其中就隱含了技術(shù)和事物之間的關(guān)系,即被技術(shù)制造的物體本身是不擁有技術(shù)的法則:技術(shù)與事物是分離的。在《技術(shù)與時(shí)間》里,斯蒂格勒則是這樣談?wù)摤F(xiàn)代技術(shù)的:“技術(shù)進(jìn)入現(xiàn)代化的標(biāo)志就是,從形而上學(xué)到自我表現(xiàn)和自我實(shí)現(xiàn),就像是計(jì)算理性完成了旨在占有和支配自然的計(jì)劃,而這種被占有和支配的自然本身也就失去了自然本來(lái)的意義。”斯蒂格勒也反對(duì)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技術(shù)和哈貝馬斯的“合目的的理性行為”,認(rèn)為他們只是將技術(shù)作為工具強(qiáng)加在自然和人類之上,技術(shù)沒能自覺,而不是技術(shù)的本質(zhì)在于技術(shù)自身。今天的事實(shí)也驗(yàn)證了斯蒂格勒的判斷: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呈現(xiàn)了技術(shù)自身的不斷進(jìn)化,并非只是工具而已。甚至,按照尤瓦爾 · 赫拉利在《人類簡(jiǎn)史》里的說(shuō)法,技術(shù)自身的積累和發(fā)展會(huì)讓智人“退休”。
柏拉圖在《斐德羅斯篇》里談到早期哲學(xué)家曾判斷文字的記載對(duì)知識(shí)記憶的危險(xiǎn),并且會(huì)玷污了人的回憶。這開啟了最早技術(shù)與文字、語(yǔ)言之間關(guān)系的判斷。蘇格拉底的知識(shí)世界是依靠人類口口相傳,并在頭腦中記憶而形成的。當(dāng)文字出現(xiàn)以后,人類逐漸將知識(shí)的儲(chǔ)存交給了文字。在《技術(shù)與時(shí)間:2.迷失方向》中,斯蒂格勒介紹了技術(shù)的持留與語(yǔ)言文字之間的關(guān)系。他介紹了三種記憶的持留技術(shù),第一、二持留7還保留了作為主體的人在記憶中的作用,而第三持留則是“投射的質(zhì)料” ,是記錄人類的感知和回憶的物質(zhì)載體,是一種“技術(shù)——書寫”。“拼寫文字已經(jīng)是某種在延遲中可見的時(shí)鐘”。8文字語(yǔ)言系統(tǒng),特別是近代以英語(yǔ)為代表的符號(hào)化的文字語(yǔ)言系統(tǒng)是一種記憶技術(shù),它將人類的感知、意識(shí)等通過(guò)這個(gè)符號(hào)系統(tǒng)進(jìn)行外化,延遲感知意識(shí)的時(shí)間,將記憶的時(shí)間空間化,這種方式排除了胡塞爾等的(見注釋7的解釋)還將人類作為記憶主體的記憶技術(shù)。記憶外化技術(shù)也為后來(lái)知識(shí)的信息化儲(chǔ)存打下了基礎(chǔ)。今天的電腦、人工智能等能夠不再依賴人而記憶。并且,機(jī)器之間的信息交流也得益于這種記憶的外化。
并且,第三持留的出現(xiàn)使記憶技術(shù)物質(zhì)化以后,能實(shí)現(xiàn)“既像‘生產(chǎn)’,又像‘再——生產(chǎn)’,也就是一種以再現(xiàn)的材料為前提的生產(chǎn)。”9這樣,它可以像前面我們提到的加速主義中自我“目的性螺旋”方式來(lái)不斷發(fā)展自己,逃脫人類賦予的限定性,形成超強(qiáng)的“增長(zhǎng)率”。
陳述
書寫是一種技術(shù),語(yǔ)言系統(tǒng)是一種技術(shù)。作為話語(yǔ)系統(tǒng)中的話語(yǔ)與陳述也是這樣的技術(shù)組成,接下來(lái)談一談作為技術(shù)的陳述。
在《知識(shí)考掘?qū)W》(國(guó)內(nèi)翻譯為“知識(shí)考古學(xué)”)里,福柯花了整整一個(gè)章節(jié)來(lái)描述陳述(statement),其定義極為復(fù)雜。臺(tái)灣學(xué)者王德威在翻譯序言中對(duì)福柯這一術(shù)語(yǔ)的總結(jié)是:“‘陳述’是一種‘功能’,此一功能需籍一個(gè)句子、一項(xiàng)命題予以具體化,但是不能為其所役。”10它是一個(gè)“穿越結(jié)構(gòu)和統(tǒng)一模式的功能”,用語(yǔ)言元素、命題等來(lái)實(shí)現(xiàn)對(duì)客體的話語(yǔ)建構(gòu)。按照福柯的說(shuō)法,一個(gè)語(yǔ)言學(xué)上的系統(tǒng)只有在運(yùn)用一組陳述或一套話語(yǔ)事實(shí)時(shí),才能架構(gòu)完成。11也就是說(shuō)語(yǔ)言學(xué)的系統(tǒng)根基在于陳述,人類世界的話語(yǔ)系統(tǒng)都是建立陳述之上的。這樣,如果說(shuō)語(yǔ)言的書寫系統(tǒng)是第三持留的話,陳述則是這個(gè)持留技術(shù)的組成。
在對(duì)陳述的描繪中,福柯發(fā)現(xiàn)了陳述的積累性和追加性。他認(rèn)為在陳述中,并不是去喚醒文本原有的狀態(tài),而是在文本被遺忘、沉睡中去尋找原有的“殘存”,對(duì)這個(gè)技術(shù)儲(chǔ)存方式進(jìn)行當(dāng)下的解讀,尋找今天對(duì)過(guò)去不斷地疊加。并且,按照重復(fù)的陳述的追加性,即在陳述的系統(tǒng)里,即使同樣的陳述由于在時(shí)間上的不同使用,它不會(huì)像熵般消退,而是堆積:“有各種方法去合并、相互取消、排斥、增補(bǔ)、以及形成各種組合……陳述組成它自己的過(guò)去,定義自己的分支,并對(duì)使它成為可能及必要的情況再加定義,排斥那些不能與其相融的元素。”12福柯意義上的話語(yǔ)考古實(shí)際上就是對(duì)不同時(shí)代對(duì)文本的技術(shù)存留——這個(gè)技術(shù)存留就是我們所講的第三持留——的“重復(fù)”,也即“加速”。這個(gè)持留的“重復(fù)”由于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其他因素的影響,讓不同時(shí)代的文本增加一些斷裂的意義。這些意義的積累讓文本自身系統(tǒng)也會(huì)構(gòu)成一種強(qiáng)度,從而不斷地跨越原有的系統(tǒng)。
根據(jù)福柯對(duì)陳述特性的描述,我們或許可以簡(jiǎn)要地從以下幾個(gè)方面來(lái)對(duì)陳述進(jìn)行加速,形成新的強(qiáng)度,讓它去瓦解資本主義陳述體制的根基,促使資本主義成為陳述歷史的一個(gè)階段。
首先是對(duì)語(yǔ)匯和規(guī)則進(jìn)行加速。福柯認(rèn)為要了解陳述,先要確定所使用的詞匯和說(shuō)明的組合,他也將決定符號(hào)存在與否的模式稱為陳述。語(yǔ)匯、命題、句子等都是陳述的使用手段之一。如果我們將語(yǔ)言書寫系統(tǒng)作為技術(shù),將陳述作為書寫技術(shù)的組成,那在加速主義的范疇里,應(yīng)當(dāng)對(duì)這些手段進(jìn)行強(qiáng)度化的推進(jìn),讓語(yǔ)匯、命題等在一定的模式下自我運(yùn)動(dòng)起來(lái),讓這些運(yùn)動(dòng)了的陳述成為既有話語(yǔ)秩序的解構(gòu)力量,建構(gòu)新的寫作方式。然后,對(duì)陳述所依賴的非統(tǒng)一模式的加速:陳述依賴于一系列符號(hào),但不會(huì)依賴于統(tǒng)一的文法和邏輯,不會(huì)像有機(jī)體一樣完滿自足,也不是在固定的結(jié)構(gòu)之中,所以才有系譜學(xué)的斷裂和再次解讀。加速注意可以讓這種無(wú)機(jī)、斷裂的非統(tǒng)一的性質(zhì)成為常態(tài),甚至創(chuàng)造更多這樣的斷裂常態(tài),通過(guò)這些斷裂以及它的快速運(yùn)轉(zhuǎn)來(lái)盡快達(dá)到范式的突破。接下來(lái)是連接“加速”和陳述的外緣性,按照福柯的說(shuō)法,陳述是沒有時(shí)間性、無(wú)主體性、無(wú)思維中心,也就是無(wú)邊緣,那么加速主義可以推動(dòng)這種特性,徹底革除邊緣。
小結(jié)
如果將書寫語(yǔ)言系統(tǒng)作為技術(shù)的話,陳述也是技術(shù)的組成方式,按照德勒茲的《重復(fù)與差異》和他的生成理論,以及后來(lái)的加速主義理論,陳述也可以是技術(shù)加速的一個(gè)范疇。因此,當(dāng)陳述被加速時(shí),它也會(huì)和社會(huì)的其他技術(shù)一樣推進(jìn)社會(huì)的發(fā)展。當(dāng)然這種發(fā)展是否有利于人類,還是一個(gè)未知。就如同當(dāng)年蘇格拉底對(duì)文字的擔(dān)憂一樣,其后的歷史發(fā)展很難簡(jiǎn)單地將文字作用判斷為有害或是有利。
注釋:
1.源自“毛繼鴻藝術(shù)基金會(huì)”公眾號(hào)發(fā)表,許煜,《論德勒茲與西蒙東思想中的加速概念》。
2.源自“潑先生”公眾號(hào)發(fā)表的文章《關(guān)于加速主義和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的21條筆記:金錢是個(gè)謎宮》。
3.陳永國(guó)編譯,《游牧思想—吉爾·德勒茲、費(fèi)利克斯·瓜塔里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4頁(yè)。
4.陳永國(guó)編譯,《游牧思想—吉爾·德勒茲、費(fèi)利克斯·瓜塔里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8頁(yè)。
5.陳永國(guó)編譯,《游牧思想—吉爾·德勒茲、費(fèi)利克斯·瓜塔里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0頁(yè)。
6.[法]貝納爾·斯蒂格勒著,裴程譯,《技術(shù)與時(shí)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guò)失》,譯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35頁(yè)。
7.胡塞爾認(rèn)為意識(shí)具有時(shí)間性的結(jié)構(gòu),他通過(guò)分析音樂(lè)來(lái)向我們解釋了第一、二持留:在聆聽音樂(lè)的時(shí)候,我們借助當(dāng)下的感知形成“第一記憶”;聽完音樂(lè)后,我們借助想象形成“第二記憶”。這就分別對(duì)應(yīng)了“第一、二持留”,它們分別需要主體對(duì)外界客體進(jìn)行感知和回憶,也就是不能離開主體。
8.[法]貝納爾·斯蒂格勒著,趙和平、印螺譯,《技術(shù)與時(shí)間:2.迷失方向》,譯林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49頁(yè)。
9.[法]貝納爾·斯蒂格勒著,方爾平譯,《技術(shù)與時(shí)間:3.電影的時(shí)間與存在之痛的問(wèn)題》,譯林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第58頁(yè)。
10.[法]米歇爾·福柯著,王德威譯,《知識(shí)的拷掘》,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4月,第46頁(yè)。
11.[法]米歇爾·福柯著,王德威譯,《知識(shí)的拷掘》,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4月第101頁(yè)。
12.[法]米歇爾·福柯著,王德威譯,《知識(shí)的拷掘》,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4月第243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