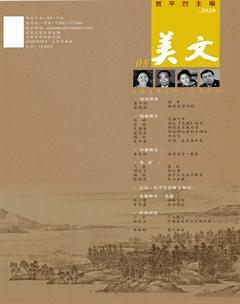迷人的樂園
韓小蕙
對于我們的少年時代來說,協和大院里最迷人的,還屬千花萬草之間、濃密樹葉里面、墻角泥土深處……隱藏著的各種小生靈。
昆 蟲 世 界
那時,一到夏天,尤其是快要天黑的傍晚,晚霞紅光灼灼地映亮了天上、地下的整個世界之時,蜻蜓們便在我們眼前飛舞起來。越早的年頭,飛得越多,輕輕盈盈地在天空中溜著冰,跳著舞,最后,大大咧咧地落在小樹枝上、花瓣上、草葉上,甚至飛過來落在小洋樓的紗窗上。此時,只要躡手躡腳走上前,用兩根手指一捏它的翅膀,它就是我們的俘虜了。輕捏著它的小身子,讓那一對薄薄的翅膀像滑翔機一樣放開,它的大眼睛便咕嚕嚕地轉,小細爪子不停地撓動,有時還把肚子尖彎成一個勾,不知是抗議被抓?還是表達失去自由的疼痛?
據網查,目前世界上已發現了63種蜻蜓,學名都特別深奧,比如異色多紋蜻、低斑蜻、白尾灰蜻、線痣灰蜻、異色灰蜻、黃蜻、紅蜻、玉帶蜻、黑麗翅蜻、北京大蜓、北京弓蜻……可惜我只知道4種:最普通的叫“紅果”,個子中等,全身呈淺紅顏色;還有一種叫“黃果”,顧名思義,它的身體是黃色的;叫我們孩子們最稀罕的是“老桿兒”(雄性)和“老籽兒”(雌性),據說學名叫“碧偉蜓”,個子比一般蜻蜓都大,身體呈綠黑色,像一架小直升飛機,靈敏度和警惕性極高,不容易逮,一般只有男生才能逮著它們。有一次,我突然發現一只“大老桿兒”飛了過來,就落在我面前的小樹枝上,心里又驚又喜,就輕手輕腳地去逮。正在此時,大院男孩兒里的“淘包”高XN也看見了,但他在我身后好幾步遠,就小聲嚷著讓我別動。我沒聽,依然走上前去,但就在我張手快接近它時,它卻警覺地飛走了。身后的高XN實在是氣急了,過來就給了我一拳,好疼啊,所以我到今天還記得——哈,君子報仇,一百年不晚,高XN,你還該我一拳呢,何時還?
后來隨著時光一天天逝去,我們長大一些了,逐漸知道蜻蜓是益蟲,就不再逮它們了。乃至于有時看見它們傻傻地落在觸手可及的花葉上,還要去搖搖花葉,叫它們高飛,免得遭受屠戮。如果有外院的孩子來逮它們,就趕快去告訴傳達室的爺爺,把他們趕走……可惜現在,蜻蜓越來越少了,連普通的“紅果”“黃果”都難以見到了,更何況“大老桿兒”!
樹上的蟬兒也是我們一天到晚都想得到的寶貝,但大院孩子都不叫它們“蟬”,也不稱“知了”,而是叫“季鳥兒”——大概全北京的孩子都管它們叫“季鳥兒”吧?多么形象、生動的名字,它們真的就是一季的“鳥兒”呀,一生經過受精卵、幼蟲、成蟲三個階段,每到夏天,早年產下的受精卵會孵化成幼蟲,鉆入土壤中,以植物根莖的汁液為食,等幼蟲長大后,爬到地面上,蛻去黃澄澄的外殼,就羽化成有翅膀的蟬兒,飛到高樹上去鳴叫啦。孩子的階段與成人的就是不一樣,那時聽慣了季鳥兒叫,一點兒也不覺得吵,也不煩,相反,它們突然在窗外叫起來的時候,還會興奮地扒頭去找,真希望能逮到一只,放到家里讓它叫。我記得有兩三次,真看到它們像一枚小炮彈似的,“騰”地在樹葉間彈起身,由一棵樹彈到另一棵樹上。可是我從來也沒逮著過它們,那是男孩子們的絕招兒,他們在長長的竹竿頭綁上一根小細棍兒,抹上用猴皮筋兒熬制的膠,然后揮舞著竹竿,炫耀地從我們面前走過,身上的小網兜里裝著他們的戰利品,有時那些季鳥兒還特給力地叫上一聲。
我很早就知道季鳥兒是害蟲,每當它們渴了、餓了,就用自己堅硬的口器插入樹干,吸吮汁液,把大量的營養與水分吸入身體中,用來延長自己的壽命,所以我們逮季鳥兒都理直氣壯,一點兒也沒有負罪感。但我直到今天讀了相關的書籍,才知道只有雄蟬會鳴叫,它的發音器在腹肌部,像蒙上了一層鼓膜的大鼓,鼓膜受到振動而發出聲音,由于鳴肌每秒能伸縮約1萬次(天吶,太天才了!),蓋板和鼓膜之間是空的,能起共鳴的作用,所以其鳴叫聲特別響亮。它們還能輪流利用各種不同的聲調,激昂地唱出不同的歌曲。雄蟬的喊叫,一是為引誘雌蟬來交配,二是與其他雄蟬的集合聲,三是被捉住或受驚飛走時的吼聲。但好玩的是,雄蟬只會叫,聽不見;雌蟬不會叫,只會聽,你看,大自然是多么高明的締造師啊!
還讓我大為驚愕的是,你道世界上有多少種季鳥兒?說出來嚇死你,居然已知的就有3000種!因此,它們的名字也特別多,自古以來,有:蜩、蜺、蝒、螓、蠽、五色、日暮、丕蜩、茅蜩、秋蜩、蚱蟬、寒蜩、寒螀、螂蜩、蜻蜻、蜓蛛、螗蜩、蟪蛄、螗蛦、馬蜩、螇螰……哎喲,有些字,我學中文的都是第一次看到,不認識,念不出發音。還有,雖然它們是害蟲,但中國古人認為它們棲息于高處,餐風飲露,生性高潔,故對它們頗有偏愛,很多古詩寫到了它們。最有名的有三首,都是唐代大詩人的:
其一:
《蟬》 虞世南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其二:
《在獄詠蟬》駱賓王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其三:
《蟬》李商隱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文學史上的評價是,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
從前我以為“螞蚱”和“蚱蜢”是同一種昆蟲,后來才知道“螞蚱”就是蝗蟲,平頭圓腦袋的那種;而“蚱蜢”是我們俗稱的“呱嗒扁兒”,長身子,尖頭,上面有兩個尖角的須須。論地面上的活物,這兩種是我小時候見得最多、捉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的朋友。
剛搬到協和大院那會兒,草木多,人少,所以螞蚱特別多,個頭兒還大,稍不留神就飛到腳面上來了,對了,它們帶翅膀,會飛。有兩種顏色,綠的和土黃色;兩種個頭兒,大的能有大人的食指那么大,小的有半個小指頭尖兒大。我當然喜歡大個兒的、綠色的,其他孩子也是一樣,有的還給拴根粗一點的棉線,遛螞蚱玩。它們也不難逮,你只要看著它們雙腿一蹬,“噗”地一跳,你跟過去拿手一撲,就有了。捉在手里,給它掐個草葉兒送到嘴前,它便兇狠地咬住,不撒口,那樣子還滿嚇人的。而“呱嗒扁兒”就溫順多了,拿在手里,一般不拼命反抗,捏住它的雙腿末端,它就會僵住上身,一伸一屈地蹬腿,導致身體呈90度上下杠悠,十分有趣,這一“絕技”,螞蚱就不會。呱嗒扁兒的學名叫“中華劍角蝗”,飛起來能發出“呱嗒、呱嗒”的聲音,所以才得了這么個別名。在大院里,呱嗒扁兒比螞蚱少,依據“物以稀為貴”的原則,身份就比螞蚱金貴些。我不知道它算不算“蝗災”的一種?
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差不多我七八歲那一年,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發現大院里的螞蚱特別多,在地上蹦來蹦去,竟然還有兩只落在紗門上。可把我樂壞了,逮了好幾只大個兒的,拿回家玩兒。奶奶看見了,嘆了一口氣,說是“又不(知)道哪兒鬧蝗災了”?果然,第二天我聽小同學說,最厲害的地方,竟然有警察也不指揮交通了,拿著大簸箕在大街上掃那些蝗蟲!說來,那時我一個城里的小屁孩兒,真的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哪知道蝗災的厲害?后來我讀到普希金的《蝗蟲》詩:“蝗蟲飛呀飛,飛來就落定。落定頃刻全吃光,從此飛走無音訊。”心里隙隙有所動,據說這首詩是嘲諷沙皇派出的欽差大吏的,諷刺他們像蝗蟲一樣,所到之處,就把百姓全吃光。對于普希金這樣寫出《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騙了你》《致西伯利亞的囚徒》等杰作的偉大詩人來說,這首《蝗蟲》詩簡直像白話一樣簡單,起初我都不相信是他的作品,直到看了背景介紹才明白,這也算是表達詩人心境的一方面作品吧。
而最讓我接受不了的是,有一回在山東,吃飯時候的一道菜,居然是炸螞蚱。主人還將之作為珍肴,一而再、再而三地盛情邀請客人們“嘗嘗高蛋白”。我知道山東人愛吃昆蟲,以前就見他們吃過蝎子、蠶蛹、蟬蛹,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哈哈,不知山東人的豪爽里面有無這些“高蛋白”的貢獻?
北京孩子管螳螂叫“刀郎”,有時候,青綠色的它們也會從草叢里面鉆出來。樣子很萌,煞有介事地二目圓睜,朝你舉著大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可是肥胖的大肚子拖在地上,一邊舉刀,一邊沉思,倒把它們的游移不定表露得纖毫畢現,讓人哈哈一笑,捉住它們了事。不過它們畢竟是條好漢,你別以為這時你就贏定了,不,你一個不注意,它們的大刀就到了,能一下子把你的手指割出血,它可就趁機得勝回朝了。
蟋蟀是蟋蟀,油葫蘆是油葫蘆,兩種小蟲長得差不多,可是“社會地位”差遠了。記得小時候在大院里,倆男孩兒趴在草地上斗嘴,一個貶低另一個,輕蔑地說:“你那個哪兒是蛐蛐兒呀?那是油葫——蘆,嘁,不值錢!”最后那個“蘆”字,在他嘴里,不發二聲“盧”音,也非輕聲,而是發成第三聲“魯”,而且還用重音、還要拐上一個彎兒,以示強調。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油葫蘆”這個名字,又因為他如此之蔑視,所以就記住了。
他倆撲騰得渾身都是土,是在捉蟋蟀。北京人不叫“蟋蟀”,而是叫“蛐蛐”,連盛它們的罐子都跟著叫“蛐蛐罐”,這是因為這種小蟲能發出“瞿--瞿--瞿”的叫聲,因此而得名。嚴格說起來,那不是蛐蛐在叫,而是利用翅膀在發聲:在蛐蛐右邊的翅膀上,有一個像銼子一樣的短刺;左邊的翅膀上,長有像刀一樣的硬棘,左右兩翅一張一合,相互摩擦,就發出“瞿--瞿--瞿”的悅耳動聽聲響,讓人以為它們在唱歌。這些聲響有不同的音調和頻率,表達著不同的意思,比如在夜晚,蛐蛐們大聲地發出長節奏的鳴響,既是警告別的同性禁止進入其領域內,也是求偶的歌唱;而當有別的同性來犯,它便改為威嚴而急促的短鳴,以示嚴正警告。但油葫蘆就不會鳴叫,所以它們的身價一落千丈。
蛐蛐好斗,陰險的人類就利用這弱點,讓它們互毆,給自己找樂。據考證,這從唐代就開始了,還有名稱,叫“斗蛐蛐”,亦稱“秋興”“斗促織”。從那以后的一千多年過去了,華夏最愛斗蛐蛐的是宋代和清代,朝野內外俱大興斗蟋蟀之風,并有官宦富商將“萬金之資付于一啄”的,就是賭博,據說這還成了“具有濃厚東方藝術色彩的、中國特有的文化生活”。據說,甚至還形成了三種境界,第一種叫“留意于物”,其最典型代表是南宋宰相賈似道,竟然因玩蟲而誤國;第二種稱“以娛為賭”,把斗蟋蟀作為賭博手段;第三種是“寓意于物”,境界最高,多為文人雅士所為。直到今天,還有不少閑人持“文化”之名而樂此不疲。
對小孩子們來說,捉蛐蛐乃天性,當然不夾帶賭錢,但輸了,也很可能被小伙伴“訛”去一個心愛之物,比如一根冰棍或一個彈球什么的。這一般都是男孩子的玩意兒,我們小女生不敢把那小蟲子抓在手里,一是因為它們長得丑,土黃色,土里土氣的;二是它們爬得太快了,我們可怕它們鉆到衣服里面去。
蟈蟈也不少見,但大院里基本沒有,都是快秋天的時候,有人推著自行車,上面拴著高高厚厚的一大堆小籠子,帶著“嚯--嚯--嚯--嚯—嚯--”的一大堆叫聲,來叫賣蟈蟈。和賣別的不同,他也不用吆喝,蟈蟈們自己就喊了:“誰把我買走?5分錢一個!”現在早市上偶爾也還有賣的,但是得漲到10塊錢一個了吧——哎喲我還真不知道。
小時候,奶奶也給我們買過蟈蟈。拿回家來,叫我們去摘一朵不結果的老窩瓜小花,插進小籠子的眼兒里,說是蟈蟈愛吃,然后就把蟈蟈籠掛在窗戶框上。可把我們高興壞了,一會兒就去偷偷看上一眼,過一會兒再去偷看一眼,直到發現蟈蟈爬到花上了,便興高采烈地跑去報告:“爬上去了,蟈蟈吃花了!”待大肚子蟈蟈吃飽喝足了,心情好了,情緒高漲了,便開始唱歌:“嚯--嚯--嚯--嚯—嚯--”嘿,歌聲嘹亮,高亢動聽,連白云都聽得呆了,駐足不走了……
我們大院里有一株巨高的大椿樹,得有二三十米高,兩個大孩子都合抱不過來的那么粗。椿樹對我們有特殊的吸引力,是在于夏天時,樹干上經常會趴有兩種叫“大姐”的蟲子——為什么會叫“大姐”呢?這叫我至今也不明白,按理說在人世間,“大姐”的稱謂可全都是褒義的正面形象呀。
第一種叫“臭大姐”,指甲蓋大小,黑色身子,冷不丁“嗡”地就飛來了,落到人眼前,可是千萬不能打,因為它會釋放一股臭氣,非常臭,久久不散,是屬于惹不起的地痞流氓。它的中文學名叫“椿象”,別稱“臭腥龜仔”,因體后有一個臭腺開口,遇到敵人時就放出臭氣,俗稱“臭屁蟲”。據說世界上已發現其有3萬多種,多數是害蟲,而且居然還分門別類地加以禍害,比如有專門危害水稻的稻黑蝽、稻褐蝽、稻綠蝽等,有專門危害果樹的荔蝽、碩蝽、麻皮蝽等,有專門危害蔬菜的菜蝽、短角瓜蝽、細角瓜蝽等,只有一小部分以獵捕其他軟體昆蟲為食的是益蟲。此外,還有一種名叫“瓜黑蝽”的可以做成名貴藥材,李時珍《本草綱目》將其稱為“九香蟲”,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于是在我朝就必然引來“吃貨”了,一盤炒瓜黑蝽要價數百元;于是就必然還有后續,有人專門養殖瓜黑蝽當作食材賣,暴利呢——當然,這是當年的我們所萬萬想象不到的!當年的我們只知道,可以在爹媽面前撒嬌,可以在哥姐面前耍賴,可以在小朋友面前“臭訛”,但絕對不能在“臭大姐”面前任性。
第二種叫“花大姐”,居然有一個學問頗深奧的學名,叫“斑衣蠟蟬”,也是飛蟲,北京人形象地叫“灰蛾子”。成年的有小拇指上端那么大小,落在樹上時全身灰褐色,很難看,但一旦張開翅膀,內側膀尖上居然有一片鮮艷的大紅色,上覆小黑點,還綴著一小塊翠藍,也很晃眼呢。不過我們小孩子對這些漠不關心,也不碰它們。讓我們大感興趣的是它的幼蟲 “小象”,那時我真不知道“小象”就是花大姐的童年,還以為它們是另一種爬蟲。“小象”比蜜蜂還小一點兒,細瘦,渾身上下黑白碎點兒,有一只像管子般的尖鼻子,長得的確很像濃縮型的大象。它們爬在樹干上緩緩挪動,仔細點兒就看見了,很容易捉到手,而且它們溫順,女孩子們也不怕。放在手心里,起初它裝死不動,過一會兒看看沒什么動靜了,就一下子弓起身子快速爬動,企圖逃走。大孩子告訴說它們是害蟲,用那管子似的長鼻子吸吮樹汁,大樹就會被吸干,然后枯死。對此我表示出一小點兒懷疑:一是它的體量那么小,能吸多少樹汁?能把那么粗壯高猛的大樹吸死?二是這么多年了,不僅沒見大樹被吸死,它反而越長越高、越粗、越壯,可見迷你的小象根本沒什么殺傷力。不知為什么老讓我想起一句詩“蚍蜉撼樹談何易”——當時,毛澤東的37首《詩詞選》已經出版,大人孩子都會背“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
我小時候挺喜歡天牛的,也敢抓,然后拎著它們的兩條大“辮子”玩。因為它們長得不難看,黑色油亮的小身子,上面有漂亮的小白斑點,頭頂上那兩條大辮子也是一截黑一截白的美麗圖案,甩嗒甩嗒的,像極了穆桂英掛帥的那兩條大翎子。天牛也不鬼鬼祟祟的,不像蟑螂那樣見人就抱頭鼠竄,而是大模大樣地守護著它們自己的心情。
其實天牛挺兇的,有一張類似鐵鉗型的嘴巴,把一片樹葉放到它嘴前,立刻就能被咬爛,看著它那窮兇極惡的樣子,你心里還真襲上些許忌憚。但它實在是很好玩,比如當你抓住它時,它會憤怒地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拼命掙脫,企圖逃走。男孩子們抓到“天牛”,玩法特別多,什么天牛賽跑、天牛拉車、天牛釣魚、天牛賽叫等等,比起充斥市場的電動玩具來,玩這種活物自然有趣得多。比如“天牛賽跑”,就是用一根根細棉線把一只只天牛拴起來,然后把線拴在一起,放開手,天牛們就會向不同方向角力,結果誰也拉不動誰,就在原地團團打轉,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再比如“天牛釣魚”,方法是端來一盆水,將一個系著細線的魚形小片系在天牛角上,再將天牛置于另一個浮在水面的小木條上,天牛四周環水,局促不安,就頻頻揮動觸角,拉動細線,形同釣魚;而魚若離了水,釣魚就算成功。有時候還把兩只天牛放在一起比賽,以先釣起者為勝,各自天牛的主人給各自的天牛“加油”,勾心斗膽,滿緊張的呢。
據說天牛最喜歡呆在楓樹上,因為楓樹汁含糖量高,它們喜食楓樹的嫩葉、枝條和樹皮,還在樹干上打洞產卵,對樹木生長損害很大,是害蟲。大院里只有一株楓樹,在42號樓前,它分杈而長,樹干不粗,便于攀爬,男孩子經常在這株楓樹爬上爬下,捉到了就拿著他們的戰利品炫耀。我小時候跳過墻頭、上過房,但還沒淘到爬過樹,有一次是我從那株楓樹下走過,剛好看到一只天牛趴在矮矮的樹干上,就一順手把它抓住了。
42號樓原來住的是中國第一號病理學家胡正祥教授一家,胡教授位在“大神”級別,當年孫中山逝世的病例解剖就是他做的。他和夫人都特別喜歡孩子,經常允許大院孩子們去他家看電視,有空時還陪看,邊陪邊講解。一旦發現有孩子爬上楓樹林,便驚呼一聲:“小心!”趕緊雙手接住抱下來。可惜這一對恩愛老夫妻均沒有熬過“文革”。現在,42號樓前的那株老楓樹還在,年年春抽青芽,秋落紅葉,只不知道上面還有沒有天牛了?
大院里的昆蟲還多著呢,比如瓢蟲,幾乎任何時候都能在院子里發現它們,有黃色、桔色、紅色、米色、棗色、黑色的,身上一般都有斑點,有的2個、7個、9個、12個、28個……網查,全世界有5000多種瓢蟲呢,中國有將近400種。以我可憐的知識,只知道“七星瓢蟲”是益蟲,“二十八星瓢蟲”是害蟲,有時也會把它們放在手心里玩一玩。
蜘蛛更可怕,全世界的蜘蛛居然有42055種,這還是2010年的統計,近8年來不知又發現了多少種?中國有記載的約3000種。人們普遍認為蜘蛛是一種昆蟲,但實際上,它們與蝎子、蜈蚣一樣,不屬于昆蟲而是動物。小時候,家里出現蜘蛛,奶奶都不讓我們孩子打擾它們,說是“喜蛛”,報喜來了。典籍上居然有印證,陸璣《詩疏》載,“喜子(喜蛛)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即是說,荊州那地方的人把喜蛛喻為吉祥,認為喜蛛落下象征著“喜從天降”。這在中國北方農村也有此講:平時住在房角的一種小蜘蛛高懸在頭頂,一旦它們下來,從人的眼前跑過,家里準會有客人來,就像喜鵲一樣,跑到誰家門口的樹上叫,那家就有客人來……
所以,我不怕蜘蛛,也不傷害它們。可是不知為什么,我女兒天不怕地不怕,卻獨怕蜘蛛,怕得要死,從心里極度恐懼。我最怕的是壁虎,北京人稱“歇了虎子”,每年春夏一旦發現它們出現了,我就開始天天生活在恐懼中,晚上幾乎不敢出門。這心里陰影一直持續到現在,一把年紀了,還是怕,真怕!二十世紀90年代末,我跟著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緬甸,啟程時特高興,但到那里的第一天就急切地盼著打道回府了,因為緬甸是熱帶,生態環境又好,到處都是壁虎,大的能有一尺多長,連房間里都有——你洗個手吧,它“嗖”地鉆出來了!你刷個牙吧,它“嗖”地又跑過去了!半夜,本來我就緊張得睡不著,不料黑漆漆中,它們竟然又來了,還嘹亮地唱起歌來,聲音大如鳥叫,特別瘆人,把我嚇得頭皮一陣又一陣發麻……可是說來蹊蹺,我女兒卻不怕壁虎,就像我奇怪問她“蜘蛛有什么可怕的”一樣,她也不明白壁虎有什么可怕的?因此,別那么相信基因吧,看來也并不是那么靠譜哦。
鳥兒們
協和大院里樹多,鳥兒就愿意來呼吸新鮮空氣。每天早上一醒來,就能聽到它們在窗外練聲的練聲,唱戲的唱戲,熱烈極了。記得施特勞斯有一首鋼琴曲《森林波爾卡》,我相信,他一定是聽到了晨光中的眾鳥和鳴。
我在大院里見過的鳥,有燕子、喜鵲、灰喜鵲、麻雀、老鷹、啄木鳥、布谷鳥、烏鴉、鴿子,據說還有小伙伴見過貓頭鷹。有一天傍晚,我還生生地看到天上飛著一排南歸的大雁,它們已經飛得很低了,可以清晰地看到夕陽照在它們身上,把每一只的羽毛都染得一片金紅,它們一只只伸著長頸奮力飛著,隊伍整齊得像是用尺子劃出來的,那場面可真是壯麗的詩啊……
喜鵲的叫聲不用我形容,大家都聽過,“喳喳喳,喳喳喳”的,也有人聽到的是:“喜喳喳,喜喳喳……”從古代開始,古人就謂之為報喜之聲。我有一本《唐宋詞一百首》,開篇第一首便是寫喜鵲來送喜訊的:“叵耐靈鵲多謾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里。欲他征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云里。”(無名氏《鵲踏枝》)這是唐代民間流傳的一首愛情詞,上半闋是少婦口氣,說多嘴的喜鵲呀,沒憑沒據的,你來送什么喜?下半闋換成喜鵲的口氣,委屈地說,我好心好意來送喜,她卻把我鎖進籠子,盼她出征的丈夫趕緊回家來吧,就能把我放回到藍天白云里了……哈哈!
中國民間也有很多類似的傳說,比如“喜鵲叫,貴客到”“喜鵲喳喳,財寶到家”。到不到家先不說,那“喳喳喳”的叫聲確實好聽,給人帶來愉快的感覺,因為里面充滿了一個好字——“明”:明朗、明快、明曉、明暢、明凈、明澈、明晰、明理,還有光明、聰明、鮮明、啟明、精明、神明、圣明……總之各種好詞吧。其實,這都是人類心目中自己設定的主觀美好想象,實際中,喜鵲為了個體的生存,也是很兇悍的鳥呢,餓了或是要喂食自己的雛鳥時,它會狠心地盜食其他鳥類的卵和雛鳥,痛下殺手,毫不心慈手軟。可見在自然萬物中,什么都不能看表面現象,決不能看他(她、它)穿了一件美麗的花衣裳,或者說一嘴膩得流油的阿諛話,就認定他(她、它)們的心靈也像鮮花一樣,看鳥與看人,同理。
燕子的叫聲也好聽,“啾啾啾”的,古人形容為“啁啾”,古詩中提到它們的也很多。不過北京燕子的最美特色不在協和大院,而是在正陽門箭樓,也就是前門樓子。老北京人都知道正陽門的夕陽西下時,甚是壯美,藍濛濛的澄天,一座被晚霞皴染得流光溢彩的高大門樓,大群大群“啁啾”著飛過來、飛過去的嬉燕,那幅壯美的圖畫,簡直都能把人的心美“化”了。順便說一句,正陽門是北京最大的城門,正陽門箭樓是北京最高大的箭樓,從它建成的那天起,一直是老北京的象征。
灰喜鵲的外形跟黑白喜鵲有點像,但身上的“衣裳”不同,便不以為它們是同類了。灰喜鵲長得不難看,甚至還可以說有點兒漂亮:黑頭黑喙,小臉嫩白,翠藍色的身上披著一件淺灰色的“小坎肩”,下面拖著一條長長的深灰色大尾巴,在樹上棲息的時候,宛若坐在龍庭上的帝王,我每次看到它們這個高貴的姿態,都有一種想畫下來的沖動。
但是,它們可萬萬不能開口,因為那廝們的叫聲實在是太難聽了,“嘎——嘎——嘎”的,然又不像鴨“嘎”那么清清亮亮和正大光明;而是壓著嗓子,憋著悶氣,像是積了多少年的仇怨,刻毒地從胸腔里擠出來,聽著真叫人從心里往外不舒服——很多時候,能叫我聯想到大院里的一位長舌婦“三腳雞”,伊雖然也是干部,卻連家庭婦女都不如,整天揣著一肚子怨毒在大院里溜達,碰上誰就趨過去搭茬兒,追著探問人家的隱私,然后牢記在心里,伺機下手,陷害一下。在人類社會中、起碼在我們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中,確實有這么一種整天盯著別人的小人,他(她)們對別人的興趣遠遠超過自身,唯恐別人過得舒心,那是他(她)們非常痛苦的事。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他(她)們,想不透他(她)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反正大院人,都像討厭聽灰喜鵲的叫聲一樣,厭惡跟“三腳雞”說話,一見到她的身影就趕緊閃人。不過伊不以為恥,反而轉換了另一種“迂回戰術”,通過接近各家保姆來打探其主家的隱私,何其可怕也!
我于鳥類學真是無知,不知道啄木鳥會不會發出叫聲?但我聽過它們啄木頭的聲音,“磕、磕、磕、磕、磕、磕……”敲梆子似的一串連音響過,之后還有余音。小時候讀童話書,啄木鳥的身份是“大叔”,便以為它有多大個兒,起碼也像老鷹那么高大吧?誰想,直到多少年之后,我都長成大人了,才在某一天的某一刻,在開著的窗子前,突然聽到一陣“磕、磕、磕、磕、磕、磕……”,抬頭一看,有一只比鴿子還小一些的瘦鳥,正在外面的大洋槐樹干上坐著呢,它有花冠毛,長長喙,身上的羽毛是花的,有白色、橘色、黑色,自然流暢地組合在一起,還有一頂紅冠子,隨著它轉動身體,美麗的圖案不停地轉換。一道靈感的亮光突然劃過我的腦際,啊,這就是傳說中的啄木鳥吧?這只啄木鳥的家似乎就安在我們大院里,此后,我又好幾次看見它,每次都是在用力地“磕、磕、磕、磕、磕、磕……”,不由得又想起小時候的童話書,那上面說,在樹林里,啄木鳥大叔是最勤快的“勞動模范”。
也許,布谷鳥是中國傳統詩詞里寫到最多的鳥兒吧?但一般沒有直接寫成“布谷鳥”的,而是寫作“杜鵑”“子規”“杜宇”,為什么?
有典出自《史書·蜀王本紀》:約在公元前666年,望帝稱王于蜀地,后來他認為宰相鱉靈的能力比自己強,把國家交給他打理將會是萬民之福,就主動禪位,自己去了西山隱居修道。誰知鱉靈坐上王位之后,不僅把國家治理得亂七八糟,還霸占了他的妻子和女兒。望帝心急如焚地趕回都城,想奉勸鱉靈回心轉意,但城門緊閉,根本不讓他進城。望帝只得郁郁寡歡地回到西山,日夜掩淚痛哭,不久就因傷心過度斷了氣。死后的望帝化作一只杜鵑鳥,望著遠處的都城哀聲啼鳴,晝夜不止,發出的聲音極其哀切,所以叫“杜鵑啼歸”,簡稱“子規”;它甚至常常啼出一片片紅紅的鮮血來,滴到大地上,化作一片片杜鵑花……還有另一個傳說版本:也是在古代蜀國,國王杜宇勤勉治國,愛子愛民,常常跟老百姓一起下田勞作。他死后仍然心系百姓,變為一只杜鵑鳥,每到春季便叫人們:“布谷!布谷!布谷!”啼得嘴里流出鮮血,染紅了漫山的杜鵑花……這兩個傳說殊途同歸,便是成語“子規啼血”的來歷。
悲劇性的傷懷本是文學的最熱度題材,故此,古往今來,有關“子規啼血”的詩詞數不勝數,比如王維“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李白“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李商隱“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蘇軾“蕭蕭暮雨子規啼”;秦觀“杜鵑聲里斜陽暮”;文天祥“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
布谷鳥的叫聲很大,有時在屋子里安靜讀書,便能聽見一聲聲地從外面傳來,其音疾疾,其情切切,直催得人放下書,去到窗前張望。但可惜,它總是藏身在白云深處,只能聞其聲,不得見其影。我也曾多少次在大院里蹀躞,想與它們碰個面,哪怕只交流一個眼神也好,哀乎哉直到今日,沒有緣分得見它們的真容。
小時候在大院里瘋玩時,常常突然被一個疾音提醒:“快看,老鷹!”男孩、女孩便一起停下手里的各種忙活,抬頭去尋找老鷹。就見當空有個矯健的“一”字,忽上忽下,忽遠忽近,飄移在藍色的高天上,自由自在,相當傲然。便把我們一幫孩子羨慕得紛紛亂喊:“大老雕!大老雕!”
其實,老鷹與老雕還是有區別的:老鷹叫鳶,“紙鳶”是風箏的別名,顧名思義,可想而知;老鷹一般捕食兔子、田鼠、小雞等一類小型動物,有個著名的兒童游戲“老鷹捉小雞”即為印證,不然它為什么不叫“老鷹捉母雞”或“老鷹捉雄雞”呢?老雕是比老鷹還要大而兇悍的猛禽,是人們心目中真正的“雄鷹”,它們甚至能獵取鹿、山羊、狐貍等比它們自身的體形還大、還重的大型獸類,可稱得上是真正的“空中霸王”。
一般我們在城市里看到的,基本都是老鷹而非老雕,可是,大院孩子都愛管老鷹叫“大老雕”。可惜,現在已經看不見了,大老雕們都飛走了!
沒飛走的,最常見到的是這三種鳥——麻雀、烏鴉和鴿子,不知道它們是在忍辱負重地堅守陣地?還是厚顏無恥地茍且偷生?
麻雀是最大的冤案,曾經與老鼠、蒼蠅、蚊子一同為伍,被統稱為“四害”,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罪名是吃掉大量糧食,與老百姓爭食——現在想想,也是真滑稽,中華煌煌五千年,難道在什么朝代養不起小小麻雀而必須讓它們閉嘴?說實在的,麻雀在我朝也真沒什么好待遇,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光禿禿的冬日,我在大院的石板甬道上走著,忽然飛來一只小麻雀,就落在我面前的地上。我一看,不由得“撲哧”笑了,問它說:“小東西,你怎么這么臟啊?”一冬天沒下雨雪,它就跟一顆小黑煤球似的,身上的羽毛幾乎都看不出色兒來了,還又小又瘦,也真是可憐!我看到過英國的麻雀,一只只膘肥體壯,還都特別干凈,身上的羽毛雖不華麗卻也鮮艷,那是因為英格蘭雨水多,幾乎三天兩頭洗澡,所以一只只都捯飭得跟貴族似的那么有范兒。
烏鴉是人見人惡的鳥兒,不在于它們是益鳥還是害鳥,而在于它們長得太難看,在這個越來越重顏值的時代,尤其招人不待見。其叫聲又是最難聽,有時候你正好好走著路,它不遠不近地突然在你腦袋上怪叫幾聲“啊!啊?啊——”,能把你嚇一個激靈。說來特別奇怪,很多鳥都“啊”,很多走獸也“啊”,可誰都沒有烏鴉那一聲聲怪叫瘆人——烏鴉的“啊”是明顯帶著喪氣的,就像是從地獄里傳上來的鬼叫,立刻就能使人聯想到黑色、陰暗、骯臟、禍端、不祥……用北京話說,它們就是“喪梆子”,誰遇見誰倒霉。尤其是在暮色蒼茫的傍晚時分,它們會成群成群地、成大群成大群地在半空盤旋,一邊不停地、蠻不講理地、混不吝地“啊!啊?啊——”。此刻,再好脾氣的人也都加快腳步,縮起頭,想要趕緊離開那是非之地——對啦,就是“是非”二字:比起貓頭鷹是兇梟,烏鴉還不是黑老大,也就算是個“小人”吧?不過,小人不可得罪,他們比真正的敵人還可怕,你若不小心得罪了小人,得,大禍來了,他們會片刻也不放松地纏斗你,死纏爛打,沒完沒了,咱們干正經事的人可真沒工夫陪啊!
現在的鴿子似乎只剩下了圓滾滾、胖乎乎的形象,加上飯店里來不來就“烤乳鴿”,仿佛它們就僅僅成為了美味佳肴。過去,鴿子可不是這德行,它們與人類伴居已經有上千年歷史了。《圣經》里第一次提到鴿子是《舊約》里諾亞與和平鴿的故事:諾亞方舟停靠在亞拉臘山邊,洪水過后,諾亞把一只鴿子放出去,要它去看看地上的水退了沒有?由于遍地是水,鴿子找不到落腳之處,只好飛回方舟。七天后諾亞又放鴿子出去,黃昏時分,鴿子飛回來了,嘴里銜著橄欖葉,很明顯是從樹上啄下來的。諾亞由此判斷,地上的水已經消退。后世的人們就用鴿子銜橄欖枝來象征和平。在后來的年深日久里,鴿子曾長時間被人類派出承擔通信任務,曾屢立奇功。中國也是養鴿古國,隋唐時期在廣州等地,已開始用鴿子通信……
不過現在,人類的通訊手段實在是太發達了,什么互聯網、短信、微信,3G、4G、5G,科技越來越神通,絕對不勞駕鴿子了,于是它們只剩下兩個功能:賣萌和被吃——吼,忘恩負義的人類哦,當太平盛世時,鴿子是我們觀賞的寵物;一旦“禽流感”來了,就遠避它們而不及,完全都是從我們自身出發想問題,這也太自私自利了!
熱帶魚 ? ? ??
不知您還記得不?反正我記得,二十世紀60年代末,暴烈的“大革命”搞了好幾年,人們疲塌了,厭倦了,就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反面——北京人中興起了一股養熱帶魚之風。協和大院也被帶動起來,尤其是干部家庭中有男孩子的,屋里基本上都擺著一兩缸熱帶魚。
說是“缸”,可真有點大言不慚。那時生活還普遍貧困,一般干部家庭也不富裕,家家那點工資都是要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的;所以所謂“缸”,只不過是不知道從哪兒尋來的幾根鋁帶,用鉚釘一鉚,再買一毛錢膩子,把四塊玻璃往上一膩,大業就算完成了。
我們家的魚缸小得可憐,還沒有16開雜志大,多虧熱帶魚個兒小,不然在里面就轉悠不開了。最困難的是熱帶魚怕冷,北京的冬天難熬,就必須要有加熱器,可那玩藝兒比魚缸還貴,對于當時每月只領15元生活費的父親,我們無論如何也開不了口。還是我15歲的哥哥有辦法,花1塊多錢買了一根試管,還有電阻、石英砂什么的,自造了一根土加熱器,居然也安安然然地保佑著熱帶魚們過了冬。至于魚的吃食,全是哥哥走路到護城河邊上去挖線蟲,然后回家來,切開半個乒乓球,扎上許多小眼兒,把線蟲放進一小坨,吊在魚缸上面,線蟲往下鉆出頭,就被魚兒們吃了。有一回哥哥生病了,我替他去了一次,走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到,腿酸得都不會打彎兒了。
就這么窮了巴嘰的,您想我們能養出什么好魚?也就是孔雀、黑瑪麗和紅箭,這是當時最普通、最不值錢的三種,十分好養,自己家都能讓它們生下一群群小魚。也聽說過神仙、斑馬等品種,但只是存在一份美好的神往中——今天想起那一條條靈動的小熱帶魚兒,我的心上還會滾過一陣陣波濤,在當時那種人整人、人斗人,甚至人吃人的社會大動蕩中,怡然的熱帶魚給人們釋放了多少能量(正能量、負能量)和壓力;也給處于“黑五類子女”惡境里的我們兄妹,帶來了多少心靈慰藉呵!
后來,“四人幫”垮,歲月回到了正常軌道。時間的鐘擺不停,世事急急緩緩,一下子就到了二十世紀90年代。有一天到一位朋友家做客,迎面一座大魚缸闖進眼簾,有半個書柜大,里面一群群七彩繽紛的魚兒在穿梭,不是熱帶魚是什么?可惜我只認識少年時代的那三位老朋友,余下的,聽主人一一報出名字:神仙、紅綠燈、斑馬、銀鯊、白箭、吻嘴、藍寶石、地圖魚、珍珠魚……主人每報出一個,我便在心里驚呼一聲,沒想到,孩提時代視若神明的那些熱帶魚,竟然還有緣得見風采。
我想起少年時代的窮養,便敘述起來。朋友靜靜聽完,徐徐吁出一口氣,笑著說:“現而今養魚,可跟咱們小時候的窮折騰不一樣嘍。”說著,他按下第一個插銷,缸里立即“咕嘟嘟”地冒出一串氣泡,“這是給魚加氧氣。”又按下第二個插銷,“這是吸臟東西。”第三個插銷是凈化自來水,第四個是換水,第五個是恒溫……就連魚吃的線蟲也準備好了,一塊錢一份,可以喂一個禮拜。朋友說:“現在養魚早現代化了,什么都給你準備好了,差不多你只管欣賞就好了……”
今天又二十多年過去了,還有沒有孩子“窮養”或“富養”熱帶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