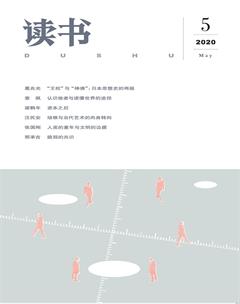語言的“通脹”與意義
岳永逸
一九八一年九月,日本人類學家中根千枝訪問成都時,“興奮而意外”地見到了已經(jīng)八十一歲高齡的李安宅教授。次年,東京大學東洋研究所出版了李安宅多年前的著述La brang: A Study in the Field(《拉卜楞寺—李安宅的調(diào)查報告》)。自此,李安宅重回學界視野。
二十世紀前半葉,李安宅是享有世界聲譽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他一九00年三月三十一日生于河北遷安縣灑河橋鎮(zhèn)白塔寨村,一九二四年,進入燕京大學的社會服務研究班,半工半讀,一九二六年畢業(yè)后在社會學系任助教,同時就讀于社會學系,一九二九年在社會學系的畢業(yè)論文是《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研究》。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李安宅先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學習。其間,前往調(diào)查了新墨西哥州的祖尼印第安人,參觀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民族復興教育。一九三六年歸國,執(zhí)教燕大社會學系,主編The Y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燕京社會學界》)和《社會學界》。一九三八年,奔赴西北,與夫人于式玉一道主要在甘南拉卜楞寺進行藏文化研究。一九四一至一九五0年初,執(zhí)教華西大學。其間,一九四七年前往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任客座教授一年;之后,直接赴英國考察,一九四九年歸國。一九五六年,調(diào)入西南民族學院(今西南民族大學),一九六二年調(diào)任四川師范學院(今四川師范大學)外語系。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病逝于成都。
一
一九三一年,是李安宅學術(shù)的豐收年—《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研究》和譯作《巫術(shù)科學宗教與神話》《交感巫術(shù)的心理學》紛紛出版。
《交感巫術(shù)的心理學》是弗雷澤(J.G.Frazer)《金枝》的第三章,包括巫術(shù)的原理、感致巫術(shù)或模仿巫術(shù)、染觸巫術(shù)和術(shù)士的進步四個章節(jié)。李安宅讀《金枝》的時間明顯更早。一九三0年,其《巫術(shù)問題的解析》一文就分為巫術(shù)的原理與種類、感致巫術(shù)、染觸巫術(shù)和巫術(shù)在歷史上的地位四節(jié),當然例證多數(shù)來自中國本土。自然,李安宅一九三一年的語言研究—《語言的魔力》(《社會問題》一卷四期)—難免就有弗雷澤巫術(shù)認知和馬林諾夫斯基(B.Malinowski)相關(guān)研究的影子。又因他對一九三0年前后在北京執(zhí)教的呂嘉慈(LA.Richards)“新批評”—將心理學、語義學引入文藝批評—的推崇,李安宅的語言觀就有別于一般的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
李安宅認為:(一)語言是人與動物的分野,人因語言而有了文化;(二)人創(chuàng)造了語言,語言也創(chuàng)造了人,什么樣的語言便成就什么樣的人;(三)“文字是將語言由著聽官移到視官的手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意義學》),因此語言包括文字;(四)作為“傳遞文化遺業(yè)的機構(gòu)”(《巫術(shù)與語言·編者序》)和情操或社會地位(象征)符號的語言文字,自具魔力,也是桎梏思想的障礙;(五)魔力和障礙都與巫術(shù)心理有關(guān),要去魔障,就需要探究語言、事物和思想間的關(guān)系,即建構(gòu)“意義學”。
在《語言的魔力》中,李安宅明確將語言視為一件有著交感關(guān)系的東西,并分為兩類:一是一經(jīng)說出就達到表情和社交目的的自足語言;二是具有巫術(shù)意義,并有神話在背后支撐的咒語。對尊者“金口玉言”“言出法隨”的盲從,同樣源于對語言巫術(shù)力量的迷信。文字是將語言從聽覺移到視覺的東西,對語言的迷信也就順勢變?yōu)閷ξ淖值拿孕拧1逼酱蠼中∠铩熬聪ё旨垺钡牧曀住⑶逵赫觊g的“文字獄”等,都是該文的例證。因為前者是基于接觸律的染觸巫術(shù),后者則是模擬巫術(shù)的相似律和染觸巫術(shù)之接觸律的混融。
對于國人姓名的巫術(shù)分析,即“名的魔力”一節(jié),是《語言的魔力》最為精彩的部分。陳垣的《史諱舉例》、胡適的《名教》和江紹原的《呼名落馬》都在其征引之列。然而,散布在字里行間的群眾、精英、城里鄉(xiāng)下、舊有新生的鮮活實例,才是李安宅分析的重點。對李安宅而言,上梁時“太公在此”之類的符咒,與“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彌陀佛”之類的宗教口語和人們在危難情急之下脫口而出的“媽啊”“(老)天啊”等并無不同,都是“初民對于基本需要的選擇作用,經(jīng)過巫術(shù)與宗教加以保存,兩相為用,脫口而出”。而保持團體秘密的行話、黑話,則有著“另創(chuàng)名目以保護原名的巫術(shù)信仰”的一面。與革命相關(guān)的例子,李安宅寫道:“‘北京改為‘北平,在南方就算平了北方;管蔣介石叫作‘蔣該死或倒寫在墻上,在討蔣的就算將他打倒了!”
“語言文字障”一節(jié),實則是十四年后《論語言的通貨膨脹》(《文化先鋒》第五卷第十五期)的先聲。在討論語言的魔障,即對人的桎梏時,《金枝》已經(jīng)讓位給呂嘉慈與人合著的《美學基礎》(The Foundation ofAesthetics )和《意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 ),因為語言文字障是專門針對當時的“智識界”而言。李安宅認為,這些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在不明就里的情況下,人云亦云地喊著“科學”“調(diào)查”“德謨克拉西”“自由”“平等”“委員制”等口號。一九三0年十月,李安宅就曾“死磕”胡適同月十七日信馬由韁講演的“哲學”(《駁“什么是哲學”—請教胡適先生》)。對“九一八事變”后盛行的有著魔力的“救國”,李安宅也一絲不茍地剝?nèi)テ洚嬈ぃā兜赖碌淖月膳c環(huán)境的改造》)。
一九四五年,在《論語言的通貨膨脹》中,李安宅引入“通貨膨脹”這個金融學術(shù)語。他認為:幣制是交換財富的手段,語言是傳達思想和情感的媒介;如同幣制與其背后財富不匹配而生的通脹,語言和語言背后的思想、情感的不匹配,就是語言的通脹。進而,李安宅將語言的通脹分為三類:(一)在科學上的無的放矢;(二)在藝術(shù)(包括一般藝術(shù)和人生藝術(shù))上的無病呻吟;(三)將陳述(statement)的科學語言裝飾成美善、將表現(xiàn)(expression)的藝術(shù)語言用于陳述事物之類的語言的誤用和濫用。科學語言和藝術(shù)語言這一分類,源自呂嘉慈《文藝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這些基本概念,早已出現(xiàn)在一九三一年李安宅對語言文字障的分析中。只不過藝術(shù)語言,當時翻譯為表情(emotive)的語言或詩的語言,科學語言又譯為指事( referential) 的語言。而且,在借用這兩個概念之后,李安宅迅疾指出了后來命名為“通貨膨脹”的語言的濫用:在詩里去找真?zhèn)危诳茖W文字中用上許多生擒活捉的比喻字眼等。進而,李安宅將通脹的原因歸結(jié)為四:(一)對聯(lián)文化;(二)起承轉(zhuǎn)合、音韻平仄、八股等限人極深的漢語格局;(三)樂于做“翻案文章”的文人積習;(四)作對聯(lián)、限格局和翻案的積習合力造成的“劣幣”語言對“良幣”語言的驅(qū)離。
其實,上述這些研究僅僅是個“引子”。借這個引子,李安宅嘗試回答的是:為何相對自然科學而言,我們的社會科學不發(fā)達?而且,他將中國社會科學的不發(fā)達指向關(guān)涉政治的“民主”和“開明的輿論”,即社會氛圍是否鼓勵人們說有意義和有效的話。
我國社會,抗戰(zhàn)八年的經(jīng)驗,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材料?然而紙料缺乏的今天,又有多少動人心弦的文藝創(chuàng)作呢?大部分還不是在作排字排句的工夫嗎?不在人格的充實發(fā)展處下工夫,則無怪情感不真摯,欣賞水平不高明,以致無病呻吟,而在藝術(shù)界也弄得語言走到通貨膨脹的地步了。(《論語言的通貨膨脹》)
語言的魔力和通脹之間明顯有著深度關(guān)聯(lián)。無論并列平行,還是互為因果,這依舊是在信息爆炸的媒介時代,我們置身其中的語言“境地”(situation/ecology)。唯其如此,在境地許可時,李安宅才更心安理得也是決絕地投身到實在、真切的社會科學的譯介與建構(gòu)之中。明了李安宅借學問憂天下濟蒼生的家國情懷,就不難理解《論語言的通貨膨脹》最終發(fā)出的對實地研究—“實際事物的體驗”—的感慨與呼召。
對李安宅而言,實地研究是土、洋八股的“頂門針”。當然,他所言的實地研究,是馬林諾夫斯基那樣,經(jīng)過人類學嚴格訓練,且具有透視力的有骨有肉的實地研究(fiel dwork),是獲取知識、產(chǎn)生真知(ethnography)的根本途徑。這與他在燕大、加利福尼亞、耶魯接受的學術(shù)訓練和廣博的涉獵、學術(shù)交往及抱負有關(guān)。奔赴西北前,他就撰文呼召國內(nèi)外同行攜手對中國進行經(jīng)驗研究(“Notesonthe Necessity of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38)。此外,這也應該與他認同進化論,并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而接受了唯物論有關(guān)。
二
近些年來,燕京學派的研究頗有聲勢,而與燕大有著深度淵源的李安宅,卻少有人知。人們偶爾提及李安宅,也僅僅因為他曾在一九三八年陪同耶魯大學教授歐茲古(C. Osgood)踏訪過昆明高峣旦族村月余。又因中根千枝對李安宅“藏學”研究的著力重現(xiàn),尤其因其與成都“華西壩”的淵源,人們似乎又認為李安宅是位藏學專家或邊疆學家。僅從李安宅對語言的研究而言,這兩種定位都不免偏頗。
事實上,與其說李安宅是狹義的社會學家,還不如說他是廣義的社會科學家。這或者與他始終關(guān)心語言的能指與所指,且力求實事求是、我手寫我口而名實相符的“實學”定位有關(guān)。何況,他又始終是以“不求償?shù)姆e極主義”律己:做事情,只求積極,不求償于外界,成不居功,敗不灰心(《社會學論集:一種人生觀》,1頁)。為求用語的精準,一九三一年,他甚至與張世文等同仁一道,編輯出版了《英漢對照袖珍社會學辭匯》(An Anglo-Chinese Glossary ofSociological Terms )。這一切,見出他的實在與嚴謹。
如果以一九三八年作為其研究整體上從理論到實用、從“雜學”到藏學(邊疆學)的分水嶺,那么他離京前試圖給人們明目醒腦的理論譯介與研究則有著格外的口碑。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意義學》的“序”中,馮友蘭認為該書對中國是“有用的藥”。哲學家全增嘏則贊該書是“近年來介紹西學學術(shù)的最有價值的一本書籍”(《李安宅之“意義學”》)。一九四六年,在《語文學常談》中,朱自清也肯定《意義學》譯介西方科學方法之功。一九三八年,在燕大法學院給本院社會學、經(jīng)濟學和政治學三系本科生編訂的《社會科學概論選讀》中,李安宅的《語言思想與事物》《巫術(shù)與宗教》《巫術(shù)的分析》《介紹社會科學集成》四篇在列,吳文藻僅有《社區(qū)的意義》一篇,后來居上的費孝通未有篇目入選。
一九三八年前,李安宅的實地研究不多,但一出手就是精品。一九三五年六至九月,作為第一位進入印第安部落的中國學者,李安宅在新墨西哥州調(diào)查了祖尼人。其成果《 祖尼人:一些觀察與質(zhì)疑》(Zu?i: Some Observations and Queries , 1937),在當時就受到斯皮爾(LesileSpier)和功能學派大師布朗(Radcliff-Brown)的交口稱贊(陳波:《李安宅:回憶海外訪學》)。至今,該文也是祖尼印第安人研究的經(jīng)典。
然而,這項經(jīng)典研究,其成功之處并非提供了多少“事實性的信息”,也非一篇會講故事的民族志,而是在其參與觀察的基礎之上,對已有的關(guān)于當?shù)厥聦嵢菀自凇八枷肷显斐苫靵y”的“個性化描述”的再詮釋。雖然是對祖尼人的實地研究,李安宅充分調(diào)動并激活了他已熟稔的意義學—他辨析的是語言、思想(心理)和事實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且是祖尼人、本尼迪克特(R.Benedict)等李安宅熟識的祖尼研究者和李安宅本人三種“語言—思想—事實”之間交互影響的動態(tài)關(guān)系。這些絕非吹毛求疵的精微辨析,確是出于能獲得一種文化洞察力,以求用于追求真理的更廣闊研究之初心。
在相當意義上,哲學和語言學是李安宅從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雙拐。或者,稱李安宅為中國社會人類學家中的哲學家、語言學家,并不為過。相較燕京學派諸公而言,李安宅更關(guān)注人,更喜歡立足于社會科學,這或者也是一九三八年他將《社會學論集》副題命名為“一種人生觀”的根本原因。
李安宅對哲學、美學與語言學的興趣,則有著張東蓀、呂嘉慈這些國內(nèi)外師友的幫助與啟迪。一九三八年奔赴西北前,李安宅與師長張東蓀唱和頻頻。哲學家張東蓀有意“把哲學和社會學打通”,專業(yè)本是社會學的李安宅則對哲學心有戚戚。在張東蓀主編的天津《益世報》“社會思想”專欄,李安宅是如期出現(xiàn)的“簽約”作者。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給《社會學論集》寫的序言中,張東蓀認為:該書是一個多艱時代的“映相”,為新舊文化之爭中出現(xiàn)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觀點與想法。一九三三年初,李安宅為張東蓀五個月前出版的《現(xiàn)代倫理學》撰寫了書評,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美學》則隸屬張東蓀主編的“哲學叢書”。一九三八年三月,李安宅譯出曼海姆(K.Mannheim)的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of Knowledge (1936)一書第五章,名為《知識社會學》,其本意就是想給對曼海姆有批評的張東蓀《思想言語與文化》“作個附錄”,以資比較參證(《孟漢論知識社會學·譯者按》)。不僅如此,李安宅還將張文翻譯成英文,刊發(fā)在次年的《燕京社會學界》。自此該文漂洋過海,直至成為克里斯蒂娃(J.Kristeva)“互文性”理論的重要生發(fā)點之一(《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演講集》)。
一九四四年,李安宅出版了譯著《知識社會學》。出于知識社會學是社會學“指南針”的新認知,曼海姆和張東蓀的兩個中文語本間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反轉(zhuǎn):張文成為附錄。明了了以李安宅為中介的曼海姆和張東蓀四個中英文語本之間的多向“互文性”,我們也就知道中西會通的李安宅,不固守于任何一端的獨立性。或者,翻譯曼海姆最根本的原因,是知識社會學關(guān)注的思想產(chǎn)生和接受的背景,實乃新的領域,有著新的觀點與方法。如果說李安宅精心譯介曼海姆的入口是社會學,那么出口應該是更偏向哲學,更重認知論與方法論,更重思想、思維方式和知識本身。對于被他者命名和不停演繹的燕京學派而言,即使算不上獨行俠,李安宅也大抵是個若即若離的自由分子,甚或旁觀者。
對于長期探討語言、事物和思想三者關(guān)系的李安宅而言,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與呂嘉慈關(guān)注的作為思想工具之語言文字符號的“語義學”不無相通之處。作為二十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文學理論家,呂嘉慈一九二九至一九三0年執(zhí)教北京。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講授文藝批評等課程的同時,作為客座教授在燕大講授“意義的邏輯”與“文藝批評”,并與燕大國學研究所、哲學系同仁一道研讀《孟子》。經(jīng)常互訪、吃飯、聊天、切磋學術(shù)的呂嘉慈與李安宅,形成了在京“私人感情最為深厚”的師友關(guān)系(容新芳:《I.A. 瑞恰慈與中國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對話及其影響》)。
一九三三年雙十節(jié),李安宅撰文《批評與宣傳:因“基本英語”而引起的評議》,為呂嘉慈踐行的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鼓與呼。一九三四年,《意義學》初版,呂嘉慈為之撰寫的“弁言”末句是:“李安宅先生會因我的影響產(chǎn)生這本意義學嘗試集,使中文讀者注意這等問題,真令我非常高興。”李安宅“自序”的首句則是:“這本東西,直接間接,都是呂嘉慈教授底惠與。”反之,呂嘉慈的Menciuson the Mind (《孟子論心》) 一書,則有著李安宅的幫助,包蘊著李安宅的心得、識見。在《美學》“什么是美”一章,李安宅對美的三大類十六小類的辨析,就是根據(jù)呂嘉慈《美學基礎》一書,該框架也用到了《意義學》對“意義”的細讀之中。在《美學》“參考書目”介紹的最得力的八本著作中,呂著《美學基礎》《文藝批評原理》和《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 )位居三甲。此外,呂嘉慈還是促成李安宅“安心學術(shù)”并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前往美國留學的功臣之一。一九三二年底,在李安宅準備組織義勇軍時,呂嘉慈來長信勸說道:“救國之圖多端,鍛煉學術(shù),亦為其一。”( 汪洪亮:《李安宅的學術(shù)成長與政治糾結(jié)》)
為推廣“基本英語”,一九三六至一九五0年,呂嘉慈又數(shù)次或長或短地來到中國。或者因為一心要做邊疆實地研究,李安宅似乎與呂嘉慈沒有了交集。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在耶魯任教期間,李安宅與在哈佛的呂嘉慈同樣失之交臂。一九七九年五月,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隆重受邀的呂嘉慈拖著年邁的病軀再次來到中國,在數(shù)地巡講,終致一病不起。洋人老友來了,身體還算硬朗的李安宅,未曾有當年吳文藻、費孝通特地被從“五七”干校召回面見老友費正清(J.K.Fairbank)的榮幸,而是繼續(xù)在獅子山蹣跚獨行。
時值李安宅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誕辰,是為記。
(《巫術(shù)與語言》,李安宅著,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版;《意義學》,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