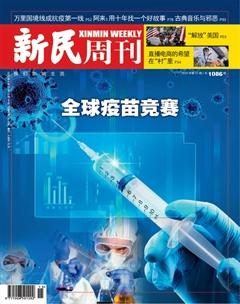一個會撩妹的張生
何日君回來

茅威濤演繹的張生堪稱經典。
戲曲創新一直在迷惘中進行艱難探索,小劇場戲曲音樂劇等形式輪番上陣,而好評寥寥,這時候回顧浙江小百花的《西廂記》或者能給我們一些些啟發。
習慣傳統戲思維的觀眾很可能不喜歡這部戲,話劇式的大轉盤影響了演員的程式,鶯鶯一角不夠立體,以茅威濤為絕對中心,而且這個張君瑞不符合那個時代價值觀,不求功名只求愛情,非常自戀、外放……本質上,這已經不像《西廂記》的故事了,而更像瓊瑤劇。但是這卻正好是浙百《西廂》的成功之處。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一個演給現代女性觀眾看的戲,就很好理解了——這就是偶像劇嘛,女主角千篇一律,鶯鶯心里想什么,誰關心?女觀眾愛看的就是男主角帥氣撩妹,反抗各種障礙,據理力爭自己的愛情……不是嗎?試問誰看《惡作劇之吻》會有心思去研究男主角為什么愛女主角?絕對不會的。我們只會覺得,哇,江直樹好帥喔。
如果我們對比上越和浙百兩個版本《西廂》,感覺會更明顯,上越的張君瑞是很老實的,但到了浙百就風流瀟灑多了——上越的張君瑞讓紅娘去做媒,還說“紅娘姐,我給點銀子,你去幫個忙。”這太有損偶像劇男主角形象了,你怎么拿錢說事兒呢?于是,到浙百版,這一片段就去掉了。同時,上越的張君瑞是被動的,要鶯鶯暗示,才敢造次,但是偶像劇的男主角一定不能老實啊,偶像劇的男主角要么高冷,要么瀟灑,老實人誰愛啊?所以浙百版的張君瑞就瀟灑主動了。

周全《最美的手》
如果大家能體會這個思路,就會知道茅威濤為什么演得那么外放,引用了那么多戲曲之外的創作手法來演張君瑞了。比如在遇到鶯鶯那一場,張君瑞一下子看到美人,驚呆了,于是,茅威濤的動作,首先是手中的扇子扇著扇著,掉了,他還不知道,手還在扇動,來表現張君瑞真是看呆了,扇子掉了也渾然不覺。這種演法是非常現代的一種思維。傳統戲重視人物身份,書生什么時候拿扇子都是有規定的,拿什么扇子也是有規定的,此時此刻卻把扇子都掉了,這從傳統戲的角度來說,太有失身份了,不像個讀書人。但是,茅威濤為了讓這個人物現代起來,干脆把這個禁忌打破了。
再比如張君瑞有個動作,踢褶子,這又被人罵動作幅度太大,不符合古代書生的氣質,那茅威濤自己知道不知道動作過火呢?肯定知道。她在采訪中講過,這個動作是借鑒了川劇的技巧。茅威濤為什么還要冒著這個危險呢?為了貼近現代觀眾的思維,那種熱烈的,外放的情感表現,而不是傳統的那種往內縮的情感表現方式。這也是浙百《西廂》演出后爆紅的原因,它的現代性,偶像劇性,吸引了一大批粉絲。
當然,這個偶像劇式《西廂》有個難題,男主角要非常厲害,因為全場的看點就只看他一個人撩妹。從這點上來說,浙百《西廂》的成功,跟茅威濤個人的舞臺魅力和舞臺掌控力有很大關系。
茅威濤之后呢?沒有那么大舞臺張力的演員,該如何接棒浙百張生?這同樣是如今新編戲的一個難題,大劇團耗資重金,在城市劇場能演出的高大上的新戲,能被民間劇團拿去演嗎?
經典的戲曲不屬于一代人,要考慮代代相傳。經典的戲曲也不屬于一個團,還要考慮這些戲是不是能由其他兄弟劇團接著往下演。橫向縱向都要考慮到,才有勃勃生機的越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