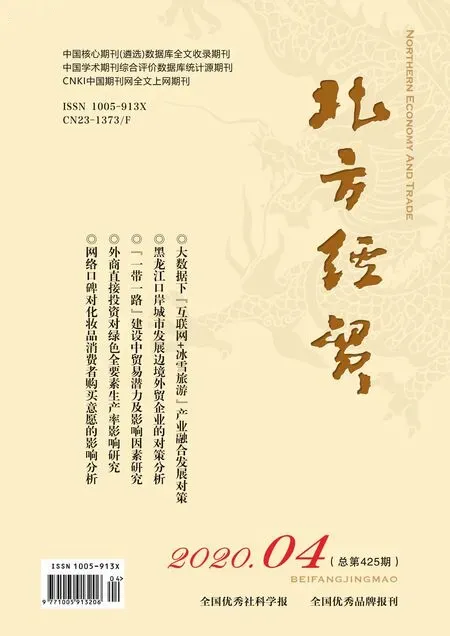中國如何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袁宏恩
(新疆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烏魯木齊830000)
1987 年,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戰略。十九大報告也提出了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三個階段”部署,即到2020 年,是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定性時期。2020 年至2035 年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期;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到2050 年建成現代化化強國。這比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的實現現代化提前了15 年。要成為現代化強國,人均國民收入必須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2017 年中國的人均GNI 排名世界第66 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我國正處在轉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長期粗放式發展,目前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大,發展中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中國能否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內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發表了相關論文。
一、概念闡述
(一)衡量國家收入水平的指標和標準
世界銀行按照“人均年國民總收入”作為標準,收入水平不同的國家分為四類,即高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以及低收入國家。標準是每年變化的,每年7 月份核定新標準。該劃分方法是基于Atlas 方法計算的人均GNI。用于計算和相關閾值的單位是現價美元。2018 年7 月1日,世界銀行發布了最新標準,即人均國民收入門檻(現價美元),人均收入低于995 美元是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996-3895 美元屬于中低偏下收入國家,人均收入為3896-12055 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人均收入超過12055 美元的屬于高收入國家。

表1 2017 年世界部分國家(地區)人均GNI 排名
表1 顯示2017 年人均GNI 排名前10 名的國家,瑞士、挪威、盧森堡分列前3 名,美國排名第6。表1 同樣顯示2017 年我國人均GNI 為8690 美元(現價美元),處在第66 位,屬于上中等國家。
(二)中等收入陷阱
當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達到國際中等水平時,就無法順利實現國內經濟發展方式的進一步轉型升級,經濟發展將停滯不前,這種現象被稱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首次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 年)”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理論如下,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時,可能會出現兩種結果:第一種是持續發展成功躋身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基本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掠奪和殖民擴張,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形成了強大的經濟基礎,英國、德國、法國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少數東亞國家成功跨越成為資本主義大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主要依靠工業化;此外,發展的結果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國家和一些東南亞國家。一方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這些國家無法在工人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另一方面,他們無法在尖端技術領域等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國家出現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國家發展陷入停滯狀態或經歷大幅度波動,社會矛盾激化,引發社會騷亂,國家可能會出現倒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廣泛傳播,因為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相對有針對性和現實的,專家學者對它們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發表了許多論文。主要研究內容有描述經驗事實,陷入陷阱的原因,陷入陷阱國家的研究以及對中國的警示、突破陷阱的啟示等。“中等收入陷阱”理論起源于發展中國家的追趕模式,主要分為兩類,兩類國家都實現了工業化。這兩種國家都享受了工業化帶來的好處,也都經歷了或者正在經歷高增長之后的停滯和彷徨。第一種是中央計劃體制下的國家,如蘇聯和東歐;第二個是特權國家,以東南亞和南美洲國家為代表。第一種模式說明計劃經濟機制會使國家長期處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因為在缺乏私人產權和市場的蘇聯和東歐中,工業化紅利消失殆盡,經濟增長失去了動力,國家增長只能依靠強制資本積累,增加投資,保持經濟增長,但由于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存在,單位收入只會隨著規模的擴大而減少,經濟逐漸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種國家是因為權貴階級和大家族把持著國家的經濟命脈,為了和別人競爭,私人企業家把主要的時間、精力用在和政府保持密切關系,而不是用在擴大生產上。甚至有些權貴直接參與到生產經營中去,榨取民脂民膏。國家經濟與大家族和權貴階級的動向息息相關,存在著不穩定性。東南亞國家經常出現軍人政變的現象,國家經常因此陷入動蕩,經濟發展缺乏穩定的發展環境,難以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泰國就是鮮明的例子。
二、經濟現狀分析
2016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經濟高增長率不再是唯一追求目標,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高速,近幾年經濟增速都維持在6.5%以上。在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的同時,必須更加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重視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收益感。在過去40 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在前30 年中一直處于快速增長期,平均增長率超過10%。2010年,中國整體經濟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按目前的增長速度,超過美國的總經濟產出時間不會太久。但是我們應該深刻地認識到,我國的人均GDP 的排名遠沒有經濟總量排名靠前。2017 年,中國人均GDP 超過8,800 美元,排名第70 位,處于中等水平。中國的人均GNI 排名第66 位,也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我國人均GDP 和人均GNI 排名比較靠后,一方面是因為我國人口較多,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不高,人均創造財富相對不高。長期以來,中國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的發展模式,實現長期高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帶來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資源環境破壞比較嚴重。人均收入增長率長期低于GDP 增長率。為此,政府逐漸改變唯GDP 論的經濟發展考核體系,要求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同時實現人均GDP 增加,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這樣能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
三、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理論中有三種收入陷阱理論:低收入國家存在“馬爾薩斯陷阱”,中等收入國家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國家存在“代際貧困陷阱”。低收入國家可以通過工業化實現經濟起飛來跨越“馬爾薩斯陷阱”,中等收入國家則很難實現跨越。根據世界銀行1960 年的統計數據,截至1960 年,101 個經濟體實現了經濟起飛,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但這些經濟體中只有13 個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數國家都未能跨過。
為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會如此困難?結合世界各國的經驗,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未及時增加人力資本投資,走內部價值創造之路;第二,未能適時地對僅僅適合于經濟起飛時期的、政府主導的追趕型體制加以改革,從而壓制了市場力量發展;第三,過度的收入再分配導致投資下降和勞動參與率下降,使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知道了前人未能實現跨越的原因,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處理好以上存在的問題,需要做到:第一,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第二,適時推進經濟體制轉型;第三,人均收入差距要控制在適當的水平,不能過大,也不能削弱積極性,和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要解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需要建立制度性的市場經濟。建立適當的制度性市場經濟可以為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相應的制度支持。在經濟起飛階段,市場可以由政府主導,但是在中等收入階段,政府過度的干預經濟將會擠壓私人資本的發展,導致經濟發展的低效率。為此,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將要逐步過渡到以市場為導向的體系。1992 年,黨的十四大提出要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充分認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對市場經濟的深刻理解,2013 年黨的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正式提出,要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必須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正在增加,政府正在轉向服務型政府。市場經濟可以通過價格調節機制調整供需平衡,兼顧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需要看到的是,現實中市場的地位仍然會存在被忽視或者被低估的現象。政府管的過多,擠壓了市場的活力。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創新發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徑。創新不是發明,創新是顛覆性的發展。諾貝爾獎獲得者埃德蒙菲爾普斯對創新做出了非常有用的定義:發明不是創新,“復制”“轉移”和“適應”不是創新,它們在本質上是“應用”;改頭換面的“舊創意”更不是創新;外部技術的引入不是創新,它只是模仿“外部創新”;真正的創新是內生和本土創新。勞動力元素創造新的組合,構思和生產新產品,并最終完成生產和銷售過程。創新做的最好的國家是美國和德國。美國主張毀滅性創新,因此電腦取代了打字機,數碼相機取代了膠卷,平板取代了電視。德國則是通過科學與技術緊密結合來實現創新,德國的大學實驗室建設在企業內部,產學研深度結合,大大提高了科學技術的轉化成生產的效率。這一方面做得不好的國家是日本,雖然日本的很多科學家獲得了諾獎,科學研究水平也很高,但是科技轉化效率特別低,大大影響了日本的發展,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特別是20 世紀90 年代經濟泡沫破滅以后,日本經濟長期以來經歷了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日本的深層次問題是缺乏企業家精神,這源于日本社會所信奉的儒家文化和武士道精神。儒家文化強調等級秩序,武士道又特別強調下級服從上級,企業內缺乏自由,創新無處實現。
十九大報告強調,國家經濟發展必須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排在首位,可見創新的重要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將長期引導中國經濟發展。
開放是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重要方式。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人均不到300 美元的貧窮落后國家躍升到人均收入超過8800 美元的上中等收入國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據海關統計,2017 年,中國商品貿易進出口總額27.79 萬億元,其中出口總值1 533 萬億元,同比增長10.8%;進口額達到12.46 萬億元,增長18.7%;貿易順差2.87 萬億元,收窄14.2%。三大貿易伙伴的進出口同時增長,“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國家的進出口有所改善。2017 年,中國對歐盟,美國和東盟的進出口分別增長15.5%,15.2%和16.6%,這三個貿易對象占到中國全部進出口總值的41.8%。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大驅動力之一,長期以來,出口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較高。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改革開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中國必須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中國的發展才會持續下去。明清時期國家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雖然暫時抵御了外敵的侵略,但是近代的百年屈辱史告訴后人,閉關鎖國的政策是失敗的,中國大大落后于世界發達水平。古代中國長期領先于世界,與我國開放包容的文化有著很大的關系。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明確地告訴我們,開放會讓我國發展進步,封閉自我只會讓自己落后于世界大勢。
學者們就如何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行了討論。王麗莉等認為一個由國家主導的自下而上的“從農村到城市的”“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的”立足于制造品(包括原始手工品)出口而不是農產品和原材料出口的工業化發展路徑和產業升級政策,是成功跨越各種收入陷阱的關鍵。高淑桂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與經濟發展相關聯的制度匹配,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轉變為高收入國家行列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的一項重要任務。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維持在3.5%—6%的增長速度,超過12000 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成為高收入國家不是問題。40 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未來改革開放的腳步不會停下。要想實現現代化乃至成為現代化強國,改革開放是必須要走的道路。過去我們閉關鎖國,落后于世界強國,有了百年屈辱史。歷史是鏡子,以史為鑒,我們更要堅定改革開放的決心。改革內部,破除經濟發展的制度束縛;對開放外,引進資金,學習先進管理經驗,同時也要走出去,提高對外投資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