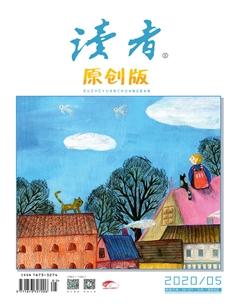我們無處安放的美好情操
祝羽捷

一
偶然發現,我喜歡的好幾個人物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活著活著,突然不知哪里不對勁,都隱居到鄉下去了,好像結束了一份兢兢業業的工作,得給自己放一個悠長雋永的假期。
亨利·摩爾在42歲的時候搬到了小村莊佩里·格林,我從他的工作室寫字臺前的窗戶望出去,一群圓滾滾的黑臉羊正匍匐在他的雕塑周圍打盹兒;地道的倫敦人約翰·伯格在47歲時隱居到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小村莊昆西,他不再關心政治,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人類愛莫能助的事情上,比如四季的變化、動物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樂;E.B.懷特也在39歲時辭掉雜志社的工作,跑到緬因州當農民,養豬養雞,孵化雞蛋,給母羊接生。
我有時在倫敦也待不住,想去鄉下住幾天,從國王十字街火車站出發,那心情就跟《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聽聞舅母一家將邀請她去湖區游玩時一樣狂喜。
連續三年,我都住在名叫“The Wild Boar”的湖區農舍里。那里的標志是一頭野豬,有古老的木頭房屋,用木柴點燃的篝火在壁爐里跳躍,晚飯永遠是它家招牌的烤豬排和自釀啤酒,這一切滿足了我對英國鄉村生活的想象。
雖然每次來的季節不同,但都避開了冬季。湖區的朋友告訴我,每年圣誕節后的1月和2月是他們最忙的時候,忙著努力工作賺錢,等春天來了,誰還坐得住呢?
二
湖區自然是美,能輕而易舉占據人的心,不然不會成為英國本土最受歡迎的度假地。
沒有氣貫長虹,也沒有重巒疊嶂,那種美從靜謐中幽幽地沁出來,像一位最嫻靜的淑女,只是坐在那里,不動聲色,就足以讓人轉不動眼睛。每每面對湖光山色,或聞到水仙花香,你總想借景抒發一下情感,贊美這美妙的自然風光,想到的都是湖畔詩人的詩句。
最容易想到的當然是威廉·華茲華斯的《水仙花》:
我孤獨地漫游,
像一朵云,
在山丘和谷地上飄蕩,
忽然我看見一群
金色的水仙花迎春開放,
在樹蔭下,在湖水邊,
迎著微風翩翩起舞。
連綿不絕,如繁星燦爛,
在銀河里閃閃發光,
它們沿著湖灣的邊緣,
延伸成無窮無盡的一行,
我一眼看見了一萬朵,
在歡舞之中起伏顛簸。
讀了華茲華斯如赤子一般贊美自然的詩,你會很容易忽略他曾經是因為仕途失意才回湖區定居的,也會忘記在那個時代,機器早已轟鳴高歌,工廠煙囪冒著黑煙,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烏煙瘴氣、臭氣沖天。甚至,你根本看不到一個陰霾密布的冬季湖區,仿佛這里只有人間四月天。
你不得不開始懷疑詩人的可靠性。
畢竟,那時的英國鄉村已不再是杰弗雷·喬叟時代的純凈之地,說不定滿是炭灰的大霧也彌散在湖區的上空,太陽穿上白色的紗裙,由于“圈地運動”而無地可耕的農民正黯然神傷……可這些絕不會出現在湖畔詩人的作品中。在他們優美的遣詞造句里,既沒有工業革命的影子,也看不到勃朗特三姐妹筆下的沼澤和陡峭的山崖,也看不到像碧雅翠絲·波特小姐那樣在農場勞作的景象。
未被污染包圍的喬叟,并沒有寫出一個純美可愛的鄉村。而華茲華斯好似對真實的世界閉上了眼睛,全然沉浸在自己家湖邊的“鴿舍”。我去參觀“鴿舍”的時候,看到了他生前使用的寢具用品,他可真算不上是闊綽的鄉紳。可能是經濟并不寬裕,買房子的錢也是靠人接濟,另外,他可能也并不熱衷于奢侈的生活方式,欣賞一朵花的綻放勝過幾件豪華家具帶來的滿足。
華茲華斯對自然的崇拜帶著一種病態的成分,我因此讀出了另外一種心酸,那就是把自然歌頌得越是絕美,他的現實生活越是不盡人意,對自己的人生越是失控。那些詩正是他的避難所,幫他回避了真實人生中的暴風雨和殘酷。
但毋庸置疑,大自然讓這些湖畔詩人很快樂,連呼吸到的空氣都充滿自由。比起一些把眾生的因果背負在自己身上的知識分子,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和雪萊等人則用詩把人們引入他們心中的烏托邦,避世的詩句藏在胸口,宛如一道道護身符。
華茲華斯堅定地認為:“所有的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寧靜中積累起來的情感。”自然滋養和激發了詩人,他的詩作又讓更多人看到自然的魅力,延綿的山巒、整齊的田莊、清澈的小溪、蔚藍的湖水和散布其中的裊裊炊煙。
在華茲華斯的自然觀中,自然是神性、理性和人性的結合,兒童是成人重返自然的中介,自然是拯救人類社會的良藥。
他曾提出過這種前所未見的觀點:人生最好的年華都是受大自然影響的結果。大城市里擁擠不堪以及不人道的生活方式有害人性,而回歸自然則是拯救人類的最好方式。
兩百年后,華茲華斯的論斷依然有先見之明,即便我們已處在如此繁華便利的城市,卻并沒有比那時候的人們感到更幸福。因為,他早就發現了,“從大自然里獲得歡樂,乃是人們保持和增長永恒快樂的秘訣”。
三
英國的鄉村,以某種特有的氣質,表現著這個國家的高貴和永恒。一些世襲貴族的子女,其童年幾乎都在自家的鄉間大莊園或古堡里度過。
以女王為代表的溫莎家族就是典型的英格蘭鄉村貴族。英國記者帕克斯曼說:“真正的英國人就是鄉下人,這話一點兒不假,越是有錢有勢,越是受過傳統教育的英國人,越會以此為榮。”
城市化進程中,人們曾一度更愿意留在城市,城市的物質生活代表著文明和財富。也有例外,那就是出生在倫敦肯辛頓區的富家女—碧雅翠絲·波特小姐。16歲,波特小姐跟隨家人度假來到英格蘭北部的Near Sawrey村,從Wray城堡走到了溫德米爾湖畔,被湖區綺麗的風景吸引,之后10年,他們一家常常在夏天來此度假。
波特小姐一心想當農婦,而不是父母期盼的上流社會淑女。最終她如愿以償,掙脫牢籠,定居到湖區。
要說湖區人心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曾打跑豪豬的壯士,也不是湖畔詩人,正是這位種地養花、照顧豬羊雞鴨、清理水溝、翻修房屋的童話作家。39歲時,她用稿費買下第一套房產—丘頂農場,原本嬌生慣養的城市小姐竟成了種田能手、牧業專家。

除了彼得兔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波特小姐和自己的牧羊人一起,培育了在湖區瀕臨滅絕的黑德威克羊,她還當選為黑德威克羊培育員協會的會長,成為一位自然科學家、環保主義者。她還寫過一篇關于真菌繁殖的論文,并向當時英國生物分類學的最高研究機構倫敦林奈協會遞交,最后因為性別原因遭到粗暴拒絕。當青霉素的發現震驚世界時,人們才對當年粗暴拒絕她在這一領域的原創貢獻感到慚愧。
高尚的情操并非只體現在作品里。波特小姐把所有出版收入用來購買田產,致力于維護傳統的農耕技術和手工藝。去世的時候,她留下了4000英畝的田產,包括15個農場、房產和許多景色優美的地區,并將其全部捐給全國基金會,以保護英國的自然景觀和人文建筑。
四
在湖區住上幾日,大致你也會有所體會,鄉村生活為何會成為英國人終生的向往。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寫道:“鄉間是英國人的天然感情得以真正發揮的廣闊天地。在鄉村,他們心甘情愿地從城市的一切拘謹和客套之中擺脫出來,一反其平日沉默的習慣,變得歡欣舒暢。”
比起城市,鄉村確實是道德更高尚的殿堂,教化人們親近泥土,凈化人們如溫德米爾湖一樣純凈,不分偉大還是渺小。可想而知,這些郁郁寡歡的文人們紛紛投身于廣袤的鄉野,仿佛那里才是自己高尚情操的安放地。
可惜在湖區住了5天,我就開始按捺不住,滿心想要重返倫敦西區的劇院,想要潛入熱鬧非凡的考文特花園,想要走到攝政街的街角喝咖啡了。原來,只有書、木屋、花草為伴的生活也挺寂寞的,我一邊收拾行李返城,一邊遺憾于自己的凡心不能徹底適應與世隔絕的生活。驚喜的是,我意外發現自己的胸口也被貼上了一張美好情操的護身符,那應該是在林間散步時、給南瓜澆水施肥時、在讀華茲華斯的詩歌時得到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