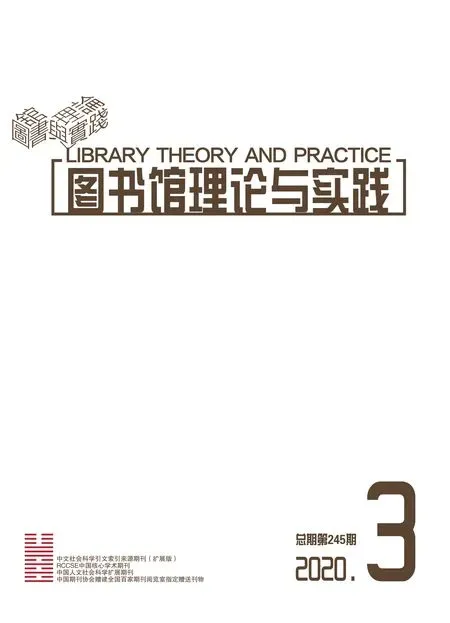厘禮正俗:晚唐李涪《刊誤》考
吳凌杰(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區域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所)
《刊誤》,晚唐李涪所撰,是一部偏重于記述唐人禮制、習俗的筆記小說,保存了大量晚唐時期社會習俗習慣的資料,為歷來史家所重視并將其收錄于各類書目之中,但其內容較少,因此目前學界對之關注較為不夠。①文章試從《刊誤》作者的生平事跡、版本以及史料價值3個方面略作探討,意在厘清此書的學術價值,尚有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刊誤》作者生平事跡考
李涪具體生卒年月失考,兩《唐書》均無記載,其為李唐宗室后裔,至于其出于何房,目前學界有所爭議。②筆者不揣淺陋,認為《刊誤》之作者李涪出于鄭王房,詳論如下。
首據《舊唐書·李石傳》云:李石子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石弟福,字之……僖宗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1]4483-4484又據《北夢瑣言》卷六云: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一作“泊”。[2]45又同書卷九云: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一作“不”。為小文,好著述……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2]72-73再據勞格《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十五云:李涪,新表蔡王房……又大鄭王房:太子太傅福(見戶中)。子涪。不詳歷官。[3]739
由此四條可知李石為李福兄長,而李福為李涪與李航兄弟二人的父親,那么李涪是否出自于鄭王房呢?這就必須知道李石出自何房。據《新唐書·李石傳》云:“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4]5439此段明言李石出自李神符一脈,那么李神符出自何房呢?據《舊唐書·李神通傳》云:“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1]2340又同卷《李神符傳》云:“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孝悌聞。”[1]2344蓋李神通與李神符二人為親兄弟之關系,其父是被封為鄭王之李亮,可知李石確實出自于鄭王房,從而李涪出自于鄭王房明矣!
因此《刊誤》作者之李涪,其家庭來歷頗為清晰:其兄弟為李航,曾任監察使;其父為李福,曾任僖宗朝宰相;其伯父為李石,則歷任文、武兩朝之高官;其祖上出自鄭王李亮一脈,正是擁有如此顯赫之家室背景與才學淵源,才能使得李涪作此《刊誤》一書。至于黃永年于《唐史史料學》一書中指出的《新唐書》所寫蔡王房的“李涪”,蓋黃氏見于勞格《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有所提及,筆者囿于史料之缺乏,尚不知其來歷與生平,但值得措意的是,黃氏所引《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一書,其記載的蔡王房“李涪”之事,其史源可能源于《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所記載的蔡王房之“李涪”,極有可能是歐氏修史訛誤了名字相近之人物、姓名、關系,因而將一人誤作為兩人,分別注入世系表內。此說僅供參考,不敢引為定論。③
但鄭王一脈之李涪,確為《刊誤》之作者,而他自身官職經歷不見于現存史書,唯有《全唐文》卷七六四《刊誤·序》小傳對簡要提及:“(李涪)昭宗時歷官金部郎中、河南少尹、國子祭酒、詹事府丞。”[5]7945《唐故御史中臣汀州刺史孫公墓志并序》墓志中也有關于李涪官職之記載,該墓志落款云“朝散大夫前守河南縣令柱國李涪書”,[6]可知李涪確實在河南任職較久,與《全唐文》小傳記載相吻合。由此可一窺其官職,同時在《文苑英華》中,還保留有皇帝委任李涪為國子祭酒的詔書,文云:“敕。右武以來,國子失教……具官李涪,以爾受爵素高,去朝斯久。奉車親重,乃以太仆命之。宗籍宿儒,時謂非稱。擢居雅秩,幸得其人。以爾蘊學之優,當吾選求之要。勉來分職,昭我用才。可依前件。”[7]2032而后,李涪因唐末混戰,避亂于梁州等地。即書云:“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2]45雖然其出身高貴,官至高位,但結局頗為凄涼。《新唐書·叛臣傳》云:“始,(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4]6406
由此可知,李涪因替王行瑜開脫獲罪,流放并死于嶺南,而其為何替王行瑜進言辯解,由于正史缺載,現已無從得知。總之,李涪仕途起伏皆與唐末喪亂大背景密不可分,而他仕途之升降除了與其擁有雄厚家世背景外,更與才學不無關系。史書云因其博學多識擁有“周禮庫”之美譽: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一作“不”。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咨稟之,時人號為“周禮庫”,蓋籍于舊典也。[1]72-73
除了自身博學多識外,他的才學還體現在與當時文人唱和上,在他辭官歸鄉之時好友薛能贈詩一首以表慶賀,其詩全文名為《送李涪廵官歸永樂舊居》,現收入于《文苑英華》之中。[7]1430李涪的書法造詣也頗為深厚,如前所述之墓志,便是李涪親手書寫而成。
總而言之,從李涪個人生平可知,他不僅出身皇室、位至高官,更精通禮學書法,這為他撰寫《刊誤》一書打下深厚基礎。
二、《刊誤》版本流傳考
李涪于《刊誤》開篇指明五十篇,而今存世為四十九篇,蓋傳世過程中散佚一則,現存《刊誤》一書分為一卷本與兩卷本,筆者將翻閱歷代史書所存兩者所收入書目制成下列兩表。

表1 歷代書目中一卷本《刊誤》之版本

表2 歷代書目中二卷本《刊誤》之版本
由表1、2可知,最早書目中載有《刊誤》之書為宋代歐氏所修《新唐書·藝文志》。而在唐五代,無論是官修《舊唐書·經籍志》,還是私人所修書目均缺載。筆者推斷蓋五代戰亂頻發,時人無法盡獲全本,至宋初時,國政安和,故尋得此書。《刊誤》一書,在宋以前為二卷本,到了宋及以后大體出于流傳方便與內容不多等原因,后世將兩卷本合為一卷本,因而一卷本與二卷本皆有流傳。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卷本與二卷本僅為卷數分合之別,其內容并無刪減,皆為四十九篇。
現存《刊誤》有一二卷本之別,因而版本各自有差,筆者特成兩表以明晰之。

表3 現存一卷本《刊誤》版本

表4 現存二卷本《刊誤》版本
由表3、4可知,《說郛》一書版本較為復雜,在流傳過程中書名也有不同,且部分版本已亡佚,筆者經過比對部分現存版本,現將說明如下。
1.《二都不并建》篇中“……旋為巨寇焚爇廟室悉成煨燼……”。《四庫全書》《百川學海》本為“盡”;而《說郛(宛委山堂)》本、《古今逸史》本為“燼”。
2.《都都統》篇中“……武將莫不望風愿受其畫……”。《四庫全書》本為“指畫”;而《說郛(宛委山堂)》本、《百川學海》本、《古今逸史》本為“畫”。
3.《上事拜廳》篇中“……余乃詰之曰曷拜……”。《四庫全書》本、《古今逸史》本、《說郛(宛委山堂)》本皆為“曷再拜”;而《百川學海》本為“曷拜”。
4.《婦謁姑不宜表以絹囊》篇中:“投刺始于雋不疑……”。《百川學海》本、《古今逸史》本、《說郛(宛委山堂)》本皆為“儁”;而《四庫全書》本為“雋”。
5.《樂論》篇中:“……《記》不云乎……”。《古今逸史》本、《說郛(宛委山堂)》本為“《詩》”;而《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為“《記》”。
6.《奉陵》篇中:“……此無視父母所愛……”。《四庫全書》本為“皆”;而《古今逸史》本、《百川學海》本、《說郛(宛委山堂)》本為“此”。
7.《宰相宰相合與百官抗禮》篇中:“……然與九品抗禮古今謂會昌已前……”。《說郛(宛委山堂)》本為“古之謂”;而《四庫全書》本、《百川學海》本、《古今逸史》本皆為“古今謂”。
8.《切韻》篇中:“……游夏侯詠撰……”。《說郛(宛委山堂)》本為“遊”;《百川學海》本、《古今逸史》本為“游”;而《四庫全書》本無此字。
9.《切韻》篇中:“……又以恐字若字俱去聲……”。《百川學海》本、《說郛(宛委山堂)》本、為“若”;而《四庫全書》本、《古今逸史》本為“苦”。
由上可知,雖然《刊誤》一書版本繁多,但是由于其內容較少等原因,流傳之中不同版本之間的差距較小,僅在文字表述以及脫字等處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引述之文獻,皆采據三秦出版社《全唐五代筆記》所收錄的陶敏標注《刊誤》二卷本,其文前自有序。
三、《刊誤》史料價值考
在歷代書目中皆將《刊誤》列入子部小說家類,作為一部筆記小說集,正如李涪在自序中所言:余嘗于學古問政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或未造其理,則病之于心……而沿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十篇,號曰《刊誤》。雖欲自申專志,亦如路瑟,以掇其譏也。[8]2575
李涪作為晚唐時期的禮學大家,擁有“周禮庫”之美譽,在面對晚唐時期習俗敗壞之風,他撰成此書意圖在于澄清風化以示后人,筆者據《刊誤》內容,將所存四十九篇引出,據其內在相關性,重新排列,大體形成五類,并與唐人文集相應對,發現其獨特價值。
(一)吉禮類
吉禮類有《鵝》《拜客》《拜四》《婦謁姑不宜表以絹囊》四篇,這類篇幅中多列舉晚唐當時婚禮時與先前禮制發生的若干變化,進而提醒世人需重視傳統婚禮之俗。此四篇從用奠之禮、來賓之禮、拜姑舅之禮以及新婦面謁婆婆時的注意事項作出了規勸與諷刺,進一步以《周禮》等文獻相參照,可補現今學界對晚唐吉禮史料之闕。
(二)兇禮類
兇禮類有《吊者跪》《舅姑服》《仗周議》三篇,在此三篇中多論述晚唐喪禮中出現的違禮現象。在《吊者跪》篇,他對喪禮時吊客對主人家只行拜禮不行跪禮之事進行了批判,并從官職品階出發,認為在傳統喪禮秩序中低位官須向高位官行跪禮。在《舅姑服》篇,他指出媳為舅姑喪服三年之事進行反駁,認為按《開元禮》并參詳周禮,媳為舅姑齊衰乃是正確之道,而因《開元禮》藏于官府,使得時人未能盡知,造成禮制錯訛不斷,進而向政府提出將禮法條文公布于天下的建議。在《杖周議》篇,他指出當時兄弟喪禮時,為兄弟服仗周禮有違禮制,并闡述了杖周禮的適用范圍。從此三篇兇類可知,李涪考釋了晚唐時人在喪葬禮的做法之錯誤性,進而以澄清當時教化。
(三)官禮類
如前所述,李涪本為李氏宗室而后屢被升遷位至高官,因而對于官吏名稱之設置以及官吏內部所用之禮也頗為精深,因此在官禮類有《禮儀使》《開府儀同三司》《副大使》《都都統》《侍中仆射官號》《京尹不合避御史》《封爵》《宰相合與百官抗禮》《進獻奇零》《宰相不合受節察防御團練等使櫜鞬拜禮》《上事拜廳》《壓角》《祭節拜戟》等十三篇,筆者根據其內容進一步細分為官職設置類與官員禮制類。
1.官職設置。在官職設置中,李涪考釋唐代某些官職的不合禮性,如,在《禮儀使》篇中便指出唐代所設立的“禮儀使”一職不合古之禮法,并指出其職原來已久,先前歷代皆有官號為郎中、員外等人掌管禮儀,而唐代卻專設“禮儀使”之職,以“使”來掌握國家禮儀,此行為乃是累贅之事。在《開府儀同三司》篇中認為古代以三公為階,而唐代以開府儀同三司為階,實足以羞。同樣在《副大使》《都都統》《侍中仆射官號》三篇中指出副大使、都都統、侍中仆射官職設立的不當之處,進一步認為這些官號來歷非正,理該停止。
2.官員禮制。在官員禮制中李涪則考釋了當時官員內部禮制典范,如,在《京尹不合避御史》篇認為京尹作為朝廷重臣,握有保衛京城安危之責,而御史也作為高官有糾察百官得失之職,不可以私自受到拜見。兩者同屬重臣之列,因此,京尹于道逢御史不可為之避讓。在《宰相合與百官抗禮》《宰相不合受節察防御團練等使櫜鞬拜禮》《壓角》三篇中集中論述了宰相與其他官員相處時的禮儀制度。在《進獻奇零》《祭節拜戟》兩篇中集中論述了君臣之禮,臣子給君父上供之錢財應用整數、拜皇帝之賞賜應該叩謝皇帝本人等禮節。在《封爵》《上事拜廳》兩篇中集中論述當時官員禮儀知識的弱化現象。由此十三篇可知,李涪深諳官場禮儀,能引經據典的論述官職之設立與官員禮儀之由來,同時也可以看出晚唐時期因吏治不清,加之戰亂頻發,致使當時官員都無法明晰自身之禮法,因此,此部分可為研究晚唐官場提供新的史料。
總而言之,無論是吉禮、兇禮還是官禮,李涪對此都深有研究,他不僅論述唐代社會對于禮制遵守情況,更追根溯源地寫出了禮制對某種現象規定之沿革以及人們之所以不遵守禮制規定之緣由。由此觀之,《刊誤》一書在禮儀記錄上確有補如今唐禮不足之特點。
(四)習俗類
李涪對于當時習俗也頗有研究,面對當時之習俗與傳統習俗之別進行了探究,作成《二都不并建》《短啓短疏》《九寺皆為棘卿》《客卿》《參謀》《臘日非節》《奉陵》《起居》《春秋仲月不合擊樹》《出土牛》《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祭物先》十二篇。習俗在不同群體中表現各不相同,從國家層面而言,習俗多表現為禮俗,即統治者用禮法的形式對習俗進行嚴格的規定,因而此類習俗帶有禮法的色彩,對于統治者而言具有一定的約束性,因此筆者稱之為禮俗;從民間而言,習俗多為人們時代口耳相傳之產物,主要依靠人們的自覺遵守與家族約束才得以流行,較之國家禮俗而言具有隨意性與多樣性。
1.國家禮俗。國家禮俗類即從整個國家角度去分析,找到唐代與前代禮俗之異。如《二都不并建》《短啟短疏》《九寺皆為棘卿》《春秋仲月不合擊樹》《出土牛》五篇皆從國家層次出發論述唐代之與前代禮俗之別。《二都不并建》篇中指出唐代建立長安、洛陽二都不合傳統習俗禮制,從“國無二主”“天無二日”的角度指出一個國家只能擁有一座都城,洛陽之修建起于高宗,出于游樂之用,而武氏后改為都城,致使二都并立,此詭吊之事應當改正。《短啟短疏》篇中認為短啟短疏之習起于晉宋之代,蓋戰亂頻發之緣故,而唐代國泰民安,因而革除此制。在《九寺皆為棘卿》篇中指出大理寺自稱為棘卿不合古代禮俗,古人皆言三公九卿都是棘卿。在《春秋仲月不合擊樹》篇中指出皇帝在掃墓時選任官員擊樹之習,不符合《開元禮》提出的春秋仲月遣三公掃除枯朽枝葉之禮,并發出了“其為不經,又何甚也!”[8]2577的感嘆。在《出土牛》篇中指出當時州縣立土牛的行為不合古之習俗。[8]2579
2.民間風俗。民間風俗類即從當時唐人自身的風俗出發,找到前人與今人在傳統風俗之異。如,《客卿》《參謀》《臘日非節》《奉陵》《起居》《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祭物先》《火》八篇皆從當時唐人角度出發論述唐代民間與前代風俗之別。《客卿》篇中指出古代的客卿是才學宏達的儒生,而當時藩鎮招納的儒生,并不是為帝王開創霸業之人,因此民間對藩鎮所招納的儒生輒號為客卿有著明顯的錯誤。在《參謀》篇中指出藩鎮雖然選用參謀,但給與其職位低微,不合傳統參謀位高權重之禮。在《臘日非節》篇中指出節日乃是五行運轉而非春夏秋冬四時之產物,當時人制作物品必集中于臘月之臘日是不必要之行為。在《奉陵》篇中指出以前為帝王奉陵之人皆為性格良善之兒孫,而今奉陵內官多為罪罰之人,此制有悖孝道。在《起居》篇中指出“起居”本意為下屬拜見達官顯貴時等候其面見的過程,而如今卻將其濫用,連常人等候面見普通官員皆稱之為“起居”。在《祭物先》篇中指出古之祭祀便以祭物為先,但時間推移,情隨事遷,受佛教之影響,祭祀多祭佛,而不祭物。因此他號召士子儒人,宜遵典教。在《火》篇中李涪從“鉆燧改火”這一詞語出發,考證了當時季春禁火來源于《論語》,而非介子推之事,只是年代弭久,時人皆誤解其風俗之來源罷了。[8]2581在《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篇中針對當時官員于家中立私廟向朝廷奏請之事提出批評,并指出官員立私廟是寄托個人哀思之情,因此并不需向朝廷奏請。原來之所以向朝廷奏請是立廟之地不在家中,而在他處。隨著時間之推移,現在人皆以為只有官達某階才可立私廟。
由上十二篇可知,晚唐時期社會風氣日衰,當時人們對于傳統習俗不甚明確,在生活中做出了種種不合習俗之事,而李涪卻對此甚為明了,并將其一一列出,并辨析傳統習俗之做法及緣由。同時在現存有關唐代風俗之史料中,有范攄《云溪友議》、段成式《酉陽雜俎》、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封演《封氏聞見錄》等筆記小說,此類多論及中晚唐時期習俗軼事,而《刊誤》一書則進一步豐富了唐代特別是晚唐習俗之史料。
(五)文字、歷法、音韻類
李涪除了精于習俗之外,對于文字、歷法、音韻也頗有造詣,《昭穆》、《洛隨》、《僅甥傍繆廄薦》、《切韻》、《繕完葺墻》、《樂論》、《佳禮》、《七曜歷》八篇皆是其考證文字、歷法、音韻功底之體現。
1.文字考證。在文字考證中,李涪借考證文字,深究古字之流變,其體現在《昭穆》《洛隨》《僅甥傍繆廄薦》《佳禮》《繕完葺墻》篇中,在《昭穆》篇李涪指出昭穆一詞由來已久,只因晉朝避諱之故改為韶穆,在本朝應重新改為昭穆。在《洛隨》篇指出“洛陽(陽)”一詞的流變,從洛陽(陽)到隨朝等字的變化,皆因隋文帝厭惡“隨”字,而改“隨”為“隋”,除去“走”字,本朝則應要改回“洛隨”以正視聽。[8]2585在《佳禮》篇中指出“佳”與“嘉”字之別,嘉禮屬五禮之一,因而婚嫁之時皆為嘉禮,而當時人們多稱婚姻為“佳期”是錯訛的。在《繕完葺墻》篇中考釋了《左傳》“繕完葺墻”一詞之來由,并疑此詞乃是《左傳》字誤,致使后世禮節繁瑣。在《僅甥傍繆廄薦》指出當時人們對于“僅甥傍繆廄薦”等字錯誤使用,蓋時人不懂字體變化之源流以致錯誤百出。
2.歷法、音韻。除文字考釋外,李涪對于日歷音韻也頗有研究,在《七曜歷》中則體現出他對歷法也有專研,在此文中他諷刺賈躭所撰《日月五星行歷》差誤較多,且撰寫過于隨意,面對他人曲解之言卻妄信。在《樂論》篇指出音樂非能亡國,亡國者乃為政得失。在《切韻》篇中對陸法言所著《切韻》一書提出了批評,并用《小雅》《詩經》《國風》等書論證陸法言所著《切韻》一書對音韻撰寫之偏差,雖其觀點后世學者可否不一,但卻留存有關唐代語言研究之史料,這為研究隋唐語言之演變提供了證據。[9]397由上八篇可知李涪對于文字、歷法、音韻皆有造詣,故可補現存唐代史料中關于文字、歷法、音韻之闕。
(六)個人觀點類
《刊誤》作為一部筆記小說,李涪除了論證禮法、文字、音韻等方面之流變外,也記錄了他個人讀書之觀點,以及對生活之體會。在《廄焚》《釋怪》《論醫》《曾參不列四科》《祈雨》《發救兵》《非驗》《座主當門生拜禮》八篇分別論述了他讀書之體會與生活之感悟。
李涪在讀書時針對時人所誤皆做出了詳細解釋,如在《廄焚》中指出當時一些人以為孔子在廄焚時,問馬安全否后又問人安全否是不值得記述。[8]2587在《釋怪》篇中指出李商隱認為老子師于竺干為無稽之談。[8]2584在《曾參不列四科》篇中指出曾子之所以明言被列入孔門四科,并非孔子不重孝道,只是無法盡舉科目而已。[8]2579
李涪對生活的感悟也見于此書,如在《論醫》篇中認為醫生年輕好財且記憶好,讓醫術較高明,而老后志怠心慢,記憶衰退,使得醫術不行。在《祈雨》篇中認為祈雨不應該遵照吉日之法。在《發救兵》篇中指出戰爭瞬息萬變,將領選擇吉日發救兵就來不及了。在《非驗》篇中指出城陽公主與駙馬一起死并不是卜驗的結果。而對當時社會中科場上門生座主禮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座主當門生拜禮》篇中認為科舉之門生,受官來自于朝廷而非座主,而當時門生拜座主之風盛行,相互攀親戚現象較多,此類現象無疑會敗壞官場之威嚴。由上八篇可以看出李涪對于讀書與社會之感悟也盡載于書中,這為研究晚唐的人物研究提供了珍貴之史料。
綜上所述,現存李涪著《刊誤》雖四十九篇,但卻為唐史研究保留下來大量珍貴史料,這些材料包含了當時的禮制、習俗以及文字、歷法、音韻。通過對這些材料的分析可更為明晰地看到晚唐社會風氣之變化,以及此種變化在社會各個方面的反映。
四、結語
歸納全文,李涪為李唐皇室之宗親,出自鄭王一脈,其伯父為李石,憲宗年官居宰相,其父親為李福,僖宗年官至宰相,兄弟李航,官至監察使,從中可以看出李涪的家勢頗為顯赫,這種顯赫的家勢讓他的仕途升遷頗為順利,歷任金部郎中、河南少尹、國子祭酒、詹事府丞。顯赫的家境使他自幼便接受到優良教育,因而李涪精于禮制,并擁有“周禮庫”之美譽。博學多識的他,與當時文人多有詩歌交往。晚唐亂起,李涪流離輾轉多地居住,他日益感受到風氣沉淪之弊,深感其矯正匡失、厘禮正俗之責,遂著成《刊誤》一書以敦化之。《刊誤》原為二卷本,由于內容較少之緣故,流傳至宋時合為一卷,以后二者皆有流傳。雖然在流傳時,書名屢易、版本繁多,但經筆者考訂,各版本僅在文字等方面有著細微之別,而內容大體無差。原書本為五十篇,流傳過程中逸去一篇,現存為四十九篇,為后世史家著錄于子部小說家類,見于各類書目之中。其書在偏重于記述唐代禮制、習俗的同時,也為后世提供了大量有關唐代社會文化之材料,故頗受歷代史家重視,流播久遠。筆者認為:作為一部唐人筆記小說集,《刊誤》具有史源近真、補史之闕、反映現實等特點,但目前學界對此書重視尚為薄弱,現著成此文且備一說。
[注釋]
① 據筆者所見,目前學界專題性對《刊誤》研究的期刊論文則尚未發現,而涉及《刊誤》的學位論文有畢彩霞:《〈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小說集解》(華中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李儼峰:《宛委山堂本〈說郛〉所存若干稀見唐人筆記之考釋》(上海師范大學2019年碩士論文)。
② 學界對李涪出于鄭王房或蔡王房有爭議,陳寅恪、黃永年皆提出不同看法,具體參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M].北京:三聯書店,2015:407;黃永年.唐史史料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5:166。③ 有關歐陽修在禮書中的錯訛事例,可參見吳凌杰:《唐代帝王喪葬禮制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論文第五章第三節),并見:吳凌杰,洪家琪.國恤:唐代帝王喪葬禮制研究的回顧與反思[J].天中學刊.2019(6):1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