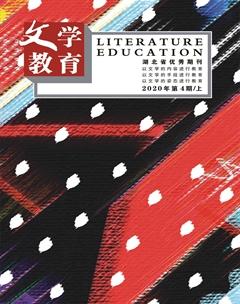《浮生九記》寫作的三個向度
朱永明 張德萍
內容摘要:《浮生九記》是王小忠2019年出版的非虛構紀實散文集,其敘述手法與小說有著一脈傳承的關系。因此不少作家將其列入短篇系列小說集。避開文體不談,這部紀實散文集集中抒寫了當代農村勞力的逃離問題、農村及小城鎮的人心、人道、人論問題,以及農村教育現狀等諸多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可以說這是披露問題的“問題散文集”,其具有現實性和當下性。
關鍵詞:鄉土 文明 禮俗 人倫
《浮生九記》出版后,就被很多人堪稱為是非虛構作品。是的,我們在討論這部作品集時,也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部作品集到底有沒有虛構?其實,在文學創作手法多樣化的今天,虛構與非虛構并不重要了,關鍵是要寫出生活的真實,指出生活的病苦,以引起更好的療救。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浮生九記》無疑是對農牧結合地道德倫理、記憶與現實的扭結、自然的關懷與擔憂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是值得研究的。
一.鄉土蛻變與文明禮俗的破敗
《浮生九記》最大的特點其實還是它的紀實性。《浮生九記》關注的是當代底層人的生活變遷,堅持了文學與人道的創作立場,從人倫道德、個人思想方面對所謂“軸心時代”的當下社會給予了強烈的回應和關照。
《浮生九記》中的“浮生”是作者建構的“后鄉土時代”的物象群。這些人大多是被現代世俗觀念異化了,他們的身上體現出了后鄉土時代的生活裂變與知識分子尋找精神家園的焦慮與迷茫。通部作品中,作家站在土地這個“根”的文化坐標中,審視鄉村的新變化,從中表現出了作者鄉村經驗的書寫和人性關懷。這個集子總共包括九篇文章,每一篇中敘述者都是站在“當代性”這樣的一個節點上去發現問題、反映時弊。正如他所說:“這是我年輕生命對這土地的理解”[1]。
新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社會呈現出的深刻性與復雜性,《兄弟記》中可見一斑。《兄弟記》中作者以家作為敘述空間,以“我”作為講述視角來展開。從“空間詩學”來解讀這個長篇作品時,可以看出,“家”在這里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家庭,而是洞察新型鄉土社會的一面鏡子。費孝通在《鄉土中國生育制度》一書中說:“血緣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世代人口的繁殖,像一個根上長出的樹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說是血緣上親疏的一種反映。”[2]從后鄉土時代的農村現狀而言,血緣只是漸行漸遠地維持著一個家族的名分,成為倫理道德上的必須。地緣的概念和地域的情分完全被利益所異化,攀比、排擠,對金錢的占有等欲望已經魔隨心生了。血緣關系、地緣社群的觀念已經被徹底踐踏,大批青年人擠進城市的現象讓農村直接衰竭。空巢鄉村、空巢家庭、空巢老人,已經成為后鄉土時代農村捉襟見肘的事實。
養老問題以及耕地的不斷縮減,家庭矛盾復雜化程度的加深,農耕為生計變成以經濟為主導的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及土地的荒蕪、知識分子精神家園的喪失已經成為當今最緊張話題。丟失土地,就意味著喪失了農耕文明,意味著人與土地的距離在不斷疏遠,這也是新世紀農村呈現出的新問題。在“后鄉村”人的思想中,土地給不了他們什么,他們只能棄之。這其中也免不了城市生活對他們的強大吸引。盲目地奔向城市、爭當老板、帶頭致富成為新型鄉村人的時尚和追求,這種超前的“理想”,打破了農村原有的生活秩序,破壞了以血緣、地緣為情系的詩意鄉村。誠然,《兄弟記》就是立足于這樣一個嚴肅的話題,思考著鄉村的當代變局。
《兄弟記》中的敘事人“我”就是一個以農村人最理想的方式脫離了土地,這是農村人觀念的轉變,更是理想的選擇。這些微不足道的進步與傳統美德已經無法拯救一個亂序版的鄉村。拐騙婦女,觸犯法律都成為農村常有的事,背饃走親被大吃二喝的團拜風氣取代、虔誠的守喪禮俗被喝酒打牌的惡習踐踏。美好的人情變成了金錢交易。家庭利益的分爭,娶親的高彩禮讓人望洋興嘆。我們可以看出農村這塊精神家園對農村知識分子來說已經成為生命中的彼岸世界,難以回去。“更為奇怪的是在日益變化著的社會環境里,更多地鄉村人似乎找不到謀生的方向,也無法找到自我。”[3]從《兄弟記》中,我們看到“我”在彼岸世界里深感茫然,而此岸世界給不了“我”任何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說《兄弟記》是直擊當下鄉村真實生活的寓言,呈現出極強的憂患意識。
二.自然之道與人倫之道的言說
作為一個有寫作激情的作者來說,每一次漫游并不是散心、郊游和消遣,而是一次寫作靈感的獲取與寫作經驗的匯總。《漫游記》中作者發現草原生存者“以商輔牧”的生存方式轉變,這個轉變從根本意義上說是社會發展與時代的進步,是傳統意義上以游牧業為主生活方式的消解。如果說鄉村放棄堅守田地,讓鄉村自覺亂序。那么草原的裂變更是外界的入侵所致,他們受到草原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吸引和誘惑,受到世俗欲望的促使,把目標瞄準草原凈土。奇珍資源、名貴藥材等的索取,使草原漸漸地被掏空,從而喪失了傳統的游牧文明和富于經驗的生存方式。《漫游記》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漫游,它突顯了另一個寧靜之地在新時代的裂變——如何保護草原,回到傳統,追求人與自然詩意的棲居,這才是《漫游記》的深刻思考。
《做珠記》表現的是農村人的經商史,其中也不乏關于佛道、人道、自然之道的探索。我們可以從“物性詩學”的理論來探討這一個篇章。張進說過:“‘物不是由于被話語反映而被人讀懂,而是因為物已經安置在人類的精神之中,成為一種‘物話語這種話語本身有物質性。”[4]后工業革命時代是一個物質極其富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生活的我們,卻感覺到無法說清的焦慮和迷茫,孤獨寂寞的心驅使我們更注重人身心的修養,因此對佛珠的喜好又成為人對精神生活的另一種追求。作者對“佛珠”這一“弘法之器”進行進行了概括:“靜慮離安念,持珠當心上。”因此對佛珠的喜好,又成為人對生命追求的另一種境界,從玩佛珠到販佛珠再到做佛珠,人們又開始探索生活之雅趣、人生之道統,這種道是通過觀察而感知的。《做珠記》中作者以“觀珠”作為時間線索推進、并不斷地轉換敘述視角,陳述珠所蘊含的“物道”與人道。
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解釋這“觀”:謂學詩可以論詩事也……世治之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宋代大理學家邵雍的論述最為深刻:夫所以謂之,以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皇極徑世·觀物,而是通過觀物而觀道。)從人們對佛珠的喜好而言,佛珠區分了木頭與木頭之間的高低貴賤,在提升人對生活雅致的同時,更加輻射到了人心的奸詐與虛偽,從念佛的層面看,佛珠代表了人對信仰的堅守,是虔誠之心的表征之物。“拿起佛珠,就告誡自己心念純潔,一心貫徹于善念之中,久而久之明心見性。心開意解是故持珠善念大抵如此。”[5]。在五花八門的佛珠市場,包含著復雜的人性,求珠、念善本身是“仁義”的體現。但是在金錢欲望的促使之下,變成了交易。作者先是從魏文海的販珠中觀察到了人情之道,接著又從河沿路做珠攤上見到了佛珠之道,“自己以為好的,自然就是好貨了”這便是人心之道,生活之道、自信之道、自我人格之道。這是“心觀”的結果,這也就是宋代理學家邵雍所說: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這里說的“性”是事物的本性。以物觀物,即是從物本身的情狀認識物,這種觀物,相對來說是便客觀的。它能見出事物的本性。作者在沿河路的攤點上觀察到的金絲楠木,小葉紫檀、黃花梨、烏木等等,這是以物觀物,見證了佛珠的高低貴賤之分。而老頭所說的“人心所向”由是以我觀物的結果。“以我觀物”情也,這便有了人心所向。
《做珠記》從美學層面來看,體現了人類對美的追求,這也是后鄉土時代生活富裕的披露。類似于古代所謂的“飽食思欲”。與其不同之處是對自然美的追求。對自然美追求安然落實到“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之上,這就不得不談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問題。人對不同審美情趣的滿足,卻讓自然界奇珍植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以自然生命來滿足個人的行為其實是危害人類的行為。由此看來,《做珠記》是作者對放大農村的真實寫照,并把它落實到人的行為觀念與精神追求之上。人滿足了自己的精神需求,也宣揚了人的虛偽,但這一切行為損害了自然,損害了人倫道德。這是不符合人基本的生存之“法”,這是生活理念上出現的偏差。做珠之道是對人道的發現與披露,是對新時代人欲的張揚與批判。
三.往事記憶與現實的沉思
《少年記》是一篇童年真實生活的記憶之文。我們從書寫的內容與作者成長的時代斷定,《少年記》寫的是新舊世紀交替的真實的農村生活,從作者對童年趣事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農村人對教育觀念的認知,他們對子女既抱有“望子成龍”的期盼,但又無法改變落后的教育現狀與松散的管理模式。
《堡子記》是他者口述的歷史,這篇散文中,作者以記憶和想象的方式努力還原原始時代的生存印記:堡子村是有著濃郁的農業文明的模式,通過這個村寨讀者最容易見證原始人類在與自然界斗爭中產生的智慧。在歷史發展中,落后的,舊的習俗觀念總要被新的、先進的思想和科技替代,這是新事物戰勝舊事物的必然規律,也是社會向前發展的邏輯。堡子曾經居住過樸實的鄉民,但堡子也遭遇過土匪的打劫,這里發生過的戰爭見證了原始文明之地所遭遇的野蠻重創,但也恰恰成就了堡子在民間的影響力。堡子并不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一個布局,而是一個過去歷史的考證的依據。堡子最后坍塌被無知的人們運到荒野,燒成肥料。這是現代人對文明的破壞,同時也是堡子的必然遭遇。
《浮生九記》把童年的美好與成年的迷茫呈現給我們,又把后鄉土時代年輕人生活艱難與焦慮展現給我們。它握住了“當代性”這樣一把尺子,體現了紀實散文的當代性價值。它繼承了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創作原則,關照了被主流作家筆涉較少的“鄉村”這一底層空間,也反映了農牧區人民的生存矛盾與生活困境,發揮出了文學最大的時代功用。
注 釋
[1][3][5]王小忠.浮生九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2]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張進.活態的文化與物性的詩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介紹:朱永明,文學博士,蘭州文理學院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當代藏族作家漢語文學創作;張德萍,甘肅省甘南州合作藏族中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