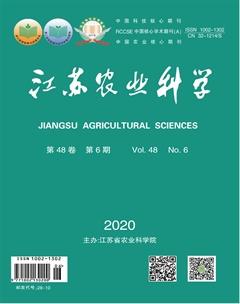基于參與者利益的農產品供應鏈可追溯推廣驅動因素
羅巒 王亞魯



摘要:如何有效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健康權益,是各國政府長期致力解決的重大問題。從國際經驗來看,實施供應鏈可追溯管理是預防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的有效途徑。推廣和使用可追溯系統需要供應鏈主體的積極參與。采用博弈論方法,從參與者利益出發,對影響參與者行為選擇的主要因素進行理論剖析。結果表明,產品價格溢價的獲得、預期安全成本和賠償機制的合理性及內部違約懲戒制度的有效性是驅動供應鏈主體參與可追溯系統的3個關鍵因素。
關鍵詞:農產品供應鏈;可追溯管理;參與者利益;博弈;賠償機制;監督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0)06-0295-05
隨著我國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的日益重視,農產品的安全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在農產品的生產、保鮮、儲藏、加工等環節,危害消費者健康安全的事件屢屢發生,造成廣大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的擔憂。建立嚴格的農產品可追溯管理制度,提高農產品質量屬性的透明性,強化農產品供應鏈各關鍵節點的質量控制,是目前各國提高產品品質、保障農產品安全的重要手段。農產品供應鏈追溯系統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可追溯系統能夠通過溯源信息識別問題源頭、召回問題產品和劃分事故責任,為消費者提供透明的向前或向后追溯的食品質量安全信息[1];其次,幫助企業在某種程度上隔離或控制問題源頭,追溯系統越精密越能更快識別產品安全或質量問題,使發現和更快響應并解決農產品安全問題成為可能[2];最后,可追溯系統還能協助消費者和政府檢查從生產到銷售的每個企業的安全責任,它的建立能激勵企業改善產品的品質,使消費者恢復對食品安全的信心[3]。如媒體曝光北京市某知名連鎖超市出售假冒有機食品,就是通過商品提供的可追溯系統進行追蹤溯源,發現農場基地有機生產存在可能造假的嫌疑。這雖然是一負面事件,但同時也表明可追溯系統的建立協助了第三方和消費者對食品安全質量的監督,也有助于政府部門對企業產品質量承諾的檢查和監管。因此,推廣實施農產品供應鏈可追溯管理對保障農產品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各國實踐來看,政府的公共強制標準與組織的私人自我約束標準是實施農產品供應鏈可追溯管理的2種重要途徑,而自愿的可追溯管理計劃來自參與主體從利益出發的主動構建,其實施成本較低,并能獲得較好的效果。本研究從參與者的利益出發,應用博弈分析方法對影響其參與意愿的因素進行分析,詮釋驅動農產品供應鏈可追溯管理實施的內在動力,對提升生產者的參與意愿,促進我國農產品供應鏈可追溯推廣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1 農產品供應鏈主體參與可追溯的利益決策博弈
整體來看,供應鏈可追溯對于食品安全狀況來說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但對于企業而言,其利潤得失才是決定其是否使用該系統的關鍵因素。上游的農場和下游的加工企業、流通企業是農產品供應鏈上的核心主體。供應鏈上所有的企業,包括農場、加工企業、運輸企業、銷售商等是否都參與該體系以及對可追溯所投入的成本、可追溯系統的寬度、精度、深度等都對食品安全系數有一定影響[4]。企業基于成本及利潤的權衡之后才能決定是否使用產品可追溯系統,各企業之間就利益問題展開博弈。假設上游企業主要由大型或小型農場組成(簡稱農場);下游企業由各類中間商組成(簡稱企業);進而對企業的行為進行分析。
首先,追溯系統的使用須要投入成本,有時甚至是高昂的成本,企業可能負擔不起。其次,消費者可能對可追溯產品了解不多或不愿為其支付更高的價格,甚至對投機性企業來說可追溯風險性高、成本大,因此許多企業不會使用。但其產品相對于其他產品來說具有安全性高的特點,因此其預期賠償成本也可能相對其他企業來說要低一些;除直接收益外還可能帶來無形收益,如產品給人們以更加值得信賴的形象。再者為了促進供應鏈可追溯系統在我國的普及與發展,政府可能給予補貼,因此有許多企業也會選擇使用。基于上述各因素對企業選擇的影響,建立模型分析。
假設1:在使用可追溯系統時消費者愿意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價格,且上下游企業的決策是單一的,不存在特殊情況。每個企業都有足夠的資金可以支付使用可追溯系統的成本。
假設2:上下游企業都不采取可追溯,農場收益為T1,企業收益為T2。農場使用農產品追溯系統的投入資金為C1,企業農產品追溯的投入資金為C2,資金主要用于開發和購買可追溯技術和設備。供應鏈的可追溯水平θ與投入資金有關,隨著供應鏈的完善,追溯水平提升不須要花費大量資金購買設備,即可追溯水平與資金投入呈指數型增長關系。設θ=12rC2[5](r為正常數)。
假設3:農場按最大的產出能力A向市場提供農產品,且假定農產品價格與可追溯水平呈正相關,消費者更愿意為高安全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設Δp=λθ,Δp為實施可追溯后產品可能增加的價格[6]。
假設4:生產每一單位可追溯產品,其成本都會增加,設農場每生產一單位農產品增加的成本為c1,企業每一單位可追溯產品增加的成本為c2。設c1、c2與C1、C2無關。
農場和企業根據自己的收益進行決策,不同決策決定了不同收益。農場和企業都可單獨作出決策且其決策不會相互影響,博弈樹見圖1。
在理論決策中,企業和農場的收益見圖1。農場或企業實行可追溯,其收益將發生變化;不使用可追溯,其收益不變。僅在收益影響決策的情況下,若T1+λ2rC21-c1A-C1≥T1,即λ2rC21-c1A-C1≥0,農場因使用可追溯而獲得更高收益,因此農場就會選擇使用;同理,當λ2rC22-c2A-C2≥0時,企業也會選擇使用;且在農場選擇使用之后會激勵企業也選擇使用,因為企業將會獲取比自己單獨使用時更大的收益T2+λ2r(C22+2C1C2)-c2A-C2,即雙方同時使用大于單獨使用時的總收益之和。但是企業使用并不會激勵農場使用,因為不管企業做什么選擇都不會影響農場收益。在雙方同時使用的情況下,供應鏈的安全性提高可能帶來較高的隱性收益,因此企業從中受益較多。龔強等認為,垂直的供應鏈結構中銷售者能夠從供應鏈可追溯中獲益,而農場和整個供應鏈的收益將會降低[7]。
因此,如何使生產源頭的農場能從可追溯管理中獲益,從而激勵其積極參與,是農產品供應鏈可追溯系統建設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綜上,當農場獲得的產品溢價超過其增加的成本時,其參與積極性將會被激發,企業同樣如此,說明合理的利潤空間是激勵供應鏈主體參與可追溯系統首要的關鍵動力因素。
2 預期安全責任成本及賠償支付
農產品生產企業可追溯合作策略選擇的概率不僅受可追溯體系建設投入成本的影響,還受建立后獲得超額收益及風險損失減少值、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概率、對違法企業罰款額等因素的影響[8]。
假設在一個包含消費者、農場、企業的供應鏈模型中,消費者是唯一的產品購買方,僅有一個供應鏈上游的農場供給原料,有唯一的供應鏈下游的企業進行產品加工和銷售。雙方同時使用供應鏈可追溯系統,且供應鏈中所有企業均在監管部門監管下,一旦出現產品安全問題時企業須支付賠償金M;若事后查出是農場的責任,那么農場須要支付賠償金,且須要支付給企業聲譽損失費N。
因為λ、r為正的常數,當責任追溯能力很低時,企業和農場預期的安全責任成本與A(最大產量)負相關。根據理性經濟原理,雙方都會選擇不投入,即不使用可追溯。此時責任可追溯性不強,導致許多不法商家投機取巧,鋌而走險生產低成本、低質量的產品以賺取高額利潤。而一旦發生事故,若賠償金M、N很高,很可能使企業面臨高額罰款導致破產,引起市場動蕩,企業更迭頻繁。因此,農產品安全問題的保障不僅須要建立高效的可追溯系統,還須要確立合理的責任賠償機制。
3 內部違約懲戒和監督的有效性
農場和企業即使建立了可追溯系統,在管理過程中也可能存在機會主義行為,為了約束雙方的行為,保證農產品質量,雙方往往會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在第三方的影響下雙方都存在違約行為或違約傾向。因為第三方的存在往往會影響到企業之間的原定價格,因降低成本驅使,企業會選擇第三方。如果被發現,進而會產生違約成本。其最終決定因素是違約成本與違約利益,當違約利益大于違約成本時,雙方都會產生違約行為;當違約成本大于違約利益時,雙方都會選擇履約。即使在沒有第三方影響的情況下,雙方也存在博弈行為。
假設7:農場與企業合作,農場作為供應鏈的唯一上游企業向唯一下游企業提供原材料,在可追溯成本C及可追溯規模θ不變時,農場總收益為R1,企業總收益為R2。
假如雙方的合作是1次性的,即雙方的博弈為單次博弈,在一次交易完成之后,合作結束。對于農場而言不管違約與否得到的總收益為R1,因不履約可能會降低成本,那么農場有違約傾向。對于企業而言,因最終產品收消費者及社會監督,可能會存在其他損失,因此收益會小于或等于R2。進而可知,在一次性交易中,產品的所有風險由企業承擔,企業的利益損失較大。
因此,在實際交易中銷售者往往采取簽訂長期契約的方式,與農場建立長期的交易關系,這樣不僅可以降低自身風險,還有利于穩定原料價格以降低成本。在多次交易中,農場的行為就會受到企業及社會的監督,出現問題時,農場也要為自己的違約行為付出成本。
假設8:農場在不違約時的收益為R1,成本為C1,違約概率為p,不違約概率則為(1-p)。企業可以選擇對農場監督或不監督Cs2,監督成本為q,監督的概率為q,不監督的概率為(1-q),農場在違約的情況下檢驗出問題的概率為n,檢驗不出問題的概率為(1-n)。農場在違約的情況下產品出現問題的概率為m,不出現問題的概率為(1-m)。當企業采取監督行為時,農場違約且檢驗到違約,則農場收益為0,違約金為W,農場聲譽損失為L1;農場違約且沒有檢驗到違約時,企業受到市場懲罰為F,聲譽損失為L2,農場賠償損失為E。當企業不采取監督農場違約時出現食品安全事故,企業受到的市場懲罰為(F+l),聲譽損失為(L2+l),農場賠償損失為(E+l),聲譽損失為L1。l為企業不監督時的額外懲罰(l>C)。
農場是否違約和企業是否監督的決策最終都會影響他們的收益,不同決策下的收益見圖2。
當市場沒有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時,企業傾向于不監督,此時企業的收益為R2,農戶選擇違約,收益為R1,此時達到納什均衡。但是在企業不監督的情況下,如果出現安全事故其懲罰損失l將會很大,很可能導致其凈利潤為負值,甚至導致企業停產,所以不監督對企業來說不是好的選擇,企業選擇監督的可能性大一些[6]。
當(R2-F-Cs2-L2)>(R2-F-L2-3l)即 3l>Cs2時,說明企業不監督的損失大于監督時的損失,企業為長遠考慮會選擇監督。就農場而言,不違約也是更好的選擇,隨著農場對可追溯系統的了解,農場會知道違約一旦被檢出其損失將很大,不但要繳納違約金W,還會影響聲譽,聲譽影響對農場來說可能是致命的,不僅合作的企業不會購買自己的產品,不合作的企業也會因為有違約記錄而選擇不合作,最終農場產品將無路可銷。因此,為了避免風險農場會選擇不違約。此時,企業監督和農場不違約將是雙方的風險上策均衡,雙方受益為(R1-C1)、(R2-Cs2)。該結果是供應鏈可追溯系統所達到的最好結果,此時社會福利將達到最大化,不僅對供應鏈各成員有利,也給消費者帶來了健康安全的食物。長遠來看,該結果有助于促進社會、經濟、生態三者利益的協調和統一。
4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博弈論分析影響農產品供應鏈上主體參與可追溯系統的因素。總體來看,可追溯系統建立帶來的產品價格溢價的獲得、預期安全成本大小、賠償機制的合理性及內部違約懲戒制度的有效性是影響農產品供應鏈上主體參與可追溯管理,實現可追溯系統推廣的3個關鍵因素。首先,供應鏈主體合理利潤的獲得是可追溯系統建立的前提。參與者會比較其可能收益與成本,若可以獲得利潤,參與者就會使用可追溯管理,不得益就會選擇放棄使用。在農場使用可追溯管理的情況下,企業有使用可追溯體系的激勵,因為在農場使用可追溯管理的情況下企業會獲得更高收益,且供應鏈主體全部使用可追溯管理的情況下,企業獲利大于農場,即企業有更大的動力使用可追溯,企業為增加自身收益也會支持農場使用可追溯技術。因此,供應鏈主體的合作有助于可追溯系統的建立,應鼓勵企業通過補貼等方式激勵農場使用可追溯系統。其次,預期安全責任成本和賠償額度是影響企業行為的重要因素。在第三方責任追究能力不高的情況下企業使用可追溯的激勵效果就較差,因為消費者和食品安全管理部門很難追究到他們的責任,預期的責任成本很小,將選擇不實施。當賠償責任超出合理區間時,又會引起參與者頻繁地進入或退出市場,引起參與者投機偏好最大化。因此,政府須要增強農產品安全責任追究能力并構建合理的賠償機制,還要幫助供應鏈參與者設立合理的資金投入規模,以獲得最高收益。最后,企業對供應鏈的監管和農場的合作是可追溯系統運行的重要保障。雖然使用供應鏈可追溯系統,但也不能完全保證參與者的行為一定規范,因此須要對彼此的行為進行監督。尤其對企業而言,在追溯不到農場責任時,所有事故責任都由自己負擔,因此,企業有對農場行為進行監督的偏好。對于農場而言是否違約要看其收益或損失的大小,因此,企業應加強監督力度,減少農場的投機行為。
對建立更加有效的農產品安全管理機制有如下建議:加強食品安全責任可追溯性,明晰事故責任方,保障消費者權益,禁止出現包庇及推卸責任等行為;建立合理的農產品安全賠償機制;為促進可追溯系統的使用和推廣,政府須對供應鏈的源頭農場進行補貼,鼓勵他們使用供應鏈可追溯系統;升級及創新可追溯系統并降低使用者的成本。
參考文獻:
[1]Sterling B,Gooch M,Dent B,et al.Assessing the value and role of seafood traceability from an entire value-chain perspective[J]. Comprehensive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Food Safety,2015,14(3):205-268.
[2]Aung M M,Chang Y S.Traceability in a food supply chain:safety and quality perspectives[J]. Food Control,2014,39(5):172-184.
[3]Chang A H,Tseng C H,Min C Y.Value creation from a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based on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consumer personality traits[J]. British Food Journal,2013,115(9):1361-1380.
[4]周湘貞,馮穎超. 近場通信策略下生鮮農產品可追溯供應鏈價值研究[J]. 江蘇農業科學2017,45(23):324-329.
[5]鞏永華,薛殿中,仲凱旋. 可追溯食品供應鏈博弈分析與協調研究[J]. 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7(1):44-48.
[6]王曉平,張旭鳳. 農產品可追溯制度下企業與農戶行為的博弈[J]. 中國流通經濟,2013,27(9):94-99.
[7]龔 強,陳 豐. 供應鏈可追溯性對食品安全和上下游企業利潤的影響[J]. 南開經濟研究,2012(6):30-48.
[8]楊正勇,侯熙格. 食品可追溯體系及其主體行為的演化博弈分析[J]. 山東社會科學,2016(4):132-137.許黎莉,般麗麗,烏云花. 非對稱信息下農業信貸擔保機構擔保支農的最優契約配置——基于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分析范式[J]. 江蘇農業科學,2020,48(6):3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