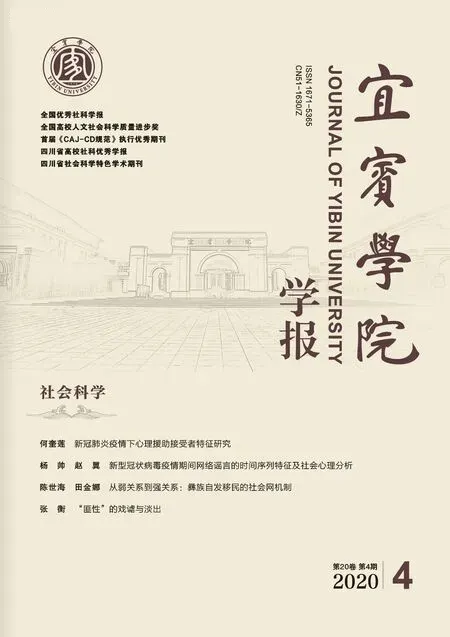從弱關系到強關系:彝族自發移民的社會網機制
——對寶鄉空心化后彝族填充現象的田野調查
陳世海,田金娜
(1.宜賓學院法學院,四川宜賓644007;2.四川外國語大學社會學系,重慶400031)
欠發達地區少數民族自發遷移到相對發達但呈空心化狀態的漢族農村地區,以尋求發展出路實現脫貧,是當前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流動領域中的一種特殊現象,也是異地扶貧搬遷的一種“變異”。現有研究指出:“少數民族自發移民”通常具有以下幾個特征:沒有列入政府移民搬遷計劃、不能享受到相關移民的政策待遇[1],由少數民族在無組織下主動、自發實施[2],能夠在流入地獲得更高質量的生活但是難以獲得本地戶籍[3]。少數民族自發遷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遷出地通常氣候寒涼,山高坡陡,土地貧瘠,生存條件惡劣[4];自由遷徙的阻力小,遷入地的發展條件相對優越,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完善,前期自發移民的示范效應[5]等。但是,遷入移民面臨戶籍、土地、勞動保障、醫療等社會問題,給移民適應和扶貧工作造成了很大障礙[6]102,需要在民族互嵌格局縱深推進與發展鞏固的理念引領下,從社會治理、文化互融、產業發展、基層組織建設等各方面加強工作[7]。在當前本領域的研究中,有關少數民族自發移民的原因、問題及解決對策均較為充分,但是在實現遷移的機制和路徑上,反倒研究較少。事實上,對于少數民族而言,自發向相對發達但呈空心化狀態的漢族農村地區移民,在渠道方面仍然面臨諸多困難,目前難以呈規模化發展。本文以涼山貧困地區彝族自發遷移到相對發達的漢族空心化農村寶鄉為田野點,系統考察了彝族自發移民的社會網運行機制,并針對機制運行的內部邏輯開展反思,以期助力于少數民族自發移民的理論與實踐。
一、 寶鄉的空心化:彝族自發移民的基礎
寶鄉位于四川省R縣。R縣地處成都平原中南部,緊鄰成都市,是四川省首批擴權強縣試點縣、縣域經濟發展先進縣、省直管縣、成渝經濟區核心縣、天府新區重點縣,縣域經濟基礎好。寶鄉北距成都82公里,距R縣城僅2公里,南距樂山100公里,省道106線(國道351線)橫貫全鄉,成赤高速寶馬段(5.683公里)、遂資眉高速路寶馬段(8.05公里)均已建成通車;寶鄉擁有村道150余公里,村莊道路成網絡,已達到“村村通”“社社通”,交通非常便利。從人口狀況來看,寶鄉面積55.9平方公里,轄12個行政村,86個社組,全鄉1.09萬戶、3.08萬人,非農業人口2 965人,僅占9.6%,農業人口仍然是寶鄉的主要構成部分,男女性別比為108.6∶100;18周歲以下人口占比17.3%,60歲以上人口占比21.8%,老年化程度很高,2011年至2015年的五年內,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即提高了兩個百分點,本地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現象非常明顯;從農村經濟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11年的6 433元、2012年的7 655元、2013年的8 811元、2014年的9 730元發展到2015年的11 525元,年均增長15.8%。據寶鄉內部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和201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4 533元[8]和15 786元[9],均超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8個百分點,在全國農村屬于經濟發展程度中等偏上的水平,且近年增長迅速。從總體上來看,因毗鄰縣城和成都市,寶鄉在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獲益較大。一方面就近務工機會多,使得農民收入較高,經濟較為富裕;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農業勞動力不足。以上因素,從吸引力和資源需求兩個方面,為相距不遠的涼山彝族的自發遷入,提供了前提條件。
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不斷向相對發達的城市、城鎮等地區轉移,形成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日益減少的局面,以致出現了很多婦女、兒童、老人留守的空心村,學術領域稱之為農村空心化現象[10]。這種現象在緊鄰中心城市、周邊城鎮化發展迅速的寶鄉表現明顯。伴隨著大量人口的遷出,寶鄉呈現出了與普通空心化有一定差異的非典型“空心化”狀態:一般的空心化是因為青壯年勞動力外出,非勞動力留守,呈現出村莊活力不足的現象;而寶鄉的空心化主要因為大量人口舉家外遷到縣城或成都市,呈現出人氣不足的現象。在開展寶鄉空心化的訪談中,長期在鄉政府工作的本地漢族干部MKJ介紹說:
全鄉外出務工的人員,占本地勞動力的45%左右,加上帶著老人、孩子在外生活的,估計要占到本鄉人口的60%。這方面沒有詳細的統計數據,只能是一個估計數。外出務工人員的去向主要是成都以及本縣的周邊地區。大量年輕人外出,連村社干部都要找人來擔任,土地閑置、拋荒的現象很多。本來本鄉人均耕地約9分,真正用來種植的不到一半。本地人外出務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農民賺了錢以后,有些在城里買了房子、搬出去居住,土地閑置。當然,勞動力流失比較嚴重,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造成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的增加;土地閑置或荒蕪也是一個大問題,有一些外地彝族搬到本鄉后,種了閑置的土地,也是一種資源的再利用。
(個案編號:Z20170824MKJ50①)
約六成的人口是人戶分離狀態、超過半數的土地閑置,說明寶鄉的空心化狀況明顯,也為涼山彝族的自發移民提供了基礎條件。大城市帶動農村協同發展策略、統籌城鄉發展改革策略,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天府新區的設置,都為寶鄉等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并扎根于城市,進而實現整家遷入城市生活、加快城鎮化發展提供了條件。這一系列的區域發展措施,為寶鄉的空心化和涼山彝族的自發遷入奠定了基礎,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R縣作為天府新區核心縣、成都市統籌城鄉發展重點縣,充分利用了融入大成都發展的機遇,在城鄉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較大成績,特別是大量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在成都市、R縣城獲得了持續生存的機會后,通過自身身份的改變突破了城鄉二元體制的局限,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市民化的過程,而其留存在農村的房屋和土地,因丘陵地理條件的局限制約了大規模流轉的可能,出現了較為普遍的房屋閑置、土地拋荒現象,而寶鄉緊挨R縣城,對意圖遷入的彝族有較大吸引力。另一方面,統籌城鄉發展和天府新區建設過程中,需要大量勞動力資源,特別是能夠吃苦耐勞的低端勞動力資源,這種資源在本地漢人中已經較為稀少,而可以為“肯賣力、酬勞低”的彝族提供良好的補充性生計來源(有大量的打零工機會)。綜上兩個方面可以看出,本地城市經濟發展為漢族農民遷入城市生活帶來了機遇,這也是農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而其農村閑置的房屋和土地可以為彝族的遷入提供落腳地和基本生存保障。同時,本身較為發達的城鄉經濟、新區建設帶來的就業機會,可以為彝族遷入后的持續發展提供進一步的可能性。在這種背景下,自21世紀初,陸續有外出尋找打工機會的涼山彝族遷入到寶鄉,從開始的勞動力遷移,到后來的整家遷移、安家,這其中的遷移機制,則非常值得探討。
二、 從弱關系到強關系:彝族自發移民的機制
寶鄉村莊空心化、土地和房屋閑置,為外來人口的遷入奠定了前提條件。而且,在青壯年人口外流的條件下,有關村莊事務的關注程度和治理能力均呈弱化態勢,特別是農村基層權力淡漠現象明顯,降低了外來人口遷入的管控壓力。于是,自21世紀初,陸續有附近的涼山彝族自發移民到寶鄉,在本地長期生活。事實上,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寶鄉,R縣的其他鄉鎮、成都周邊的城市都不同程度接納了外遷進來的涼山彝族人口。只不過,寶鄉因毗鄰縣城(打零工的機會多)、空心化程度高(閑置的土地房屋多),涼山彝族的自發移民現象較為突出。
在寶鄉各村的入戶訪談中發現,沒有人能夠記得起第一戶彝族是什么時候遷入的,只知道大約在2000年左右。事實上,當地政府部門和村委會,也沒有對外遷進來的彝族進行過歷年統計,因此缺乏這方面的連續性數據。寶鄉XG村干部HJG介紹彝族的遷入過程時介紹說:
我們這邊的彝族大概是2000年前后來的,有十幾年了。一開始我們隊只有一兩戶人,是我們這邊的年輕人在外打工,娶了一個彝族女人,彝族女人嫁進來后,介紹了自己家的親人到這邊打工。也有彝族到鄉上的鐵廠打工,后來租了這邊房子后搬過來的。到了2003、2004年后,一家介紹好幾家,這好幾家又介紹好幾家,像個樹枝分叉,越分越多,最多時候大概是2008年左右,光我們隊怕有十多戶彝族、四五十人,我們也沒有仔細統計過。主要是因為以前出去打工的,慢慢也把娃兒帶出去讀書了,房子、田地,越空越多,所以彝族也比較方便找到可以租的房子。只不過近些年,彝族少了一些,主要是本地人很多不愿意租房子給他們,他們慢慢地就到其他地方找活路去了。現在我們隊總共也只有200多人,常年在家的,只有30多個年紀大一些的老人,娃兒都少了,彝族有3戶、16口人。這些年新遷進來的都少了,能夠留下來的一般都是比較“乖”的,跟本地人處得來,要不然也租不到房子了。當然也有一些買了本地人的房子,就算是安家了,只是戶口遷不過來,本地人也不希望他們落戶。
(個案編號:S20160312HJG29)
筆者通過對各村走訪調查,以請當地老人和村干部回顧的方式,大致整理出了彝族遷入寶鄉的人口發展歷程,結合本地常住人口的逐村統計、累加,得出了歷年遷入彝族與寶鄉本地常住居民數據對比圖(見圖1)。

圖1 歷年遷入彝族與寶鄉本地常住居民數據對比圖②
結合圖中的估算數據和訪談得知,彝族遷入寶鄉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3年以前,為彝族的少量遷入階段,遷入的觸發因素包括在外打工時與寶鄉漢族人結婚后的親屬遷入,以及彝族在本地務工形成熟悉關系后的家庭遷入。本階段遷入的彝族人數較少,僅88人,占本地常住居民的0.4%。第二階段是2004年到2011年,為彝族遷入的上升階段,遷入的方式基本是彝族內部的相互介紹,來源地基本是涼山州的各貧困區縣,遷入的人口從之前的88人增加到376人,到頂峰時期的550人,占本地常住居民的比例分別為1.9%和3.4%。第三階段是2012年到2015年,為彝族遷入的下滑階段,本階段遷入彝族的存量呈下降趨勢,從550人下降到320人,占本地常住居民的比例也下降到了2.1%,主要原因是遷入的部分彝族在本地生活過程中,與漢族人的關系出現了一些障礙,難以找到持續發展所必需的房屋和土地,故而再次遷移到了其他地方(或者回流)。第四階段是2016年以來,為彝族遷入的穩定化階段,遷入彝族的存量保持在240人左右,占本地常住居民的比例保持在1.9%左右,彝族留下來持續生活的主要原因是能夠與本地漢族人“處得來”,能夠租得到房子和土地(或者已經購買了本地漢族人的房子)。
從以上階段劃分③可以發現如下規律:婚姻關系的建立和勞動機會的持續存在是彝族遷入寶鄉的兩個重要引致因素;親屬、朋友等社會關系網絡,是彝族持續遷入的重要影響因素;作為擁有不同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的彝族,在遷入寶鄉后的生存和發展極其依賴于與本地漢族的相處,特別是漢族對彝族的接納程度:被接納程度高的彝族人能夠在本地持續生活與發展,程度低的則可能面臨“淘汰”,而不得不尋求新的遷移。自2000年以后,彝族遷入寶鄉經歷了逐漸增長的過程,特別是2004年至2011年,增長速度較快。正如前文所述,彝族早期遷入的主要引致因素是婚姻遷入(通過共同在外務工,結識并嫁給寶鄉的漢族人后,到寶鄉本地安家)和職業遷入(在寶鄉本地從事體力勞動多年,積累了一定社會關系后將家庭成員隨遷過來)。那么,這些早期移民與后來遷入的彝族有什么關系?彝族遷入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對多位彝族開展跟蹤式訪談以后發現,社會網在彝族遷入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我們老家在喜德山區,我和弟弟一直在外面打工,因為認識了一個寶鄉本地的漢族朋友,他說寶鄉這邊有彝族人搬遷過來生活,我們就很感興趣。我們那邊屬于高山地區,就靠土地和打工,地也種不出什么來,打工也只能干些苦力,都找不到多少錢。通過這個漢族朋友的提供的信息,我們2007年在寶鄉經過很長時間的尋找,終于找到了一個房子,把全家都搬出來了。搬出來的時候我們四塊(口)人,父母和我們兩兄弟,后來我在這邊娶了一個雷波搬來的彝族女子,現在生了3個孩子,總共有7個人了。我們搬出來以后,老家的房子空著,土地沒有種了,也不值錢。回鄉的時候,老家的人看我們過得還不錯,也想搬出來,那邊條件太苦了,娃兒讀書要走兩三個小時,交通不方便。后來,我們在2008年幫四姨家找了一個房子,他們就搬了出來;2009年幫二姑家和以前村里鄰居各找了一個房子,他們也都搬出來了。現在要我們幫忙介紹的也還有,只是少了一些,村子里的人基本都搬出來了,其實主要是能夠找到房子,要不然不好落腳。
(個案編號:CY20150719MKR06)
筆者對彝族MKR提到的搬遷過來的三家人進行了滾雪球式的走訪,發現如下:MKR四姨一家自2008年搬到寶鄉,6口人,該家庭的男主人又分別給自己遠在老家的親人找到了房子,幫助其搬到寶鄉,分別是2009年幫哥哥家(6口人)和弟弟家(6口人)實現搬遷,2010年幫妹妹家(7口人)實現搬遷;MKR的二姑家(8口人)自2009年搬到寶鄉,8口人,后又于2011年幫侄子家(7口人)在寶鄉找到了房子并搬遷過來,2012年幫老家的鄰居(8口人)搬了過來;MKR的鄰居家(6口人)自2009年搬來后,又介紹了四家人實現搬遷,分別是其姐夫家(2011年,8口人)、妹夫家(2012年,8口人)、堂叔家(2013年,10口人)和朋友家(2013年,7口人),詳見圖2。

圖2彝族遷入過程中的社會網運行案例分析示意圖
正如寶鄉XG村干部HJG所說,“一家介紹好幾家,這好幾家又介紹好幾家,像個樹枝分叉,越分越多”,這種親友的相互介紹是彝族遷入寶鄉的最主要途徑。整個社會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由個體、群體或組織之間相互交錯或平行發展所形成的網絡進而構成的大系統,這個大系統便是社會網[11]21-23。從個體角度來看,整個社會經過細分后最終可以化約為相互聯系的個體,個體是自身社會網的中心,社會網中的每個成員均為相互關聯的節點,這些節點以地緣、血緣、親緣和業緣等關系為基礎,共同構成了網絡中心點采取社會行動的“資本”。所以,社會網分析通常強調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這兩個概念,而對這兩個問題的分析有利于進一步了解社會個體的行動及其參與社會變遷的過程[12]72。
從訪談信息與“彝族遷入過程中的社會網運行案例分析示意圖”中可以看出,MKR通過在外打工結識了寶鄉的一位“漢族朋友”(這個人成為MKR社會網中的一個節點),并通過他的介紹,順利在寶鄉找到落腳點并實現了家庭的遷移。這種基于業緣關系所拓展開來的社會網,蘊含了與其自身原有網絡成員相異的資源(外界的信息),增強了網絡的異質性。在社會網研究中,網絡成員的社會聯結強度可以區分為“強聯結”和“弱聯結”兩種,其區分的主要依據是網絡成員之間交情的久暫、親密的程度和互動的頻率[13]14,交情越久、越親密、互動越頻繁,聯結的強度越高、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越大、投入支持的意愿越強,通常存在于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的網絡成員之間,這種即為“強聯結”;反之,存在于業緣地緣關系的網絡成員的聯結通常為“弱聯結”④。格蘭諾維特在社會網研究中,曾提出“弱聯結優勢”的理論,指出弱聯結在信息傳播方面比強聯結更有價值,兩個社會網絡團體之間的信息通路可以被看作是“橋”,這種橋往往是弱聯結所構成的,因為在社會網絡團體內部的信息通常較為類似,而不同團體之間需要互通信息時,則往往是因為兩個社會網絡團體中有部分成員建立起了鏈接關系,使得兩個網絡聯系在了一起[14]。MKR的“漢族朋友”與其本不屬于同一社會網絡團體,兩人建立了聯結,搭建了兩個社會網之間的“橋”,使得彝族獲得了其他民族群體成員所知的“信息”,在付諸行動后實現了搬遷。由此可見,“弱聯結”是早期的彝族遷入寶鄉的關鍵因素。進一步來看,這種弱聯結發揮作用的根源是,彝族拓展了自身社會網的范圍,使得網絡成員的異質性增強,獲取的信息也才可能更多樣。所以,網絡異質性蘊含的資源具有更多的可能性,提高社會網資本存量的重要方法是擴大網絡異質性。
在MKR一家遷入以后,其先后幫助親屬和鄰居等三戶人(共計20人)實現了搬遷,這三戶人又分別幫助三戶、兩戶、四戶人(共計67人)遷入寶鄉⑤,這個過程就如同種下的樹木,逐漸成長、分叉,在形式上就像是一張網絡。可以看到,后續遷入的人員基本都是家支成員、親屬、鄰居,這些在社會網中可以歸入“強聯結”的范疇。威爾森研究指出,在國內移民和跨國移民中,移民過程的實現,往往是通過親屬網絡予以“策劃和安排”的,關系強度高的(也即強聯結),可以為后續移民提供或介紹“住所、工作機會、貸款等等資源,以幫助(他們)遷入后能夠適應當地生活,以及尋找更多的發展機會”[15]。由此可見,在MKR之后的12戶、87人,遷入寶鄉的社會網運行機制與MKR不同,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基于血緣、親緣等關系所形成的“強聯結”,是先遷者對后遷者在道義上提供幫助和支持的具體體現。
總之,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社會網中的“弱聯結”在早期的彝族遷入寶鄉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后續遷入過程中,“強聯結”則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轉變的關鍵因素,依賴于網絡蘊含資源的差異與遷入者的資源需求相匹配的程度:早期遷入者在外打工期間結識了寶鄉漢族人,這種異質性的網絡結點(弱聯結)為其提供了寶鄉人口遷出、土地及房屋拋荒等信息層面的資源,這些資源符合早期遷入者尋求家庭持續發展的需求,進而幫助其實現了自發移民;后期遷入者網絡資源的主體,則由前期已經實現自發移民的彝族同鄉等同質性資源(強聯結)構成,這些網絡結點在實現搬遷后,可以就近尋求自發移民所需的閑置房屋和土地,能夠為前者的搬遷提供信息及各項具體的幫助,符合后期移民的資源需求。由此可見,少數民族自發移民的社會網運行機制中,強弱關系各自發揮作用的邏輯,在于網絡資源在何種階段、何種程度可以滿足網絡主體的需求,當資源需求與網絡供給相匹配時,不論是強關系還是弱關系,都可能發揮相應作用。
三、 彝族自發移民后的社會網聯結
涼山彝族在自發移民到寶鄉的過程中,社會網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遷入后,彝族成員之間,仍然保持了自身社會網聯結,同時,還在不同程度上嵌入到本地漢族人的社會網之中,這種嵌入過程,事實上也是社會網的拓展過程。
我家里面有5塊(口)人,有3個兒子,老大18歲了,在外面打工,老二16歲了,在老家的時候還在讀書,搬過來了以后就沒有讀了,在家里幫著干活路,老三滿了8歲,在這邊讀書。是我大姐把我們介紹過來的,才來了不到一年,有的地方習慣,有的還不是很習慣,主要是蚊子太多了,那種墨蚊子。房子租的是當地人的,每年交1000元的房租,我們已經先給了3年的。我老公原來是在阿壩修房子的,現在在這邊打零工,這些零工都是這邊的親戚幫忙介紹的。我們現在有3、4畝地和水田,才開始種,谷子也是才學著種的,是自己的親戚教的。在這邊還是覺得我們自己人更親,走動很多,與周圍漢族人沒有什么走動,也不太會說漢語,但是與那個漢族人HXR關系好,打谷子、收苞谷都是他幫忙的,他經常幫助周圍的彝族人。現在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在這兒長住,還是有可能會回去的。大概每1-2個星期,房東老板家里有個老婆婆就會回來一次,跟我說房子要打整干凈些,還會主動教我們用東西(主要是農具),說我們太窮了,遭孽得很,所以屋里面好多東西都主動拿給我們用了,說省得我們又再花錢,不劃算。
(個案編號:CY20180114ZDJ89)
遷入寶鄉的彝族在日常生活和生產中,與原先遷入的親戚保持了較為密切的聯系,內部的社會網絡更為緊密。ZDJ家遷入的時間較短,在進入寶鄉這一原本陌生的環境之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作機會的介紹、農業生產技術和工具的使用,都有賴于自身社會網中的彝族提供幫助,這些向本族人求助并互相往來的過程強化了彝族自身原來親屬網絡的緊密程度,“我們自己人更親”便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另一方面,“老板家的老婆婆”“漢族人HXR”也在日常生活和生產中給予了很多幫助,使得ZDJ的社會網絡向本地漢族人拓展了一定范圍。但是,語言不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自身社會適應的可能性,對于能否在本地長期生活,ZDJ的信心仍然不足。可見,社會網拓展范圍、網絡資本的積累程度,是彝族能否在本地站穩腳跟、獲得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事實上,根據筆者對彝族的大量深訪發現,遷入的彝族之間相互熟悉、相互來往的比例很高,這既印證了其遷入過程本身有著社會網的推動作用,也說明了遷入后彝族仍然保持了密切的網絡聯結,構成了集體性的力量。這種抱團發展的思維,在一定程度上為其增強自身的“實力”“話語權”“資本”提供了幫助。當然,反過來看,本地漢族人也正是因為彝族的這種“團結”思想,產生了較強的負面印象,進而在不同民族的社會互動中種下了“差異”的種子,被視為是與本地人博弈的資本。
當然,也有的彝族在遷入寶鄉后,基本脫離了原先的社會網,組建了以本地漢族人為主體的社會網絡,這種現象較少,但很有分析價值。
我2013年從雷波馬湖過來這邊,是一個同村鄰居介紹來的。以前在河北挖過礦,在湖北大冶、鄂州的鋼鐵廠做過工,都沒有攢到什么錢。以前老家的鄰居2007年就到了這里,生活比老家強很多,我那里住在山上,從家里出去趕場,來回要一天時間,熱天去買一塊肉,回到家差不多就臭了。孩子上學、看病那些都不方便,山路也不安全。種的苞谷、土豆,還不夠一家人吃,日子太苦了。到這里后,我和婆娘在這邊的養牛場打工,200多頭牛,每天都要喂,離不開人,一年四季不休息,兩個人每個月一共5 000元。因為除了喂牛,基本沒有空余時間,所以和搬過來的親戚朋友基本沒有往來了,倒是這邊的老板和工人對我很好,經常給些菜、孩子的衣服什么的。我搬了3次家,都挨得很近。第一個是老鄉給介紹的,1 600元一年,還有一塊荒地,種點苞谷,后來人家回來了,就不租給我了;第二次是LCM的房子,是工友介紹的,也是1 600元,沒有地,后來人家嫌我們把房子弄得煩(很臟、亂),就不肯再租了,我們在牛場旁邊找不到房子了,就想回去,后來牛場老板舍不得我們走,怕找不到人做事,就幫我們找了2隊的隊長,租了隊長的房子,也是1 600元一年,但是沒有地種。
(個案編號:CY20160221JLER16)
在訪談中明顯感到,JLER的日常生活非常簡單,除了工作和日常生活,基本沒有時間和彝族往來,甚至是家支親戚之間,走動也極少。多處的打工經歷使得JLER認識到,和當地人處好關系是多么重要。JLER的鄰居、老板、工友均反映,JLER勤勞、肯做,不多話、不惹事,不像其他彝族,賺了錢就喜歡買酒買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JLER逐漸退出了原來由彝族組成的社會網,并建立了主要由本地漢族人所構成的網絡,這個網絡中蘊含了較多的資源:生活物品的支持、工作的支持、找房子的幫助,甚至當JLER想離開時,老板還會“舍不得”。由此可見,具備如下特征的彝族更能取得更好的生活適應和社會認同:有較多的外界工作生活經歷,使得價值觀念上容納性更強;工作勤勞肯干,使得自身具備較高的勞動力價值;生活上與彝族接觸少、與本地人接觸多,不鋪張浪費,使得本地人有較好的印象。所以,遷入的彝族重構自身的社會網,甚至嵌入到本地漢族人的社會網絡之中,有可能獲得更好的持續發展機會。
總之,在社會網的支持下,涼山貧困地區部分彝族實現了向相對發達的漢族農村自發移民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對空心化的寶鄉農村發揮了“填充”的作用。完成自發移民后,彝族在寶鄉仍然維持了以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內部社會網,且在不同程度上向本地漢族擴展。內部社會網的維系,一方面為彝族在寶鄉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群體基礎(正是在相互幫助的依賴關系中,這種內部網絡才得以加強),并為更多涼山貧困彝族的遷入提供持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異鄉”保持較強的內部社會網,可能對寶鄉本地漢族人造成一定的群體壓力,這種群體壓力在某些事件的激發下會引起本地漢族人的應力,從而對外來彝族在本地建構高層面的社會關系造成障礙。由此可見,彝族在寶鄉維持較強的社會網,是一柄“雙刃劍”。另外,遷入的彝族向寶鄉本地漢族擴展社會網,嵌入到本地人的社會生活之中,這對其獲取強異質性的網絡資源無疑是一個重要幫助,有利于獲得本地人的支持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可以為引入更多的涼山貧困彝族提供幫助。由此可見,自發移民到漢族農村的少數民族,在一定強度上保持自身內部的社會網,同時向本地漢族拓展網絡邊界,是獲得本地可持續發展機會、爭取更多貧困人口實現移民的關鍵。
結語
周邊城市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是寶鄉人口大量外流并造成空心化的根本原因。村莊空心化之后寶鄉出現了人口減少、土地閑置、集體經濟衰落的現象,村莊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都呈弱化、散亂狀態。這些因素既為涼山貧困地區彝族的自發移民奠定了基礎,也降低了遷入過程的阻礙,當然也減少了外來彝族適應本地生活的制度和管理支撐。研究指出,彝族自發遷入寶鄉經歷了少量遷入階段、遷入的上升階段、遷入的下滑階段以及遷入的穩定化階段,在這個發展過程在,社會網中的“弱聯結”在彝族的早期遷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強聯結”則在后續遷入過程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實現自發移民后,彝族一方面繼續維系并強化了自身群體內部的社會網,同時向本地漢族擴展網絡空間,這種行動實踐對移民的持續發展與流入,發揮了不同性質的功能。當然,在彝族自發移民的過程中,除了社會網的作用之外,宏觀人口流動制度的寬松化、微觀社會環境的差異化,都相應發揮了作用,這些作用如何與社會網產生協同機制,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規模較小的彝族人口自發移民到空心化狀態的漢族農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利用閑置資源、實現振興鄉村的作用,尚需進一步研究;彝族遷入到不同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的漢族農村,如何與本地漢族人產生良好的互動關系,促進雙方的良性發展,也需要社會治理方面的深入探討。
注 釋:
①訪談個案的編碼規則:按照個案性質、訪談時間、個案姓名的字母簡稱、訪談序號進行編碼。其中,個案性質包括:Z為政府人員,S為村社干部,CH為本地居民,CY為遷入的彝族;訪談時間為年月日的數字;個案姓名的字母簡稱用姓名的大寫首字母表示;個案訪談序號按照時間排列。對于一個對象開展了多次訪談的現象,以最后一次訪談時間為編碼時間。
②注:本圖數據的形成過程異常艱難,為筆者對各村深訪時,請當地老人和村干部回憶而得,并非政府部門統計數據。因記憶偏差的可能性較大,故而數據不一定準確。本研究試圖對比分析本地漢族人和遷入的彝族在數量上的關系,所以更為關注長期、固定生活在本地的人口,故而,“本地常住人口”并非社會統計學意義上的“外出務工人員雖然在外居住時間在6個月以上,但因其收入主要帶回家中,經濟與本戶連為一體,仍視為家庭常住人口”,圖中的“常住人口”不包括長期在外務工的寶鄉農民,僅計算了沒有外出務工、具有本地戶籍的農村人口,也不包括遷入的彝族和在本地務工的外地漢族人口。所以,因對比研究的需要,此處的“常住人口”不同于地方統計部門的界定,故而也沒有官方數據,亦從各村莊搜集而來。事實上,在缺乏官方統計數據的情況下,除了對各村進行口述史的量化回顧以外,別無他法。特別需要說明的是,2016年以前的數據,是按照階段進行統計的,主要是因為訪談對象無法回憶出過于久遠的具體數據,近兩年的數據則是按年度統計的。
③需要說明的是,這種階段劃分也不是完全準確、科學的,因為其所依賴的數據為訪談對象通過回憶、整理而得,這種數據本身就不是非常準確的。在沒有官方統計數據的時候,試圖完整還原彝族遷入寶鄉的人口變動過程是非常難的。當然,筆者為了印證階段劃分的真實性,特地將所劃分的階段分享給本地政府人員、村社干部和村民,得到的反饋是“和印象差不多”“比較準確”“基本是這樣”。所以,社會科學很多時候并非在描述“事實”(特別是呈歷史發展和變動的事實),而是盡量去接近事實。
④這種區分并不是絕對的,有時候關系相處不好的親屬之間的聯結強度也可能比較弱,反倒是極為親密的好友之間聯結強度很高,可以視為“強聯結”,其區分依據主要在于網絡成員為網絡中心成員提供幫助、支持的意愿。
⑤如果繼續采取滾雪球的方式,對后續家庭開展遷入過程的跟蹤調查,可能會發現這個相互介紹、幫忙尋找落腳點的方式,仍然會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