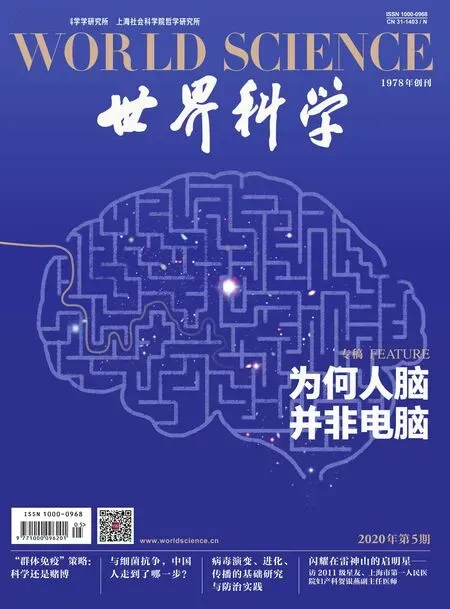數十種傳染病隨著季節消退,那COVID-19呢?

2009年7月,面對著流感病毒肆虐的巴西人一邊尋求外界幫助,一邊眼睜睜看著南半球的寒冬在大流行身后推波助瀾。
12月的一個下午,英國薩里大學的薩里臨床研究中心來了6名訪客,有男有女,在被能夠檢測16種呼吸道病毒的鼻拭子取完樣以確定身上是否攜帶病原體之后,走進了各自的溫度調節房間。然后每個人在昏暗的燈光下,半臥著,等待24個鐘頭的結束。
護士將醫用套管插入每個人手臂的靜脈中,他們的血液順著管子流到靠近墻邊的儀器中。6名受試者在這24小時內,可以按蜂鳴器,進入洗手間進行排泄,將自己的糞便和尿液送予醫護人員;而在這些時間以外,他們都是一個人孤獨地待在隔離間里。
這些人都沒有生病,但他們的這一“詭異”儀式與異教徒們的儀式無關。這6個志愿者的儀式是參加一場研究,該研究由哥倫比亞大學的傳染病生態學家米卡埃拉·馬丁內斯(Micaela Martinez)領導,旨在調查2 500年前希波克拉底和修昔底德認識到的一種現象:在特定季節,傳染病更為常見。
馬丁內斯說道:“這是一個很古老的問題,但研究還不夠深入。”
由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出現,馬丁內斯眼中的古希臘問題突然變得更加緊迫。如今,新型冠狀病毒(SARA-CoV-2,簡稱新冠病毒)已在全球范圍內確診感染超過290萬人。北半球溫帶地區的夏季快來了,一些人希望北溫帶(該地區人口約占世界總數的一半)的新冠疫情會像流感一樣消退,例如多次表示這一想法的特朗普。特朗普在2月14日說道:“有一種理論認為,4月份天氣變暖能夠殺死這種病毒。”但是,有關其他疾病的已知信息并不能為COVID-19在接下來幾周內突然消失的想法提供太多支持。
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模式。有些傳染病的高峰位于初冬或晚冬,有些則在春季、夏季或秋天;某些疾病的季節高峰隨緯度變化而異;甚至有許多根本沒有季節性。因此,沒人知道新冠病毒是否會在春季來臨時改變其行為。美國疾控中心(CDC)應對COVID-19主要負責人南希·梅森尼爾(Nancy Messonnier)在2月1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警告大家不要過度猜想。”哪怕季節確實會影響SARS-CoV-2的傳播,它也可能在第一年就違背大家的“意愿”,因為這個病毒還沒遭遇到人類的免疫力防御,一切皆有可能。
即使是對于著名的季節性疾病,人們也不清楚它們為什么會在一年當中起伏不定。同時,研究者所做出的針對若干個季節性的假設可能需要2~3年的時間來進行實證調查。曼徹斯特大學的時間生物學家安德魯·勞頓(Andrew Loudon)說:“此類研究令人煩躁!如果博士后想搞這方面調研,那么他們可能嘔心瀝血,最后也就只能完成一項實驗,從職業發展角度來看,這對他們的科研生涯極為不利。”
“混淆變量”(confounding variables)也困擾著該領域。流行病學家斯科特·道威爾(Scott Dowell)說道:“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是季節性的,比方說圣誕節購物。”道威爾在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負責疫苗開發和監管,于2001年發表了被廣泛引用的觀點,馬丁內斯當前的研究正是受到了他觀點的啟發。道威爾表示,研究很容易被虛假的相關性所誤導。
當然,盡管障礙不小,仍有研究人員奮戰在測試多種理論的第一線。其中許多人聚焦于病原體、環境與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例如,由于濕度、溫度、人與人之間更近的距離、飲食結構以及維生素D水平變化等因素,冬季的流感情況可能會好轉。馬丁內斯正在研究另一種理論——由道威爾的論文提出,但并未進行檢驗——人類的免疫系統可能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因為我們身體所接受光照強度的不同而改變抵抗力,以及改變對各種感染的敏感性。
除了“我們應對COVID-19懷有什么期待”這個迫切問題,知道哪些因素會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時間制約或促進傳染病發展,可能會為預防或治療它們提供新的方法。了解季節性還可以為疾病的監測、預測和疫苗接種的時間提供信息。道威爾表示:“知道什么東西可以將流感抑制到夏季水平,將比擁有流感疫苗有效得多。”
流行病日歷
馬丁內斯于201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至少有68種傳染病都是季節性的,但并不同步,并且季節性因地理位置而異。對流行病的季節性感興趣的她在還是阿拉斯加東南大學的一名本科生時,就追蹤了北極圈海豹的日常和季節性運動。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她對季節性的關注轉向了脊髓灰質炎,這是一種在疫苗問世之前人們非常擔心的夏季疾病。脊髓灰質炎的季節性反過來使她對其他疾病的季節性感到好奇。2018年,她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病原體》(PLOS Pathogens)雜志上發表了“流行病日歷”,其中包括68種疾病及其特殊周期的目錄。
馬丁內斯寫道:除了在赤道地區,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在冬季暴發,水痘則更傾向于在春季暴發;輪狀病毒在美國西南部的12月或1月達到高峰,在東北部的4月和5月達到高峰;生殖器皰疹會于春天和夏天在美國各地盛行,破傷風偏愛盛夏,淋病在夏秋二季起飛,百日咳的發病率在6—10月間更高......
部分傳染病具有明顯的季節性,不過大多數其他的傳染病都不會挑時間傳播。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的病毒學家尼爾·內森森(Neal Nathanson)說道:“真正令我驚訝的是,某個片區的某個環境里,幾乎每個月都會有某種病毒旺盛生長,那真是太瘋狂了。”
對于內森森而言,這種變化表明人類活動(例如,孩子們重返校園或在寒冷天氣中擠在室內的人們)不會促進傳染病的季節性暴發。
內森森懷疑,至少對于病毒而言,它們在人體外的生存能力更為重要。某些病毒的遺傳物質不光被包裝在衣殼蛋白中,還有的包裹在脂質包膜里。在感染過程中會與宿主細胞相互作用,以助于病毒躲避免疫攻擊。但內森森認為,遺傳物質包裹在包膜的病毒更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例如夏季的炎熱和干燥。
2018年《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中的一項研究支持了這一想法。愛丁堡大學的病毒學家桑迪普·拉馬林甘(Sandeep Ramalingam)和同事們分析了6.5年內尋求醫療服務的3.6萬多例呼吸道樣本,發現了9種病毒,有一部分病毒的遺傳物質被包膜包裹,另一些則不是。“那些有包膜裹著的病毒具有非常明顯的季節性。”拉馬林甘說道。
RSV與人類間質肺炎病毒都有包膜,它們也像流感一樣,在冬季達到高峰,且存在時長都不超過一年的1/3。鼻病毒是最廣為人知的引發普通感冒的病原體。它沒有包膜,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并不那么喜歡寒冷的天氣——有研究發現它們出現于呼吸道樣本的時光占一年的84.7%,在孩子們返校的春夏時節達到峰值。腺病毒是另一類感冒病毒,也缺乏包膜,傳播模式與鼻病毒相似,傳播時長超過半年。
拉馬林甘的小組還研究了病毒豐度與每日天氣變化之間的關系。當24小時內的相對濕度變化幅度低于平均值(25%)時,流感和RSV病毒表現最佳。他總結說:“當濕度急劇變化時,脂質包膜中的某些物質更易碎。”
哥倫比亞的氣候地球物理學家杰弗里·沙曼(Jeffrey Shaman)認為,最重要的是絕對濕度,即給定體積的空氣中水蒸氣的總量,而不是相對濕度。沙曼與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流行病學家馬克·里普西奇(Marc Lipsitch)于2010年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生物學》(PLOS Biology)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絕對濕度的下降比相對濕度或溫度更好地解釋了美國流感大流行發生的原因;而且,絕對濕度會因為冬季冷空氣中的水蒸氣較少而急劇下降。
不過目前尚不清楚為什么絕對濕度較低有利于某些病毒發展。沙曼表示,可能是因為包括滲透壓、蒸發速率和pH值在內的因素發生了變化進而影響了病毒膜活力。

在紐約和新澤西的一項研究中,馬丁內斯希望找出人工照明如何影響免疫系統
當絕對和相對濕度上升時,具有包膜的SARS-CoV-2在春季和夏季會變得脆弱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暫時給不了任何參考。SARS于2002年底出現,并于2003年夏季的有力防控中退散;MERS偶發地從駱駝傳給了人類,并在醫院中暴發,不過從未像COVID-19那樣在人與人之間瘋狂擴散。那兩種病毒都沒有足夠長的傳播時間,足夠大的暴發規模,以及任何季節性周期。
導致感冒和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4種人類冠狀病毒具有相對顯著的季節性。同在愛丁堡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凱特·鄧普頓(Kate Templeton)于2010年對2006—2009年間收集的11 661份呼吸道樣本進行了分析,得出結論:3種人類冠狀病毒具有“明顯的冬季季節性”,在夏季卻很少甚至沒有出現。
但這一切都不意味著SARS-CoV-2也會如此。
新冠病毒顯然可以在溫暖潮濕的氣候中傳播——新加坡就是一個力證。近期在預印本網站上發表的2篇新論文給出了彼此悖逆的結論:由里普西奇共同參與撰寫的一篇文章研究了COVID-19在中國19個省份的分布,這些省份遍及寒冷干燥到炎熱濕潤的區域,而最終的結果是疫情在這些地方持續傳播著;另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病毒的持續傳播似乎發生在地球上的一些特定區域,這些地區的溫度在5℃~11℃之間,相對濕度在47%~70%之間。
歸根結底,環境因素與人群免疫系統之間存在平衡。其他冠狀病毒已經存在很久了,因此一部分人群具有免疫力,這可能有助于我們在不利條件下防控它們,但這類情況并不適用于COVID-19。馬丁內斯說道:“即使新冠的傳播能力隨季節變化而下降的可能性很大,但如果環境中有足夠多的易感人群,它還是可以持續很長時間。”里普西奇也不認為該病毒會在4月消退。他在最近的一篇博客中寫道,“任何放緩都只是一定程度的放緩,不足以阻止傳播”。
馬丁內斯正在薩里大學研究可能最終影響COVID-19發病率的其他因素。她的受試者在四季多次回到診所,研究人員可以評估參試在一天當中,以及每個季之間,免疫系統和其他生理狀況的變化情況。
她并不指望以此證明我們的免疫力在冬季弱于夏季,而是希望通過免疫系統細胞計數評估血液中的代謝物和細胞因子,測量激素,以及破譯糞便微生物組,也希望發現季節可以“重建”免疫系統,從而使某些類型的細胞,在某些情況下,發生豐度改變,進而影響我們對病原體的敏感性。
動物研究支持免疫力隨季節變化的觀點。例如,格羅寧根大學的鳥類學家芭芭拉·霍爾(Barbara Hall)和她的同事研究了黑喉石鵖,通過一年跟蹤采集多個血液樣本,他們發現黑喉石鵖在夏天免疫系統增強,但在秋天(遷徙的時間)減弱了,大概是因為遷徙消耗了大量能量。
褪黑素一般在晚上由松果體分泌,是生物免疫系統變化的主要驅動力。西弗吉尼亞大學的內分泌學家蘭迪·尼爾森(Randy Nelson)表示,褪黑素不僅記錄著一天的時刻,還能作為季節的“生物日歷”。如果是在冬季的漫長夜晚,更多的褪黑激素會被釋放。在對西伯利亞倉鼠的研究中,尼爾森和同事已經證明,這些倉鼠與老鼠不同,服用褪黑素或改變光照模式可以使其免疫反應改變高達40%。
人類的免疫系統似乎也有先天的晝夜節律。例如,伯明翰大學的研究人員在276名成年人中進行了一項疫苗試驗,隨機分配了一半的人在早上接種流感疫苗,另一半在下午接種。2016年的研究報告稱,早上接種的參與者對疫苗里3種流感菌株中的2種有著更明顯的抗體應答。
有證據表明人類免疫相關基因的作用也存在季節性變化特點。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對來自歐洲、美國、岡比亞和澳大利亞的1萬多人的血液和組織樣本進行了大規模分析,結果發現了大約4 000個基因與免疫功能有關,這些基因具有“季節性表達特征”。在一個德國人隊列中發現,白細胞內1/4的基因表達因季節而異。當活動于北半球居民身體里的這部分基因活躍表達時,赤道以南人群體內的它們就會關閉,反之亦然。
不過,正如免疫學家扎奎因·多皮科(Xaquin Castro Dopico)及其同事在2015年描述該發現的論文中所解釋的那樣,這些巨大變化如何影響人體抵抗病原體的能力尚不清楚,而且某些變化可能是感染的結果,而非原因。正就職于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的多皮科試圖阻止那些急性感染者的出現,但正如他所說的:“季節性的傳染給我們的工作增加了難度。”另一方面,季節性免疫力的變化不能解釋疾病的全部季節性復雜變化。內森森指出:“他們彼此之間并不同步。”

濕度、溫度和其他因素的季節性變化可能會影響人們在打噴嚏或咳嗽時產生的飛沫中病毒的生存能力
但馬丁內斯表示她發現了有趣的線索。薩里大學研究已于2019年12月結束數據收集工作,而她對此的早期分析尚未揭示有關季節性的任何信息,但她確實也發現,在免疫系統的記憶和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特定白細胞亞群的數量會于一天中的某個特定時間提高。她希望在2021年開展規模更大的類似研究中進一步證實此發現。
然而,馬丁內斯告誡說,人造光可能會破壞晝夜節律,從而對疾病的易感性產生不可預測的影響。為了探究可能的影響,她將與其他研究人員分別在紐約和新澤西的城市與農村地區進行了一項研究:在樹木和電線桿上安裝光傳感器,并為參與者配備監測光線暴露和體溫的設備。
道威爾在其2001年的論文中建議,“自然實驗”還可以洞察影響疾病季節性的因素。來自南北半球、各自適應不同季節的人們在鉆石公主號游輪上相遇,他們一起遇到了相同的病原體,并共同待了兩周——研究人員其實可以通過這群人分析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有著不同的感染率問題。
馬丁內斯認為,無論這一分析的結果如何,它們最終都可能帶來重要的公共衛生益處。她說道:“如果我們知道如何最好地應用疫苗,尋找到自身免疫系統在一年或一天當中最佳狀態的時間,那將很有價值。”
她接著說道,全球COVID-19的緊急情況可能會引起更多這方面的關注,并利于得到更多科學發現。但目前,還沒有人知道濕度上升、白晝變長或某些尚未預料到的季節性因素是否會幫助我們——或者說,新冠大流行壓根就沒季節性可言。時間會告訴我們一切。
資料來源 newsf l as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