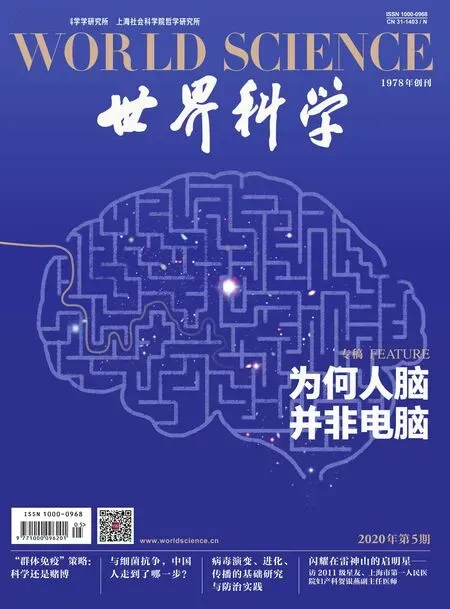病毒演變、進化、傳播的基礎研究與防治實踐
2020年3月27日,上海市科協(xié)舉辦的“病毒演變、進化、傳播的基礎研究與防治實踐(從SARS到COVID-19)”研討會在上海科學會堂召開。長期從事病毒研究和疫苗研發(fā)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一線的多位院士、知名專家參加了研討會,從多學科、多角度探討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與治療工作。這里選取部分專家的發(fā)言與讀者分享。

聞玉梅
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市微生物學會榮譽理事長
進一步加快疫苗研發(fā)步伐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疫苗被寄予了眾望,也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疫苗研發(fā)有幾個關鍵的要素:首先,是要有科學技術的支撐,包括現代微生物學、現代免疫學、流行病學、傳染病學等學科的知識儲備,各學科研究人員共同參與,協(xié)同合作;其次,要建立經呼吸道、消化道傳播并散播病原微生物的數種動物模型,探索一些新型動物模型的建立;再次,建立較為全面的檢測保護性免疫應答及自身免疫應答的實驗室指標,完成病原微生物免疫應答、保護性免疫應答等基礎工作;最后,疫苗的研發(fā)需要國際合作,事實上,我國的疫苗已經在與國際同行進行合作,如果能有一個連接全球科學家的平臺,那將會極大促進疫苗的研發(fā)。
目前的疫苗開發(fā)都是針對主動的特異性免疫,這種免疫一般只針對一種病原體,可以預防疾病,但是研發(fā)和實驗過程耗時長、資金投入大、風險高。那么,在感染源不明或是需要緊急預防的情況下,是否能研發(fā)出能夠刺激人體產生被動的非特異性免疫、具有通用特性的應急性疫苗呢?這樣的應急性疫苗或許有其特有的優(yōu)勢:不針對特定的細菌或病毒,因此可以提前生產準備,一旦發(fā)生疫情就可以直接上“戰(zhàn)場”,在短期內能夠應對大規(guī)模突發(fā)傳染病。
非特異性免疫是相對于特異性免疫而言,指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對外來病原微生物的免疫反應。這種免疫反應的特點是:不會針對某一種病毒或是細菌,而具有通用特性;其反應速度快,一旦發(fā)現外來入侵者,機體就會馬上啟動這一工作;在對抗入侵者的戰(zhàn)斗中,非特異性免疫反應始終存在,并保持著一定的強度。從生物進化角度看,非特異性免疫更加原始,而依賴免疫細胞產生抗體的特異性免疫,則更加精準、高效,也是進化樹上層的生命體才有的能力。
非特異性免疫是抗擊傳染病的第一道防線。以非特異性免疫作為理論基礎,我們可以研發(fā)一種通用的應急性疫苗。這種疫苗可以在短期內激發(fā)機體的非特異性免疫,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能迅速發(fā)揮保護作用,以此幫助人們更好地應對那些未知的病原體。
研制應急性疫苗,需要滿足幾個條件:一是不會引發(fā)自身免疫應答,避免出現“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情況;二是主要針對呼吸道、消化道的多種病原體,最好能促進黏膜免疫應答,并提高機體的系統(tǒng)免疫應答;三是制備成型的疫苗需性質穩(wěn)定,便于儲存與運送;四是疫苗可以經過口服或經黏膜吸入,如噴霧或滴鼻;五是價格低廉,可大規(guī)模制備和使用。未來研發(fā)需要考慮到這些方向,進一步建立應急疫苗體系。

盧洪洲
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
治療策略應與科研相結合
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作為新冠肺炎的定點醫(yī)院,擔負了上海市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收治的任務,是上海應對各類重大傳染病的“主力軍”,也被譽為上海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后一道防線。
上海截至目前沒有出現疫情社區(qū)流行,沒有醫(yī)務人員感染,治愈率也很高,這體現了上海的總體水平。上海新冠肺炎的治療策略是有自己的優(yōu)勢的:首先是一人一策,提升了治愈率;二是呼吸科、重癥醫(yī)學、急診醫(yī)學、感染科、心理咨詢、中醫(yī)科等多學科專家坐鎮(zhèn)現場,聯(lián)合會診;三是科學、合理地用藥,客觀理性地使用激素;四是實時動態(tài)了解患者信息,隨時按需調整治療方案;五是上海式特殊護理,每2小時翻身拍背,輔助改善肺部墜積性肺炎。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疫情中,上海重癥病人的病死率也是非常低的。細胞因子風暴通常被認為是新冠肺炎患者向重癥和危重癥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新冠病毒感染人體后,迅速激活病原性T細胞,大量產生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和白介素-6等因子,從而形成炎癥風暴,導致患者嚴重的肺部和其他器官免疫損傷,病情在短時間內急劇惡化,最終導致低血壓、凝血障礙、心肺肝腎等重要器官功能衰竭,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危及生命。
應對細胞因子風暴的關鍵是早發(fā)現、早治療。為此,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在輕癥患者病房專門安排了一組專家,監(jiān)測患者的肺部影像學變化、呼吸功能變化及實驗室指標變化。一旦患者指標出現波動,立馬從輕癥病房轉到重癥監(jiān)護室,抑制細胞因子風暴,并通過藥物、氧療阻止重癥化。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自2月9日起就開展了常規(guī)“細胞因子”檢測,以協(xié)助診斷和治療。
有效的防控治療手段也需要與科研進一步結合。在疫情初期,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復旦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張永振教授團隊第一時間把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全基因序列測出來,并在線發(fā)表在《自然》上。團隊獲得的新型冠狀病毒全基因序列是全球最早公布的,對之后全球的防疫和研究工作意義重大。
我們團隊在《中華醫(yī)學雜志》英文版上發(fā)表了“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康復患者的病毒RNA持續(xù)及清除時間研究”。研究認為,與咽拭子相比,新冠肺炎患者糞便中病毒RNA清除延遲,因此,迫切需要對新冠肺炎患者的糞便運輸進行標準化以降低風險;另一方面,新冠肺炎患者應定期進行糞便病毒RNA檢測,即使在康復期也應如此。不過,由于患者尿液或血液的低陽性率,通過這種途徑傳播的可能性很小。
科研最終的目的是服務于臨床,治療患者仍然是第一要務。因此,在研究的基礎上,我們認識到由于新冠患者在咽拭子核酸檢測轉陰后,其糞便中仍可以持續(xù)排毒,我們進一步加強了糞便管理,警惕消化道傳播,同時將患者糞便核酸檢測納入患者日常管理及解除隔離的標準中。目前看來,采取這個方法和標準確實是有價值的。同時,基于皮質類固醇治療會延長患者氣道和消化道病毒清除時間的研究發(fā)現,在治療過程中我們不建議對輕癥患者使用,重癥患者也應慎用。
為了更好地保護醫(yī)務人員,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除了對負壓病房進行清潔區(qū)、緩沖區(qū)、限制區(qū)三區(qū)劃分外,還讓要進入病房的醫(yī)務人員霧化吸入干擾素卡帕,到目前為止,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醫(yī)護人員零感染。
如今,上海與和世界衛(wèi)生組織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每個星期都有電視和電話會議、采訪及相應的討論,我們也希望好的診療和防控經驗得到進一步推廣。

張文宏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yī)院感染科主任、新冠肺炎上海醫(y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上海在本次疫情中交出了好答卷
上海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救治模式是先進的,即舉全市之力,把最優(yōu)秀的團隊、最好的資源集中到上海市公共衛(wèi)生臨床中心。我認為上海在本次疫情中交出了非常好的答卷。
從長遠來看,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難對付的病毒之一,因為在歷史上沒有一個病毒的特性這么詭異。埃博拉雖然兇險但是走不遠,停留在非洲;SARS癥狀重但傳播力不強;流感易暴發(fā)但癥狀很輕,可以置之不理;而新冠肺炎正好介于當中,傳播力極強,但是癥狀又不輕,它的狡猾之處還在于有無癥狀感染者。因此,這個病毒的防控難度可能會超出人類的估計。
目前,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經進入下半場,當前的防疫重點已從“內防擴散”轉向“外防輸入”,特別是一些無癥狀感染者,其可能成為潛在的傳播源。
無癥狀感染的特點是沒有臨床癥狀,病原學檢測卻呈陽性。無癥狀感染也意味著有相當多的人通過自己的免疫功能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毒,不像SARS那樣會引起重癥導致死亡,但無癥狀感染者仍具有傳染的可能。
對于無癥狀感染者,無法依靠體征篩查出來,那么為了降低社區(qū)傳播隱患,應在第一時間發(fā)現和鑒別,因此快速診斷體系的建立極為重要,這可能成為防止社區(qū)傳播的利器。
目前無癥狀感染者的發(fā)現主要是通過主動篩查:我們在篩查一些密切接觸者時發(fā)現病人攜帶病毒,但是沒有癥狀,而他攜帶病毒的延續(xù)時間會超過三個星期,這些人如果不去醫(yī)院就不會被發(fā)現;另外就是海外回來人員,如果他們不被檢測和隔離,或者就算進行了隔離,兩個星期內沒有癥狀,那么在隔離期結束后仍有可能造成極大的傳播風險。
上海從頭到尾采取的措施都是非常嚴格的。目前,上海對入境來滬人員實施100%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這一措施可以最大限度地篩查來自境外的無癥狀感染者;入境人員進滬后還要隔離兩個星期;此外,還有第三道防線——就是由上海市衛(wèi)健委組建的110多家發(fā)熱門診和180多家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中心發(fā)熱哨點門診,這個網絡大家通常看不見,但是卻很重要,因為在這個網絡下,如果有漏網之魚也會被篩查到,之后疾控中心會對篩查出來的病例進行追蹤。
至于疫情是否會反復,這可能取決于三大因素:一是疫情所在的國家和地區(qū)是不是會出現有出院病人肺炎復發(fā)甚至轉為慢性帶毒的情況;二是是否還有一些目前沒有發(fā)現的無癥狀感染者存在于人群當中;三是境外的輸入性風險。
我認為上海的防控體系是比較完善的,但是也不能保證將來永遠沒有病例,因為全世界的疫情沒有控制好,就不能100%保證一個病例都不會進來。我們要做的就是時刻做好準備,如果有病例進來也能在控制范圍之內。
回顧此次疫情防控救治工作,我們的醫(yī)院能夠第一時間發(fā)現病毒并鑒別出來,完成了基因測序,說明我國這方面的能力正在逐步提高;第二是上海的醫(yī)療診斷體系已經建好,這為防止社區(qū)暴發(fā)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鑒于上海的境外輸入壓力,下一步的工作重點仍是抓診斷和治療,構筑上海防控救治的“銅墻鐵壁”。
這次疫情的最終消除還是要依靠科技支撐。如果沒有科技支撐,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臨床醫(yī)生可能會忙忙碌碌,永無停歇,因為隨時會有無癥狀的病人造成社區(qū)傳播和流行。我們不希望一直做“救火隊員”,只有科學家團隊開展密切的合作,在科技支撐下形成精準的防控體系,才能掌握主動權,徹底控制住疫情。

趙國屏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tài)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市微生物學會榮譽理事長
未來的醫(yī)學研究需有機整合資源
SARS病毒從動物傳到人以及人傳人過程中,關鍵位點發(fā)生了變化,感染力也發(fā)生了變化,但新冠病毒的感染能力一直很強,其關鍵位點也沒有發(fā)生大的突變。按現有數據來看,新冠病毒的突變速率要比SARS病毒慢了一個數量級。從這個角度看,新冠病毒早已變得非常適應人體細胞環(huán)境,可以說是適應性突變后期的病毒。
從長期開展病毒基礎研究的經驗來看,病毒研究通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了解病毒是什么,這屬于分類;第二個階段是了解病毒怎么進化和演化,這屬于進化;第三個階段是了解病毒在環(huán)境中的生存狀態(tài),也就是生態(tài)環(huán)境。
我國的傳染病防控體系,包括臨床醫(yī)學研究、基礎醫(yī)學研究和預防醫(yī)學研究,病毒研究的分類、進化和環(huán)境三個階段可以分別對應臨床醫(yī)學、基礎醫(yī)學和預防醫(yī)學。其中,臨床醫(yī)學的研究對象是病原微生物,涉及病理學、生理學、循證醫(yī)學等;基礎醫(yī)學的研究對象是細胞、核酸,涉及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等;預防醫(y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群,涉及病原生理學、遺傳學等。這三者相互結合,構成了傳染病防控、治療和研究的三角體系。
目前,我國的預防醫(yī)學研究、基礎醫(yī)學研究和臨床醫(yī)學研究還沒有有機地整合起來。無論是實時、系統(tǒng)、前沿的流行病學研究,還是以臨床數據樣本為基礎,采用現代基礎醫(yī)學手段開展的研究,都還略顯不足。只有將科研隊伍與疾控隊伍、臨床隊伍在平時就組織成團隊或形成協(xié)同的體系,并且把日常臨床中常見的一次次“非典”當作一次次演練來開展三方協(xié)同的研究與實踐,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現時,臨危不亂、胸有成竹地開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及相關的研究工作,并且一步一步地把我們的科研治療水平不斷推到新的高度。

寧 光
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瑞金醫(yī)院院長
防控經驗有效輸出,藥物研究有進展
隨著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中國的經驗與方案正在加快輸出,與世界各國專家分享。例如,細胞因子風暴是我國醫(yī)學專家率先發(fā)現的,這會導致病情突然加重,很難搶救。經過臨床醫(yī)生和科研人員的合作探索,發(fā)現了一種單抗藥物在救治這類患者時有較好療效。目前,單抗藥物和康復者血漿聯(lián)合使用,已成為意大利、伊朗醫(yī)生救治重癥患者的主流方案。而伊朗按照中國專家推薦的方法,防控明顯得到改善,僅用一周時間就迎來了拐點,其重癥病人也開始減少。
可以說,我國的疫情防控救治工作為全球抗疫提供了寶貴經驗,未來也可能成為傳染病防治的經典案例。
不過,目前仍然沒有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但羥氯喹被認為是有效的藥物。《上海市2019冠狀病毒病綜合救治專家共識》里曾明確指出:羥氯喹在臨床上應用起到了比較好的臨床效果,推薦使用。不過,要想證明一個藥物對新冠肺炎有效,僅僅憑體外實驗的抗病毒效果還遠遠不夠。即使是已經上市的老藥,也需要經過臨床實驗,等待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試驗結果。
在市科委支持下,由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瑞金醫(yī)院牽頭的一項“硫酸羥氯喹治療新冠肺炎(COVID-19)的隨機、對照、開放的多中心研究”于2020年2月15日正式注冊臨床。這項新冠肺炎研究被列入國家應急科技攻關專項。
在1個月時間里,瑞金醫(yī)院基本完成了羥氯喹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研究。研究表明,羥氯喹不能起到預防的作用,也不能起到使病毒轉陰的作用,該藥主要能發(fā)揮作用的時間段是在疾病的中后期。在病程的4~12天,病人癥狀明顯減輕,體內淋巴細胞數量明顯增加,C-反應蛋白明顯減少,在阻止患者從中期向危重癥轉變方面效果很好。對于羥氯喹無法有效使患者轉陰的問題,可能是因為新冠肺炎患者的自然轉陰率約50%,所以通過藥物導致的有效轉陰,比較難觀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