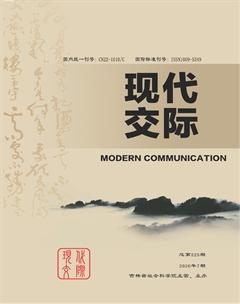人工智能的民事法律主體地位問題研究
吳宇琪 王黎
摘要: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人與人的差別越來越小,但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具有法律主體資格仍存在較大爭議。人工智能的本質是數據輸入且具有預先設定好的程序的機器體,但它通過模擬人腦的神經單元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自主地通過自己的意志作出行為,因此具有意思能力。同時,為了順應大數據時代的高速發展和強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賦予人工智能以責任能力也是大勢所趨,基于此,可以基本確定人工智能應當被認定為具有法律主體地位。
關鍵詞:人工智能 意思能力 責任能力 法律主體地位
中圖分類號:D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7-0049-02
當人工智能這一概念于1956年被正式提出后,相關研究方興未艾。法學界對人工智能的爭議點不僅在于知識產權方面,民事主體法律資格的確定與否也一直是爭議的焦點。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人擁有越來越強大的智能,機器人與人的差別會越來越小。有科學家提出未來十年左右人工智能的智商甚至會超過人類。在民法理論中,主體是人,客體是物,主客體之間有著根本的區別,這是民法體系中的基本理論,而人工智能的出現打破了主客體之間的鴻溝[1]。現代法律制度只承認兩種主體:自然人和法人。顯然人工智能均不屬于其中任何一種,那么,人工智能作為一個特殊的主體,到底是不是“法律上的人”,能不能成為法律主體,這是現代法律面臨的現實問題[2]。
一、人工智能主體地位的爭議
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日趨完善,但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具有法律主體資格仍存在較大爭議,否定的觀點在于兩個基本理論——道德權利和私有財產。道德能力是個體基于一定的對錯觀念作出的道德判斷的能力,許多哲學家認為,具有道德權利的主體要同時具備推理能力和形成自利判斷的理性。基于此,否定觀點持有者認為,人工智能的行為規則和行為的作出完全受制于輸入程序和數據的人,因此,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上的主體必須具有的自主意識。同時,人工智能不具備承擔處罰的必要性,人工智能產品在數據的控制下被動地作出行為,實質上是沒有自己的主觀意識的,因此,對其進行處罰的威懾功能也無法實現。人工智能學習的基礎仍然是最初的程序植入,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會有后面更高級的能力,比如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或者說人工智能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可以預知的,那么,其受震懾的程度就無法達到效果[3]。而有些學者認為應當賦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這與有限人格說有相似之處,都是主張要將人工智能產品運用法律的手段賦予其擬制人格。借鑒法人制度賦予人工智能產品有限的民事行為能力,這樣做有利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和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同時,對于人工智能產品在侵權問題上的責任承擔,則涉及民法理論中的獨立財產問題。由于人工智能的特殊性,當出現民事責任時,研發者、制造者和使用者多個主體都有可能對其負責。民法中將法人作為擬制主體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擁有獨立財產。民事主體資格的獲得,對于人工智能和其生成物在法律上的定性十分重要,具有意思能力和行為能力是具有民事主體資格的實質條件,而是否具有生物意義上的人的屬性,并不影響民事主體資格的認定。
二、對質疑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主體地位的反駁
有觀點認為人工智能歸根結底仍屬于“擬制人”,屬于機器體,是通過深度學習能力和模擬神經網絡的程序和數據才具有人的屬性,因此,在此情況下,我們是否也應賦予人工智能與人類權利平等、相同的權利。如果人工智能擁有與人類平等的人權,那就會存在人工智能也同時擁有如婚姻權等身份性權利,這樣就會出現有違倫理的問題[4]。對于現階段的人工智能而言,它仍相當于一件商品,沒有直接道德權利,因此,只能借助于人類之間達成的協議以獲得間接的道德權利。由此來看,現今人權理論對于人工智能的保護是極其脆弱和有限的。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等社會發展到強人工智能時代時,人工智能可以達到直接實現自身權利的堅守,那么,現在對人工智能人權的否認無疑會落后于技術的發展進程[5]。同時,有人質疑,人工智能無法擺脫物的屬性。從本質上看,人工智能屬于機器設備,不具有生物意義上的人的屬性。雖然人工智能具有邏輯能力和自主選擇能力,但都是完全受制于人類預先設定的程序和數據的,都無法擺脫人而存在。人工智能通過人規定的自主性標準而進入到社會中這顯然表明人工智能并沒有擺脫物的屬性。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生物意義上的人早就不再是認定具有法律主體資格的要件。民法上規定作為自然人集合體的法人作為擬制主體,雖不具備生物意義上的人的條件,但是仍賦予其法律主體地位。因此,人工智能即使始終具有物的屬性,也并不影響其法律主體資格。
三、人工智能可以獲得民事主體資格
1.人工智能具有意思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地作出意思表示,這一點與動物不同,它具有理性能力和自主性。意思能力可以進一步細化分為認知能力和意識能力,認知能力是人工智能獲得民事主體法律資格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工智能的本質是數據輸入且具有預先設定好的程序的機器體,通過預先的數據和程序,人工智能在對應事件反應時,只能被動地服從設定者預定的設定。因此,人工智能在程序的指令下可以作出有意向的判斷,此時的意向來自于預先設定的程序的指引,人工智能雖然所有的行為來自程序的指引,但是選擇何種程序和數據這是完全依靠人工智能的自我選擇,人工智能在自我意識的指導下選擇適合的模式作出回答,因此人工智能是具有認知能力的。傳統人工智能系統的設計與實現思路是從待解決的問題數據的特點與問題目標的解決出發,從計算的視角出發,這就使人工智能的程序只適用于解決某一特定的問題。而類腦智能研究的目標是實現通用系統,這就是要設計一套程序模擬如何通過同一系統實現不同的認知能力。在未來認知腦計算模型的研究中,需要基于多尺度腦神經系統數據分析結果,對信息處理系統進行程序設計,構建出類腦的神經網絡模型,從不同角度模擬腦的多模態感知、自主學習與記憶能力[6]。人工智能的意志能力的認定原則是當其本身至少能夠適度擺脫固有算法的束縛而形成一定程度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創造力[7]。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深度學習產生自主意識和意志,并在自主意志的支配下實施民事行為,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其實是一種無監督開放式的學習模式,因此說本質上仍是一種算法,人工智能作出的任何一個行為都是通過數理計算,模擬人腦的神經單元,自主地進行思考、選擇、認知運動,人工智能通過自己的意志作出行為,就應當為此承擔責任。就目前人工智能發展的階段而言,現在仍處于弱人工智能時代,弱人工智能時代的人工智能產品依托于一定的程序設計,僅在一定領域或特定領域發揮功能。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定程度和特定領域內作出決策,但是并不意味完全具備完全的民事責任能力,因此僅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8]。人工智能的意思能力僅限于有限范圍內,在處分財產參與訴訟的方面,還是應由其所有人代為行使權利,類似于民法上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但并不影響其民事法律主體的資格[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