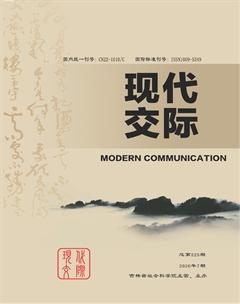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中的滿漢融合
許瑞
摘要: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一直是清代薩滿祭祀研究的重點。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本是滿族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在經過較長時間的發展、演變并在和漢族進行了較長時間接觸后,融入了部分漢族文化元素,其中所反映的滿漢文化融合現象,對于研究清前期滿漢文化的融合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采用實證史學的研究方法,探究清前期宮廷的薩滿祭祀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與漢族文化元素的結合及其發展演變。
關鍵詞:清前期 宮廷 薩滿祭祀 滿漢融合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7-0087-02
滿人素來崇信薩滿,清宮薩滿祭祀儀式由來已久,自成風格。1644年滿族入關后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同時,其民俗漸為漢風所染,祭祀亦呈現滿漢融合現象,逐漸體現出滿漢交融的多元文化風格。
清代宮廷薩滿祭祀一向是薩滿祭祀的研究熱點,白洪希的《清宮堂子祭探賾》對清代宮堂子祭進行了詳盡考析,杜家驥的《從清代的宮中祭祀和堂子祭祀看薩滿教》則對清代薩滿教的某些發展變化進行了探討。本文以實證主義手法對清前期宮廷薩滿祭儀中的滿漢融合現象進行探究,以期進一步了解祭儀中的滿漢融合現象。
一、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的發展趨勢
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始于入關前,后金定都盛京時就有了堂子和清寧宮“特殊祀典”的雛形。而薩滿祭祀作為滿族傳統文化與信仰的體現在入關后延續下來,并不斷演化發展。清宮薩滿祭祀初時雖與仕宦、民間薩滿祭祀有異,卻是因“各處之山川水土不同,所以各處之風俗言語亦各異。昔我滿洲姓氏。因其居處之地各異。是以祭家祖宗神,各處有各處之例,一姓有一姓之例”[1]9,是地區間風俗不同和各族各姓間的差異導致的。但在與漢文化的融合碰撞中,宮廷的薩滿教開始明顯區別于民間薩滿祭祀,清乾隆十二年清朝頒布了滿文本《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對清代皇室薩滿祭祀禮儀進行了系統的規范,將清宮薩滿祭祀法典化、廟堂化。頒布滿文本《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目的在于規范神辭,確保神辭準確無誤,以收“滿洲享祀遺風永遠遵行弗墜”之效,深受漢文化影響的乾隆帝,出于政治目的,于滿文本《典禮》外,又制漢文本并納入《四庫全書》,將滿洲傳統信仰提高到與漢族祭祀古禮等同的位置,從而借此展現和強化滿族文化的主體和正統地位。
二、祭祀神祗中的滿漢融合
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的滿漢文化交融首先反映在祭祀的神祗上,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供奉祭祀之神祗主要有掇哈占爺(軍神)、穆哩穆哩罕(狩獵神)、恩都力僧固(刺猬神)、佛陀媽媽(降福送子女神)、歪利媽媽(婦女保護神)、烏忻貝勒(農神)、安春阿雅喇(完顏氏祖先神)等,此皆傳統滿族神祗,但此外還增設漢族神祗如關圣帝君,在清宮各大祭祀中多供奉此神,祭辭中也多有反映。如在祭馬神儀式的朝祭灌酒于豬耳禱辭中的“上天之子,三軍之帥,關圣帝君。某年生小子(為某人祭則呼某人本生年)今為牧群繁息,敬獻粢盛,嘉悅以享兮”[2]141 ,以及每歲春夏秋冬四季獻神祝辭的朝祭神前祝辭中“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圣帝君……”[2]87 等這些祭辭中均提到關圣帝君,將其與滿族傳統神祗一起列入日常和重大薩滿祭祀中并祀,足見對關圣帝君的崇尚重視,亦可看出漢文化對清宮薩滿祭祀的影響及滿漢文化的交融。
三、祭辭中反映的滿漢融合
滿漢融合在清前期宮廷薩滿祭辭中也有所體現,清宮薩滿祭辭嚴格遵守薩滿祭祀規定,嚴謹規范,祭辭傳習需口耳相傳,心領神會,祭祀中誦讀祭辭時用老清語(滿語)誦讀,務求字音無誤,在這方面清宮祭祀延續了傳統薩滿祭祀以祭辭為重的特點,保留了滿族特色。在清朝統治者刻意保持下,滿洲傳統習俗一直傳承下來,但仍在某種程度打上了漢文化烙印。因為滿族薩滿祭祀祭辭為滿文,且必須以滿語誦讀,所以并未受到直接影響。然乾隆帝為了強調滿洲文化正統地位,于滿文本外,又編漢譯本《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漢譯本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在翻譯的過程中,語言精心雕飾,辭藻華美,一改滿族薩滿祭辭原有的活潑生動、淺顯易懂的語言風格。滿洲薩滿祭辭其格式亦不固定,不拘一格,但在經過乾隆朝這次規范調整后則顯得頗為僵化,僅舉其中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辭為例: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軍之帥,關圣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為某人祭則呼某人本生年)。今敬祝者。
豐于首而仔于肩,衛于后而護于前
畀以嘉祥兮,齒其兒而發于黃兮
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
神兮貺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2]329
從中明顯感受出漢文化思維和寫作風格,與原有的樸素活潑的風格相去甚遠,滿族祭辭本為敬神祈福,語言不事雕琢,務求表情達意,但宮廷薩滿祭祀的漢文本祭辭卻融入了漢族宗法祭祀的傳統特征,而且在漢文本祭辭中不僅體現出滿族對祖宗神的信仰崇拜,其中還糅合了漢族傳統的敬天法祖思想,將漢族宗法祭祀肅穆規整的氛圍也帶入其中。祭辭的嚴謹是滿漢祭祀的共同特點,但滿族著重強調偏重于誦讀祭辭務必準確,不要混淆發音,防止誦讀有誤,褻瀆神靈,以致不測,而漢族宗法祭祀祭辭則注重于言辭規范,誦讀時有韻律之美,兼具古風,以求追慕古賢。因此可以看出,滿漢于祭辭上原來確有不同,隨著歷史的發展推動清宮薩滿神辭融入了一些漢文化特色,滿族傳統的崇尚祖宗神的信仰與儒家文化的敬天法祖觀念也漸生交集,這是基于兩個民族文化和思想上敬奉祖先的基礎,在漢儒文化與滿文化的接觸中也加深了對清宮薩滿祭祀的影響。
四、祭祀細節上體現的滿漢融合
從祭祀細節上來看,清代宮廷薩滿祭祀在根本上與民間大體一致,同樣包括打糕祭、背燈祭、院祭、換鎖,等等,但是與傳統薩滿祭祀儀式相比,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已經走得更遠。清代自后金以來吸收漢族文化思想,等級觀念愈發強烈,為彰顯獨尊地位,強化等級區分,宮廷著力于模仿漢族廟堂文化。富育光、孟惠英的《滿族薩滿教研究》提到民間流行的“普遍流行的常例祭是春秋大祭,其中主要是巴音波羅里(即秋祭)……滿族的秋祭一般為三天,過去富有之家有五天、七天不等”[3]69。具體時間由祭祀之家掌握,并未嚴格規定。《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則指出“天子則日祭祀,王等則月祭祀,至于士大夫官宦則春夏秋冬四時祭祀……”[1]8。從兩段材料的對比可以看出,傳統滿洲民間祭祀祭期并未詳盡規定,只是一個大概日期,而第二段材料則體現滿族薩滿祭祀的祭期受到漢文化影響,融入了漢文化古禮祭祀的因素,有著較為明顯的漢族等級觀。而《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則規定更為詳盡,何種祭祀、擇何吉日清清楚楚,頗有漢族擇定良辰吉日之意。
這里以堂子立桿大祭儀注為例,探究清宮薩滿祭祀中的滿漢融合。“每歲春秋二季,堂子立桿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桿,前期一月,派副管領一員,帶領領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慶州,會同地方官,于潔凈山內,砍取松樹一株,長二丈,圍徑五寸,樹梢留枝葉九節,余皆削去制為神桿,用黃布袱包裹赍至堂子內,暫于近南墻所設之紅漆木架中間斜倚安置,立桿大祭前期一人,立桿于亭式殿前中間石上。祭期預于饗殿中間,將鑲紅片金黃緞神幔用黃線繩穿系,其上懸掛東西山墻所釘之鐵環。”[2]101這是典型的滿洲薩滿祭祀準備工作,即準備堂子立桿祭所用之“索倫桿”,首先選擇圣潔之山,其次選材嚴格,尺寸材質皆有嚴格要求,以明奉神之誠,但也有所不同。以伊爾根覺羅氏為例。“祭祀前一日下午,令人入山或野外潔凈之處,伐楊樹一株,曰三寸許即妥,荷至院內,令人修理,其桿系圓形,上尖下粗,修理人不得跨坐,得凈手修理,畢,樹于房門左邊,所刨下之木及樹枝皮,收至一堆,俟送舊桿之時,一同送出,其桿名,滿語叫蓑龍桿,桿長九尺余。”[3]76清宮立桿祭沿用滿族舊俗,細節卻有所不同,清宮索倫桿長二丈,與傳統的九尺之長不符,然其留枝葉九節亦為符合傳統之意。而清宮立桿祭較之于滿族的傳統薩滿祭祀選材更為嚴苛,動用人員眾多,不僅是展現虔誠供奉神明之意,亦在展現皇家氣度,有著明顯的漢族等級制色彩。
“屆時,衣金黃緞衣內監八人,舁黃緞神輿,進內左門,近光左門、景和門,預備于坤寧宮門外,衣黃緞衣司俎滿洲二人,恭請佛亭,并貯菩薩像黃漆木筒,貯關帝神像紅漆木筒安奉輿內,衣金黃緞衣內監八人舁行,由宮殿正門出。前引仗二對,羊角燈二對,亦用衣金黃緞衣內監執之”。[2]101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在祭祀中以崇高禮儀迎奉神祗,然傳統滿族恭迎神祗不過于院中西屋恭迎祖神至祭祀之室,而宮中雖大,亦無須如此盛大依仗輾轉數處,這樣的行動只能解釋為為彰顯皇室氣派,區別等級,以示與士庶祭祀決然不同,而這也與薩滿祭祀的樸素、活潑之意相去甚遠,反而與漢族傳統的祭祀大典注重儀式典制、以示恭謹相似。
五、結語
從發展趨勢、供奉神祗,祭祀祭辭還有祭祀細節等層面上來分析,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儀式在統治者的主觀影響和傳統信仰遺留方面,在保留了滿族傳統薩滿祭祀的特點和精髓的同時,也受到漢文化觀念的深遠影響。無論是敬天法祖的宗法思想,還是森嚴有序的等級觀念,都為清前期宮廷薩滿祭祀打上了某些漢文化烙印,促進了滿漢文化的融合,也為滿漢文化的思想寶庫留下一筆寶貴的財富。
參考文獻:
[1]鄂爾泰.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 [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2]劉厚生.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3]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4]孟慧英.中國北方民族薩滿教[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張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