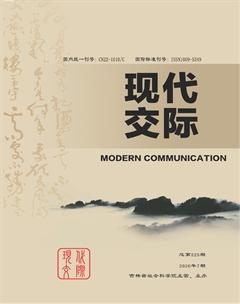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三種文化面相
申麗娟
摘要:中國近代以來歷經多次歷史轉折,無不伴隨著一場乃至數場文化變革。回觀整個20世紀,“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化變革集中表現為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三種文化面相,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融合所帶來的文化效應。如果說傳統文化面對外來知識和信仰的挑戰,努力開出現代之花,是中國現代變革之根本,那么,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主導了中國近現代革命與建設,為中國現代變革提供了方向;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大眾文化作為雙刃劍,則為中國現代變革注入文化活力。這些文化要素匯集在一起,構成改革開放得以實施和推進的重要文化動因。
關鍵詞:中國 20世紀 現代化 文化面相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7-0239-02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取得的豐碩成果為今日世界政治經濟發展框架打上了“中國標簽”,作為其成果展示的不僅是物質技術層面上的突飛猛進,還有社會制度“摸著石頭過河”的累年經驗,更是文化觀念上前所未有的碰撞與融合。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積聚起來的經驗和教訓追根究底源于對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重梳與再建。從文化的視角觀之,這40多年的發展與近代中國孵化于“外源型”的現代化道路保持了某些家族相似性,甚至可以說,相比于一百多年的那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集體努力,今日中國所面對的更是近現代中國在探索現代化強國百年道路上的一次文化大匯演。因此,回溯中國在整個現代化探索道路上先后發生的文化路徑選擇,梳理中國20世紀現代化進程中的三個文化面相,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當下中國社會文化之多元樣貌的歷史由來。
一、被西方宗教和軍事勢力解構的傳統文化
西方作為現代化的始源地,創造了處于優位的現代文明,科學與技術的聯盟改變了西方中世紀的軍事落后面貌,逐漸樹立起西方文化之于他者文化的支配地位[1],并依次借助于宗教、軍事、經濟等力量向近代中國推行其文化價值觀。西方的基督教信仰首先充當了近代西學傳播的最初載體,向中國輸出了大量傳教士,分別在明末清初和晚清出現兩次來華高潮。信仰輸出是西方文化輸出的第一選擇,基督教面向中國的信仰同化實為西方列國勢力擴張作背書。
因此,早期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很快就遭到了清政府的禁絕,為了應對清政府禁教政策和視其為“蠻夷”的“偏見”,新教傳教士采用了迂回的策略,開始轉向一些世俗事務,開展了諸如醫務、報刊、教育和作書譯著等活動[2]。這些傳教士都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如李提摩太就是神學博士,花之安是漢學家、植物學家,他們興辦了如武昌文華書院、山東廣文大學等教會學校,與中方合辦了上海格致書院,譯介、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和法律著作,為中國改變科技“末學”的地位和開眼看世界作了早期啟蒙,“我大清得天下之正”的封閉自傲的心態在地理事實面前逐漸被更改。這些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中國大學的籌建,開創了中國現代大學之建制,丁韙良擔任了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赫士被袁世凱聘為山東大學堂總教習,李提摩太則用中國政府的庚子賠款創辦了山西大學[3]。他們另一項突出的貢獻就是對新式女子的倡導。傳教士在1833年至19世紀末創辦了逾百種報刊,在編輯、出版體例、印刷技術等方面為近代中國進步思想的宣傳、女性報刊的興起作了技術準備,在內容上則直接譴責了中國的惡俗陋習如纏足,傳教士秀耀春、卜舫濟等相繼發文痛陳纏足的罪惡,并分別在廈門、上海等地成立了“天足會”,推進反纏足運動。同時興辦女學,開風氣之先,實行男女合校制度,推行女子教育、體育與醫學,中國及世界第一所婦女圣經學校是1873年成立于汕頭的明道婦女學校,隨后擴展至全國。這些學校雖然數量上遠遠少于男校,就學的女性比例也很小,卻對中國女性的現代轉型具有前所未有的革新意義。女性新形象也日益為改良派、革命派所接受,意欲破除中國舊式傳統一以貫之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倫理制度之沉疴,此后“五四運動”“新生活運動”的主張中都可見其革新遺產。
信仰灌輸帶來的新思想傳播催生了近代中國救亡圖存、要求獨立與民主的實踐,主動要求思想進步和推進近代中國社會制度的革命,加速了中國固有傳統文化的現代裂變。傳統文化在被西方枷裹軍事強權的信仰“入侵”中得到整改,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塑造現代公民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文化資源。
二、主導中國近現代革命與建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
辛亥革命后接連出現的復辟鬧劇說明中國皇權治統的根深蒂固,袁世凱為增加復辟的合法性,搬出了儒家政治的德性精神,這直接引發了1915年以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為始端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五四”時期達到高潮。如此,近代中國以對自身文化的決絕方式去迎接“現代性”為標識的新型文化。但是,打倒了自身的傳統文化,學習西方的政治實踐又宣告失敗,中國急需一個全新的思想體系來指導究竟“往何處去”的近代實踐。此時進步人士經由嚴復《天演論》的譯介工作,逐漸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思想,馬克思主義也強調社會進化論,突出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必然性,加之中國北鄰的蘇俄剛剛爆發十月革命,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這些因素匯流在一起,使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內迫切引入與學習的政治資源。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后,很快轉換了中國革命的主體,并與中國自下而上的改造路線相配合,得到迅速發展。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考察雖然主要囿于西歐諸國,但也對亞洲國家的特殊情況產生濃厚興趣,主張落后國家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繼續向前發展的可能性。這對于此時正遭受資本主義列強肆虐的中國來說,不啻是一劑精神的良藥,它所支持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將之確立為革命和建設的主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革命文化和政治文化喚醒了處于社會下層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而要真正發動起他們的力量,解除階級壓迫,必須變革勞動生產方式和所有制。無論是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土地革命,還是建設時期力推的所有制改革,都使這些群體迅速成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主力軍。新興的中國共產黨在其社會實踐中忠實踐行了馬克思等革命家的設想,視“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積極將婦女融匯到革命與生產的斗爭中,新中國成立后,人們崇尚的“半邊天”精神是這種斗爭理論的又一彰顯。
馬克思主義作為引領中國社會主義風向的主流政治文化,始終存在與中國語境適恰的課題。蘇聯作為“社會主義早產兒”,將根植于西方語境的馬克思主義強行植入本民族文化,必然突出強調馬克思主義“官方學說”中的主觀能動性和階級斗爭,強化階級意識形態以凈化精神境界,最終導致了斯大林的血腥專政,戈爾巴喬夫的矯枉過正則直接斷送了蘇俄的社會主義前途。國內外一系列失敗的政治“案例”要求新中國主動尋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土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經典理論中國化的新釋與發展不斷更新著中國人對社會主義、全球化、市場經濟、資本等縈繞已久的這些問題的觀念,也推進了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改革。
三、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大眾文化
新時期西方文化的再次傳入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主要表現為大眾文化的流行。“文革”撥亂反正后,改革開放的政策加速了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進程,市場又是社會結構與文化的交匯之地,因此,中國市場的開辟必然連帶社會結構與民族文化的變遷,促使公眾的經濟、文化生活與政治相分離。90年代初期中國正式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眾文化由此興起,并在90年代中后期漸入佳境。
大眾文化作為與精英文化相對而言的文化形態,始源于西方,是在現代工業時代,科技推動文化經濟化、文化大眾化的一種文化結果,與市場經濟的出現和發展須臾不可分離。來自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曾對這一獨特而時興的文化現象總結了六點特征:現代性、商業性、世俗性、標準化、時效性和娛樂性[4],其突出的市場化和功利性使得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鮮明的區別開來,無論著眼于理論還是立足于現實來看,大眾文化對物質化身體消費的癡迷與精英文化對精神境界的至上追求的相容問題始終貫穿其中。為消弭這種隔閡和分歧,西方學者提出了“去分化”的文化樣式,利奧塔則用“文化折衷主義”表示雅俗文化之間的合流之勢。
落根于中國的大眾文化夾帶著西式文化特色,一方面,為中國的異質文化注入新的創新因素。通過雅俗之間表達形式與途徑的互換,精英文化借助大眾的傳播形式,大眾文化吸納精英的文化內核,推動文化教育大眾化、普及化,比如百家講壇,還有形形色色的各種以知識普及為己任的綜藝節目。這些形式極大范圍內地實現了科學知識的普及,有利于傳統文化的現代復蘇與再生;另一方面,大眾文化以其商業性、娛樂化挑戰著以往嚴肅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但同時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馬克思是對的”以綜藝形式拉近馬克思與中國當代青年的距離;歌曲“馬克思是個90后”則以時興的音樂元素表達了青年的馬克思觀;接地氣的“習大大”稱呼見諸報端、被國民津津樂道,馬克思主義一改長期呆板、嚴肅的傳播方式,以當代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形式走入普羅大眾心里,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生命力不息的再現,更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自信。
四、結語
大眾文化的社會效應猶如硬幣的一體兩面,人們過分沉溺于娛樂化的大眾文化消費,可能會強化隨市場競爭而來的道德虛無主義和價值無歸感,學界關于文化理想論與文化革命論的爭辯、文化世俗論與文化階層論的分歧也未曾中斷過。但是,我們不能把時代性的道德問題單純歸咎于某種文化形態的盛行,而應該看到,由單一文化壟斷走向多元文化共享,恰恰驗證了現代社會的寬容度,個體的平權意識進一步增強,社會對公民個體權利的尊重日趨規范化、細節化。就此而言,改革開放的大格局拓寬了大眾自由選擇與自我展示的空間,中國式大眾文化具有進步的政治意義。
參考文獻:
[1]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M].何兆武,李約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489.
[2]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年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3.
[3]蘇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國:序言[M].關志遠,關志英,何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3.
[4]鄒廣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6(2):46-53.
責任編輯: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