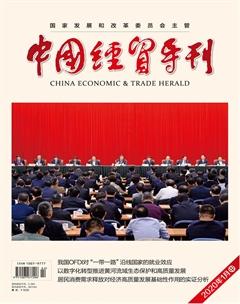制度、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
孫怡龍
摘要:從制度與企業家精神的基本概念出發,梳理了制度與企業家精神的相關文獻,進而上升到制度、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的層面,發現該層面的研究有著許多不足。例如文獻狹隘地將創業與初創企業和自營職業聯系起來、沒有將相關潛在因素理論模型化,并受到樣本局限性、遺漏變量問題、因果關系問題和異質性的影響。
關鍵詞:制度 企業家精神 經濟增長
企業家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Kirzner,1980),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企業家工作。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黨中央明確指出“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因此深刻理解企業家精神的多層次含義以及企業家精神對經濟的多層面影響就顯然尤為重要(Shep-herd,2011)。但是,現有的研究很少將企業家精神的淵源與企業家活動以及企業家精神的影響系統總結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Bjornskov和Foss,2008,2013;Holeombe,1998),究其原因主要是對企業家的決策行動進行深入調查是十分困難的,而由此引發的數據缺失使得學術研究很難進行。
經濟學家對企業家精神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興趣是近期才開始的。關于這一主題的文獻并不多,而且大部分是理論性的(Aghion和Howitt,1992;Wennekers和Thurik,1999)。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企業家精神研究,如社會學(Thornton,1999)、人類學(Oxfeld,1992)、政治學(McGahan,和Pitelis,2010)、經濟和商業史(Landes,Mokyr,和Baumol,2010)也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無論如何,從研究興趣來看,企業家精神與總體績效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僅限于經濟學。因此,我們的回顧和討論主要涉及經濟學。具體來說,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些現有的經驗研究,這些研究涉及企業家精神的制度驅動因素以及企業家精神的整體產出。
一、研究現狀
Audretsch和Aes(1994)以及Audretsch和Fritseh(1994)的研究首先探討了企業家精神與宏觀經濟狀況之間的關系。Audretsch和Acs(1994)使用初創企業指標作為企業家精神的代理變量,進而利用1976-1986年間西德地區的177個行業的初創企業的數據,主要涉及宏觀經濟增長率、失業和資金成本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初創企業受到宏觀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但是這兩項研究沒有涉及具體的制度或政策,也沒有評估創業活動的經濟影響。隨后又有一系列關于企業家精神和初創企業的特定特征的研究,這些研究更加明確了企業家精神與宏觀層面的因素相關(Freytag和Thurik,2007,Smith,和Reedy,2012)。
最早一批的關于制度和經濟政策影響企業家精神的研究是Kreft和Sobel(2005)以及Ovaska和Sobel(2005)的。Kreft和Sobel(2005)使用美國的州級層面數據發現較低的遺產稅率和較弱的勞動力市場管制促進了創業活動。Ovaska和Sobel(2005)使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分析了轉型國家的情況,他們發現較低的腐敗狀況以及穩健的貨幣政策會促進新企業的形成。因此,這些文獻的重點主要放在保護私有產權,而對于一些管制性措施,如,行業進入壁壘、資本管制等考慮較少。隨后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變得更加深刻而系統。Nystrom(2008)使用了23個OECD國家的面板數據來替代全球創業觀察的混合截面數據,進而重新檢驗了Bjornskov和Foss(2008)的研究,他們發現更小的政府組織,更好的法律結構與產權保護以及更少勞動、信用以及商業管制能夠提高自雇就業。此外,還有部分學者聚焦于非正式制度與企業家精神的關系。鄭馨等(2017)研究了社會規范與創業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規范對創業活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并且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更加明顯。
雖然實證研究探討了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對創業傾向的影響,但現階段關于研究企業家精神整體產出的文獻還較少。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如何衡量企業、地區或國家層面的生產力(Caselli,2005;Hulten 2001)。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研究只是簡單地將就業、生產率或創新效應視為既定因素,關注于如何培養企業家精神(Djankov等,2010)。Anokhin和Wineent(2012)是為數不多地進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他們對35個國家的全球創業觀察樣本數據進行了分析,研究影響企業家精神的大政方針的有效性。作者發現那些旨在促進創業活動的政策可能會誤入歧途。因為政策制定者無法在政策制定前預測到哪個初創企業會成功。因此這些大正方針很有可能幫助了現有的企業而非初創企業(Hayek,1948;Munger,2008)。此外,還有些文獻關注經濟的其他方面,如出口與對外貿易(Ezirim和Maclayton 2010)。
二、研究不足
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了許多進展,但距離理想狀態還很遠,這一點可以從學界一直沒有對企業家精神形成一個權威的定義即可看出。
(一)因變量問題
在學術界,關于企業家精神的定義,一直沒有一個權威的答案。在經濟學者看來,以熊彼得為代表的德國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強調的是創新能力;而受到Mises(1951)和Kirzner(1973)等奧地利學派的啟發,管理學學者傾向于強調機會的發現能力;而以以奈特(Knight,1921)和舒爾茨(Schultz,1980)為代表的奈特主義者則側重于強調企業家的風險承受能力以及應對市場不確定性的能力。因此,基于這些不同的概念,度量方法將有很大的不同,進而導致因變量不同。
(二)自變量問題
在自變量方面,經濟產出可以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來衡量,例如,就業增長、生產率提高等,具體選取哪種指標則取決于研究興趣和數據可得性(Arzeni,1997)。在勞動經濟學、貿易研究和產業經濟學領域,存在著大規模的公司級和行業級數據集,并已被經濟學家和管理學者廣泛使用。然而,在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中使用這些數據仍處于起步階段,因為新公司往往只是在一段時間后才輸入數據庫。
(三)因果識別問題
經驗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是如何識別因果關系。例如,企業家精神可能既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又是結果。事實上,Audretsch和Acs(1994)認為企業家精神對經濟增長的反應是正向的。此外,正如理論工作所強調的那樣(Aghion和Howitt,1992;Schumpeter,1911),企業家精神對經濟增長有著積極的影響(功cmskov和Foss,2012;KoeHinger和Thurik,2012)。互為因果關系這個矛盾也出現在制度與企業家精神之間。
(四)遺漏變量與異質性問題
和其他眾多領域的研究相似,關于企業家精神的研究也沒有對最基本的模型達成共識。因此,在經驗研究中經常會出現遺漏變量的問題。
異質性同樣也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現有的研究大多基于一個假設前提下,即無論在何種制度、文化環境中,企業家精神對其的反應是同質的。然而現實情況下這一假設并非合理。此外,制度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可能會使得估計結果產生偏差,尤其是將非正式制度考慮在內。
(五)數據缺失問題
最后一個值得關注的是數據缺失問題。近幾年,數據的可得性得到較快的改進,但是對于研究企業家精神所需的初創企業、企業增長等數據,現有的抽樣調查方法可能并不合理。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抽樣調查很難獲得那些剛剛成立以及業務規模十分小的初創企業。因此,為了獲得較為合理的數據,對各類初創企業進行跟蹤調查就顯得十分必要。
三、總結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對制度、企業家精神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一個系統性的梳理,從而找出現有研究的困境與不足,進而能夠更加深刻的理解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盡管上面提到了幾個不足,但是關于企業家精神、制度和經濟增長的文獻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進展。首先,有大量的證據支持企業家精神在經濟增長方面的積極意義。其次,制度提高了企業家行為的整體水平,也可能將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生產性而非非生產性的方向。但是,究竟哪些制度因素對產生這些有益后果更為重要,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我們對這一領域的進展感到樂觀,因為高質量的數據越來越多,各學科交叉融合也越來越普遍,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這一問題能夠獲得更多高水平學者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