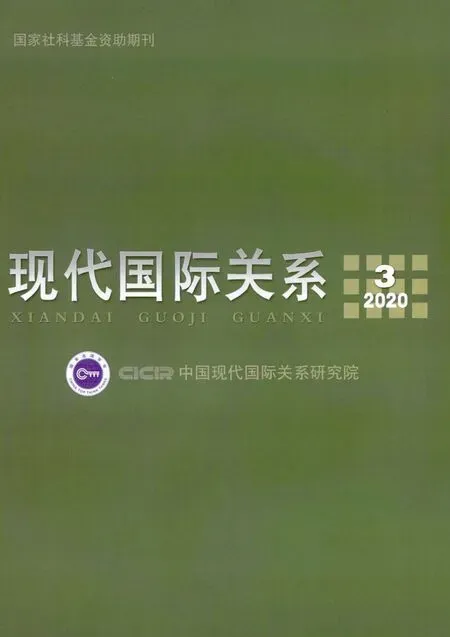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進展及問題
楊天宇
[內容提要]目前,美國股市接連發生熔斷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金融黑天鵝事件給國際金融穩定帶來了巨大挑戰。為應對全球金融風險,推進國際金融機制變革就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關切。近年來中國推動國際金融機制變革取得了一系列積極進展,包括推動金融穩定理事會完善全球金融監管框架;促進世界銀行批準新的增資和份額改革方案;落實新開發銀行擴員計劃;擴寬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在全球金融治理的合作新領域;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但是,美國金融霸權施加的結構性壓力、西方國家對于新機制運營政策標準的質疑和新機制的金融公共物品供給能力較弱等問題也是中國面臨的主要現實挑戰。展望未來,中國應當在繼續促進世界銀行和IMF份額改革、完善新機制的政策標準和監察機制建設、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新理念落地化和發揮新機制在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上的增量改革效應等方面積極作為,從而有望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推向一個新的臺階。
進入2020年以來,全球金融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宏觀層面,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在1月份相繼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和《2020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對國際金融風險提出嚴重警告,指出在全球經濟增長已下跌至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的同時,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高昂的債務壓力和負利率政策已經將全球金融脆弱性風險推升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1)“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Slow Growth, Policy Growth,” A World Bank Group Flagship, January 2020;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 United Nation, New York, January, 2020.微觀層面,2019年年底的澳大利亞山火、2020年1月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和3月發生的美國股市熔斷及沙特原油的擴產降價等迅速演變成新的金融黑天鵝事件,其引發的蝴蝶效應給全球金融治理帶來了新的危機和風險。目前,這些全球性危機亟需國際金融機制在提供應急公共物品方面作出快速反應。同時,長期積攢的新興國家與西方主要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議題上的結構性矛盾也對全球金融治理的推進構成了嚴峻挑戰。
在這一背景下,推動國際金融機制變革以應對全球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和金融治理任務就成為了國際社會的重要關切。作為崛起的新興大國和全球金融治理重要利益攸關方,近年來中國在參與和推動國際金融機制改革和創設新機制過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并對未來國際金融機制變革及其發展方向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回顧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進程,中國取得了哪些積極進展,積累了哪些治理經驗,同時又面臨哪些壓力和挑戰?如何應對這些壓力并推動國際金融機制變革邁向更高臺階?無疑,這一系列問題的探索對于進一步推進國際金融機制變革與穩定全球金融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進展
國際金融機制是對國際金融領域中的國際組織、合作論壇、非正式機制和金融公司等機構以及一系列原則、規則和行為方式的統稱。參與國際金融機制是中國維護國家金融利益、開展金融合作與提升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渠道。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歷史進程,就是中國與國際金融機制的互動關系演進過程,其間中國經歷過4次重要的身份轉型,即從國際金融體系之外的游離者到融入國際金融機制的參與者,再到國際金融機制的改革者以及推動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引領者。
游離于國際金融體系之外時期(1949-1980年)。在建國后的頭30年,由于意識形態對立與西方社會對于新中國的封鎖等歷史政治原因,中國較長時間游離于國際金融體系之外,中國在世界銀行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席位也長時間被臺灣當局非法占據。在這一時期,中國與國際金融機制的互動很少,或者幾乎是零互動。直到回歸聯合國和中美關系正常化后,中國重新加入國際金融機制才逐步提上日程。在此期間,中國對重新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進行了一系列的觀摩、考察和談判。隨著世界銀行和IMF在1980年4月正式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實現了從國際金融體系之外的游離者到國際金融體系參與者的身份轉變。
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機制時期(1980-2008年)。在這一時期,中國廣泛地加入各種國際金融組織機構,是國際金融機制的積極學習者和重要支持者。這一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80年代至90年代末)是中國作為國際金融體系新成員的適應期,中國主要是熟悉和學習國際金融機制的規章制度和治理經驗,并推動國內金融與貨幣體制改革。同時,積極利用世界銀行和IMF等機構提供的援助貸款促進經濟發展和提升金融能力建設。(2)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第二個階段(世紀之交至2008年金融危機),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與貢獻率上升,中國與國際金融機制的關系由被動型轉為主動型。一方面,基于對IMF等機構的治理缺陷進行反思,中國在2000年簽署了《清邁協議》,開始尋求通過區域貨幣互換網絡的方式增強金融風險抵御能力。另一方面,中國開始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民主化改革,促成了世界銀行和IMF在2005年通過了提升新興國家份額的增資與改革方案。
推動國際金融機制改革和創設新機制時期(2008-2016年)。為有效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與國際金融機制的互動關系更為主動和頻繁,聯合新興國家群體共同推動國際金融機制改革和創設新機制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發揮的突出作用促使西方國家與新興國家在2009年G20匹茨堡會議上就推動國際金融機制改革議題上達成共識。(3)G20 Leaders Statement: The Pittsburgh Summit, September 24-25, 2009, Pittsburgh; 王文、王鵬:“G20機制20年:演進、困境與中國應對”,《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5期,第1~9頁。從而,G20成功地取代G7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平臺。隨后,中國在世界銀行和IMF兩大國際金融機構中的投票份額也分別上升至4.42%和6.39%,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股東。同時,歷經5年之久,人民幣最終在2016年10月被納入SDR貨幣籃子也是中國推動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重要里程碑事件。自此,人民幣正式獲得了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相同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轉向快車道。
另一方面,中國在這一時期創設了世界信用評級集團(2012年)、亞投行(2014年)、新開發銀行(2014年)、應急儲備安排(2014年)和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2015年)等一系列新機制,展現了中國獨立進行國際制度建設的經濟能力和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4)李巍、唐健:“國際舞臺上的中國角色與中國學者的理論契機”,《國際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第48頁。作為現有國際金融機制的補充和平行機構,這些新機制覆蓋了基礎設施投資與融資、短期國際收支平衡和貨幣結算等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領域,基本滿足了中國在區域內、跨區域、南北合作與南南合作方面產生的多層次全球金融治理新需求,并為提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代表性與話語權提供了新的發聲平臺。
引領國際金融機制變革新時期(2016年至今)。在特朗普上臺后,隨著美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意愿的下降,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不足與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構性矛盾變得更為嚴峻,尤其是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制度性權力和話語權進一步提升受到了美國的巨大抑制。(5)Imad A.Moosa, Nisreen Moosa, Eliminating the IMF: An Analysis of the Debate to Keep, Reform or Abolish the Fund,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135-161.Oliver Stuenkel, “The Financial Crisis, Contested Legitimacy, and the Genesis of Intra-BRICS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19, Issue 4, 2013, pp.611-630.對此,中國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要進一步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9日;易綱:“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重要講話精神”,《人民日報》,2016 年10月25日。引領國際金融機制變革和拓寬多元的金融治理渠道成為了新時期中國的主要著力點。
第一,以G20金融穩定理事會為核心,積極推動全球金融監管框架的完善。成立于2009年G20倫敦峰會的金融穩定理事會是金融危機之后最重要的全球金融治理核心機構,其在制定銀行監管標準、資本流動性和場外衍生品監管等全球金融監管政策制定與落實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作用。(7)蘭德爾·夸爾斯、夏穎:“金融穩定理事會十年回顧與展望”,《中國金融》,2019年第23期,第17~18頁。作為重要的成員國,中國在2019年G20大阪峰會上為推動理事會進行金融監管改革和機制完善等發揮了積極作用。
面臨不斷嚴峻的全球金融形勢,在2019年6月日本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強調要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應對金融不確定性風險,特別是發揮金融穩定理事會在落實金融部門改革、評估改革措施影響、監測金融穩定脆弱性和金融創新方面的重要作用。(8)易綱:“宏觀政策空間充足,有能力應對各種不確定性”,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6/10/c_1210154379.htm.(上網時間:2020年3月10日)在中國的積極作用下,金融穩定理事會就啟動一個新的金融監管框架問題上達成共識,并發布了《G20金融監管改革的實施進展》。在同年10月的G20財政和央行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各方進一步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盡快落實對全球金融監管框架作出新的調整方案,包括建立更為開放和彈性的全球金融機制,完成對銀行“大而不能倒”改革效果的評估,促進金融衍生市場安全和強化對引入全球“穩定幣”的監測管控等一系列舉措,以更好地完善金融部門改革,應對全球金融系統新出現的脆弱性問題。(9)“Progress in Implementation of G20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s,” FSB, June 25, 2019; “FSB Work Programme for 2020,” FSB, December 17, 2019.
第二,推動世界銀行完成新一輪增資與份額改革。在2010年改革方案之后,世界銀行的增資計劃和份額改革就陷入了相對停滯的狀態。對此,中國采取靈活策略成功推動世界銀行在2018年4月21日的春季會議上批準以增加130億美元認繳資本和內部改革措施為主的一攬子方案和加快完成新的股份審查。(10)“世界銀行集團股東國批準了變革性增資一攬子計劃”,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8/04/21/world-bank-group-shareholders-endorse-transformative-capital-package.(上網時間:2020年2月26日)在新的增資方案獲得通過后,中國的投票份額將從5.03%上升至5.71%,而美國和日本的投票份額將由16.32%和8.19%下降至15.87%和6.83%。(11)數據來源: “IBRD Country Voting Table,” World Bank, Feb.18, 2020; Daniel Moss, “At World Bank, China Moves to the Grown-up Table,” The Bloomberg, May 6, 2018.同時,作為與美國同意世界銀行新增資計劃的交換,中國接受了以上調中國貸款利率層級為主要內容的新貸款政策。該政策規定在五年緩沖期之后,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將不再向中國提供低息貸款,同時中國將執行中高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利率標準,并逐年縮減向世界銀行的借款規模。(12)“Changes in IBRD Loan Pricing Effective,” World Bank, July 1, 2018; “World Bank Adopts $1 Billion-Plus Annual China Lending Plan over US Objections,” CNBC, December 5, 2019.
新貸款政策增加了中國的借貸成本,但相對于中國投票份額的切實提升,這一妥協和讓步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上,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新貸款政策也符合中國作為世界銀行出資國的新身份定位。如世界銀行新行長馬爾帕斯所言,“中國借款數目的減少和貸款項目的增多標志著中國將變成世界銀行日益重要的貢獻國。世界銀行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為緊密的建設性關系,尤其是支持中國在減貧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專長領域分享經驗和發揮更大作用。”(13)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David Malpass 2019 Spring Meetings Press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pril 11, 2019.
第三,加快落實新開發銀行的擴員計劃。新開發銀行是第一家由發展中國家主導和組成的國際多邊銀行機構。截至2019年9月,在促進金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新開發銀行共批準了投資與融資項目37個,總投資額達到102億美元,并在2018年獲得標普和惠譽的“AA+”長期信用評級。(14)Leslie Maasdorp, “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 Turns Four: What has It Achieved?” World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20, 2019.同時,2019年7月,新開發銀行在巴西圣保羅開設了首家區域辦公室,并計劃2020年在俄羅斯和印度開設新的區域辦公室。這也被視為新開發銀行旨在拓展與成員國的業務合作和增強運營能力的新表現。
然而,基于對IMF在最新的份額審查中未能增加份額規模和調整金磚國家份額比重的不滿,為緩解在金融公共物品供給方面不斷擴大的需求,新開發銀行決定加快落實擴員計劃。2019年11月15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發表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巴西利亞宣言》,共同聲明新開發銀行將根據《成立新開發銀行的協議》進行擴員和設立新的項目準備基金,進一步增強面向金磚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能力和與其他多邊銀行機構強化合作。同時,采取增加對應急儲備安排的脫鉤部分復雜性演練等多種措施,確保金磚國家在抵御短期收支風險的迅速反應能力,(15)“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巴西利亞宣言(全文)”,http://www.scio.gov.cn/tt/zdgz/Document/1668270/1668270.htm.(上網時間:2020年3月6日)從而盡快實現將新開發銀行打造成為一個面向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更具多邊性和開放性的“金磚+”金融合作機構的目標。
第四,拓寬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新領域,增強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能力。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演變為一場全球性危機,并迅速波及到金融領域。受新冠疫情以及沙特石油擴產降價等影響,美國股市在2020年3月先后兩次發生熔斷,全球三大股指單日跌幅均超過9%,創下近40年來最大跌幅。種種跡象表明爆發全球性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的風險在不斷上升。對此,國際社會產生了極為迫切的金融公共產品供給需求,并亟需國際金融機制作出快速有力的回應。
面對新冠疫情正在演變成為全球性的衛生危機,亞投行在2020年2月10日率先發表聲明稱,將隨時協助中國提供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基礎設施項目貸款以應對當前的疫情需求。同時,亞投行期待與其他多邊銀行和私營部門等伙伴共同合作,向中國和其他成員提供公共衛生領域的專項援助。(16)“AIIB to Invest in Emergency Public Health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AIIB, February 10, 2020.翌日,新開發銀行也發表聲明稱愿為中方提供包括緊急融資在內的全面支持,并支持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共同合作,協助成員提升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17)“New Development Bank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o China Epidemic Figh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2/11/c_138774531.htm.(上網時間:2020年2月27日)2020年3月2日,世界銀行和IMF也發表聯合聲明稱,將分別提供最高達120億和5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用于幫助其成員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特別是向疫情嚴重的中低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提供低息和無息貸款以降低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18)Joint Statement for Managing Director, IMF and President, World Bank Group, March 2, 2020.可以說,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提供專項衛生基建貸款方面的快速行動展現了它們在拓寬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領域的巨大潛力。同時,這也敦促了亞投行、新開發銀行與世界銀行、IMF為后續全球經濟恢復增長、緩解國際收支流動性風險和增加衛生基礎設施領域的金融公共產品供給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
第五,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向多元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權是由美元支付體系所賦予的。作為一種實質意義上的世界貨幣,美元霸權對于人民幣有著較強的約束和限制。(19)夏斌:“國際貨幣體系緩慢變革下的人民幣國際化”,《中國金融》,2011年第15期,第55~56頁。盡管被納入SDR貨幣籃子后,人民幣朝成為一種國際貨幣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但與美元、歐元等貨幣相比,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較弱、國際社會認可度不高、抵御國際匯率市場波動能力較弱等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因而,為緩解美元霸權壓力和增強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近期中國采取多種舉措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主要包括: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二期在2018年5月全面投入適用,支持在全球超過90個國家和地區的商業銀行用于人民幣支付;新開發銀行在2019年2月25日發行第二筆總額為30億元人民幣綠色債券,并且金磚國家領導人在同年11月舉辦的巴西利亞峰會上就發行新的債券基金和擴大金磚國家之間的本幣債券市場和本幣支付合作達成一致意見;中國人民銀行在2020年2月底宣布將發展人民幣利率、外匯衍生產品市場,研究推出人民幣利率期權促進提升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發布全國金融行業首個區塊鏈標準和加快央行發行法定數字貨幣步伐。這些新舉措既在客觀上加速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同時也是應對美國金融霸權結構性壓力的一種積極策略,并最終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
二、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面臨的挑戰
中國參與和推動國際金融機制變革取得了積極進展,但也面臨一系列全球性挑戰。短期內,它表現為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短期金融風險上升、金融黑天鵝事件的破壞效應、美國就匯率操縱國問題反復向中國施壓等等。長期看,它包括美國對中國金融改制和創制施加的結構性壓力,西方國家對亞投行等新機制的運營政策標準存在質疑,以及新機制的金融公共物品供給能力較弱等現實挑戰。
首先,美國對中國金融改制和創制施加的結構性壓力。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在國際金融機制改革議題上表現出極為保守的態度,并且多次利用它的制度性權力優勢阻礙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或設置障礙。如前文所述,中國為推動世界銀行新增資計劃的順利通過不得不接受較高的貸款利率標準。在排他性更強的IMF改革中,中國尋求份額上升的路徑更是遭到了美國的極大抑制。IMF第15次份額審查的“失敗”就是這種抑制的集中體現。
2019年10月被推遲近四年之久的IMF第15次份額審查終于完成,然而被新興國家寄予厚望的增資與份額調整并沒有實現。在10月18日的特別會議上,IMF新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作出了維持現有資金規模和份額調整保持不變的決定,并宣布涉及增資和份額調整的第16次總審查開展時間也將由2020年推遲至2023年底。同時,將引入一個新的公式取代現有份額計算公式。(20)See IMF Membership Endorses Package on IMF Resources and Governance Reform, October 18, 2019,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9/10/18/pr19379-imf-membership-endorses-package-on-imf-resources-and-governance-reform.(上網時間:2020年1月17日)盡管國際經濟力量分配與全球金融治理形勢較2010年出現了重大變化,但IMF第15次份額總審查卻未能增加份額規模和作出有利于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調整,中國期待的IMF份額改革仍止步不前,甚至依照新公式的第16次審查將對中國的份額調整可能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表1 現有份額公式(CQS)
說明:圖表為筆者自制,參見IMF基金組織份額計算方式規定。
份額計算公式是IMF在資格審查中對成員國進行份額調整的重要參照標準,不同的計算方法將對份額調整產生直接影響。現有份額公式(見表1)賦予了反映真實匯率的購買力平價GDP和經常項目收支更高的計算權重。這種測算方式對于中國較為有利。

表2 按現有份額公式計算的主要經濟體投票份額變化 (單位:%)
說明:圖表為筆者自制,其中各項指標為2016年經濟數據,參見:“Updated IMF Quota Formula Variables-July 2018,”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tas/2018/0818.htm.(上網時間:2020年1月17日)
根據2018年IMF發布的成員國份額權重測算結果顯示,若按照現有公式進行第16次份額審查,中國和美國的份額權重將發生重大變革(見表2)。中國的投票份額將由6.390%上升至12.855%,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股東。美國的投票份額則將下降至14.734%,并且失去重大事項的一票否決權。更為重要的是,金磚國家的總份額權重將超過15%,從而使IMF的制度性權力將實現由美國向金磚國家的轉移。對此,盡管IMF宣稱參照新份額公式的份額改革將與新興國家的經濟活力更加匹配,但可以預估新公式極有可能采取一種稀釋中國份額增長和保證美國投票份額高于15%的測算方法,從而保障美國制度性權力優勢不被挑戰。
同時,對于中國創設的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等新機制,目前美國奉行強硬的抵制策略,即美國反對和拒絕加入中國創設的新機制,并且反對其他西方國家加入這些新機制。(21)Sevasti-Eleni, Vezirgiannidou,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Powers in a Post-Hegemonic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3, 2013, pp.646-647.對于這些新機制,美國政界和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它們是中國試圖繞開世界銀行和IMF的“另起爐灶”和挑戰美國國際金融體系領導權、甚至是挑戰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的表現。(22)關于美國學界對于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的擔憂和質疑可詳見:Nana’ De Graaff and Bastiaan Van Apeldoorn,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Contending Elites, Colliding Vis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1, 2018, pp.113-131; Giles Scott-Smith, J.Simon Rofe(ed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and the Post-War World Or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129-148; “China vs America: A New Kind of Cold War,” The Economist, May 16, 2019; Helmut Reisen, “Will the AIIB and the NDB Help Reform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ing?” Global Policy, Vol.6, Issue 3, 2015, pp.294-304; Matthew Heller, “Lawrence Summers Calls China-Led Bank a Failure of U.S.Policy,” Capital Market, April 6, 2015; Phillip Y.Lipscy, “Who’s Afraid of the AIIB: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upport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Foreign Affairs, May 7, 2015.基于對中國威脅美國金融霸權的擔憂,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國反對和抵制中國金融創制行為的立場就極為堅定。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對于亞投行等新機制的抵制行為幾乎就是20世紀90年代反對日本創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翻版,其行為符合權力轉移理論和制度制衡理論的表征。(23)賀凱、馮惠云:“領導權轉移與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制度制衡與亞投行”,《國際政治科學》,2019年第3期,第31~59頁。它表現為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國作為制度守成國不會放棄它的領導權,并將中國的金融創制行為視為是對美國制度領導權的挑戰而傾向采取反制的策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聲音來自于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認為亞投行的建立意味著中國將在未來數十年主導一個新的多邊銀行機構。美國阻撓它的盟友加入亞投行的失敗行為將是美國失去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話事人”地位的先兆。(24)Lawrence Summers, “AIIB: We Have Lost Influence,” http://larrysummers.com/2015/04/17/aiib-we-have-lost-influence/.(上網時間:2020年2月12日)
對此,美國利用其金融霸權不斷向中國金融創制行為施加結構性壓力。比如,美國向潛在意向國鼓吹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是一個中國主導投資的政治工具而非是一個遵循多邊主義框架的銀行機構;通過設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和安全負擔轉移等方式試圖增加亞投行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和違約風險;將亞投行描繪為中國建立全球經濟霸權的亞洲版馬歇爾計劃;鼓吹應急儲備安排旨在挑戰IMF在國際金融領域的正統性;質疑新開發銀行的環境與社會政策標準破壞全球金融治理的可持續原則和透明性原則等等。(25)趙明昊:“美國競爭性對華戰略論析”,《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10期,第15~16頁;Jane Perlez, “U.S.Opposing China’s Answer to World Bank,” The New York Times, Oct.9, 2014;Kevin P.Gallagher, “Obama Abandons Allies on China’s Marshall Plan: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Increasingly Left behind as It Defies Its Closest Allies in Asia,” The Globalist, March 18, 2015;David Malone, Raja Mohan, and Srinath Raghav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33.作為全球金融公共物品最大的提供者,美國抵制和施加壓力的行為無疑對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等新機制的規模水平、融資能力和治理效能產生了較大限制。
其次,西方國家對新機制的運營政策標準存在質疑。在制度建設上,國際社會對新機制的運營政策標準存在質疑是制約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等機制面向更多成員開放,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建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系和吸引更多私人投資者的一個重要因素。國際金融機制的運營政策標準一般由環境、社會、采購標準構成,它是評估合作項目透明度的重要指標。目前,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分別采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標準,前者采用了與其他多邊銀行機構接軌的一致性標準,而后者則采用了重視不同國家發展差異性的國別體系標準。這種區別展現了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在治理結構、成員構成和合作對象上的差異性。(26)朱杰進:“新型多邊開發銀行的運營制度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8期,第35~36頁。但也引發了西方國家對于新機制運營政策標準的開放性、環境可持續性和透明度問題的質疑。
比如,西方國家質疑亞投行版本的“環境、社會與治理”標準與世界銀行版本的“環境與社會框架”標準的匹配性和通用性問題;不同多邊銀行機構參與的聯合項目可能因標準適用分歧而付出高昂的協調成本;新開發銀行依據國別體系政策標準的貸款項目會導致環境污染、滋生腐敗等問題,并對國際最佳標準造成破壞等等。(27)A.Bhattacharya, “M.Romani, Meeting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The Case for a New Development Bank,” Present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eminar, Madrid, March 11, 2013; Molly Elgin-Cossart and Melanie Hart, “China’s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Institutions,”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September 22, 2015.此類擔憂和質疑會極大地限制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與其他多邊銀行機構、私人投資者在合作領域與合作深度上的拓展。因而,如何在國際最佳標準和國別體系之間確立一種兼顧開放性、差異性和透明性的運營政策標準對于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尤為重要,其中既要在環境、社會和采購標準上與現有多邊銀行機構采用的國際最佳標準相接軌以協調不同機構的參與合作,又要充分考慮項目國當地的社會匹配條件和經濟承載能力,從而產生可持續的治理效能。
再次,新機制的金融公共物品供給能力相對較弱。中國創設的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等新機制是豐富全球金融公共物品渠道的重要補充,但也要認識到這些新機制在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能力方面與世界銀行和IMF等機構相比仍存在著較大差距,它主要面臨著自身資金規模較小、投資與融資能力較弱與聯合融資項目的合作路徑較為單一等現實挑戰。
其一,自身資金規模較小,制約功能發揮。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嚴重的投資不足。保守估計,目前每年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高達1.8~2.3萬億美元,僅亞洲地區每年的投資需求就達到7300億美元,而現有多邊銀行機構至多能夠覆蓋0.8~0.9萬億美元的投資需求。(28)A.Bhattacharya, M.Romani, Meeting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The Case for a New Development Bank, Present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eminar, Madrid, March 11, 2013.相對于全球每年超過1萬億美元的投資缺口而言,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的初始認繳規模僅分別為1000億和500億美元,依靠現有成員國的資金認繳規模遠遠不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
其二,投資與融資能力相對不足。盡管成立至今,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已累計批準投資項目(含聯合融資項目)超過100個,總金額超過240億美元。但與世界銀行在過去兩年批準總額超過1200億美元的融資貸款相比,(29)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官網。亞投行與新開發銀行在現階段的總體投融資能力仍較為不足。同時,受經濟下行壓力和金融系統性風險上升等負面因素影響,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也出現了融資成本上升、投資回報率較低、債務違約風險上升等不利情形。
其三,聯合融資項目的合作路徑較為單一。一方面,在合作領域方面,目前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的聯合融資項目仍大多集中在交通運輸、電力、能源與城市建設等傳統基建領域,而較少涉及氣候、教育、健康和社會保護等領域,而這些項目恰恰包括了私營部門更為關注、參與程度更高且與人類發展高度相關的新領域。同時,在聯合融資的合作對象上,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也存在著單一化的問題。目前,新開發銀行的合作對象僅為金磚國家內部的開發銀行和商業銀行,而不涉及與其他多邊銀行的項目合作;亞投行的合作對象則過于集中于其他多邊銀行機構,聯合融資項目中的私人投資者和私營部門參與度存在嚴重不足。
三、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的前景
展望未來,中國可望在未來國際金融機制變革中積極有為,推動存量改革、拓展與完善增量改革,為國際金融合作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在國際金融機制的存量改革方面,首先要認識到現有國際金融機制中,中國尋求投票份額上升的存量改革的步伐是穩健的,既不會因美國壓力而屈服,也不會采取過激或者對抗的政策以顛覆美國目前所具有的某些優勢。當然,隨著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地位不斷上升,可以預見美國會愈加利用“一票否決權”阻礙和延緩中國投票份額的上升,繼而中國尋求存量改革目標的實現將愈加困難。對此,打鐵還需自身硬,要通過加快國內金融領域開放步伐和提升人民幣國際競爭力等方式,加強自身金融能力建設和提升塑造國際金融治理秩序的能力,這才是中國應對美國結構性壓力和完善新機制建設最為重要的依托。在此前提下,中國應采取積極措施推進國際金融機制的存量改革。
其一,靈活運用多種策略推動世界銀行和IMF份額改革。目前,世界銀行與IMF對于中國的份額調整既不及時也不公平。盡管在份額改革議題上,中國的制度性權力上升受到嚴重制約,但要明晰隨著中國自身金融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國在世界銀行和IMF推動份額調整方面將愈加處于主動改革者的位置,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則處于被動的被改革者的位置。因此,中國更應該充分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和能動性,充分利用G20和聯合國等多邊平臺,積極團結新興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推動份額改革議題上形成合力,共同促進世界銀行和IMF份額改革的實時化、公平化與民主化。同時,推動份額改革也要注重策略,特別強調要運用好議題聯系策略和利益交換策略。比如中國通過在貿易規則談判和知識產權談判上作出適當的讓步、擴大對世界銀行和IMF的財政支持等方式推動美國支持份額改革。總之,要主動地尋求中美在推動份額改革達成妥協和一致意見的各種機會和可能。
其二,完善新機制的政策標準與監察機制建設。目前,西方國家對于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采用的運營政策標準仍然存在較大的疑慮。一是質疑新機制的政策標準與國際最佳標準不適配;二是擔憂這些政策標準可能會造成腐敗和環境破壞等問題。盡管提高環境、社會與采購方面的政策標準,逐步與“國際最佳標準”接軌是新機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但要認識到這一制度改革的艱巨性。其中主要原因是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的項目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程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很多項目國的治理能力難以滿足“國際最佳標準”的要求。因而,為保證基礎設施投資的靈活性,需要在政策標準上作出相應取舍和讓步。但另一方面,新機制必須要加強監察機制建設,通過監察和評估提升項目投資的透明度,從而彌補項目國在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以減少腐敗和環境破壞發生的可能性。
其三,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新價值理念落地化,增強話語權建設。在全球金融治理領域,知識和理念創新是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相較于直接尋求制度性權力可能加劇中美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競爭和對抗,增強根植于價值與理念創新的話語權建設更有利于中國改革目標的實現。近年來,中國相繼提出了“精簡、廉潔、綠色”“綠色金融”和“包容性發展”等全球金融治理新價值、新理念。這既是中國重要的價值創新,也是話語權的重要來源。但是也要承認,這些價值理念如果不能轉化為可操作的具體規則、可實施的程序措施和可量化的評估標準,就不可能實現落地化,甚至成為空談和口號。在如何將價值理念貫徹為具體實施的治理細則和規章制度方面,中國仍有很多需要向現有成熟的國際金融機制學習的地方。特別是將價值話語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話語權力,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推動國際金融機制的增量改革方面,要進一步發揮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等新機制在基礎設施投資和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方面的增量改革效應,包括面向更多成員開放、深化合作路徑與創新多元化投資與融資模式等方式,擴大新機制的資金池和投資能力,通過增量改革緩解國際金融機制存量改革動力不足的壓力。
其一,吸引新成員加入,擴大資金池。目前,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在資金規模上較為不足,需要吸引更多新的投資者。一方面,作為世界銀行的前兩大股東,美國和日本遲遲沒有加入亞投行,這對于亞投行擴充資金規模和提升基礎設施投資能力構成較大的限制。亞投行應該探尋吸引美國和日本加入的可能性,并支持美國和日本在亞投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成員規模少與政策標準不完善是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競爭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對此,金磚國家領導人需要探索吸納新成員的有效途徑,從而提升新開發銀行的治理能力。
其二,深化多元合作路徑,提高投融資能力與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水平。相較于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而言,亞投行與新開發銀行的總體投資與融資能力仍十分不足,這不利于滿足其成員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巨大需求。對此,要進一步深化合作路徑,拓展新機制與現有多邊銀行機構在基礎設施投資、可持續增長和應對貧困等領域的聯合融資項目合作。同時,新冠肺炎疫情等新全球危機也產生了新的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給需求,這有利于促進亞投行等機制從傳統的能源、運輸等基建領域轉向關注環境氣候、衛生醫療等新領域合作,以便提供更為充足的全球金融公共物品。
其三,充分發揮私營部門的積極作用,創新多元投資與融資模式。目前,亞投行和新開銀行的合作項目中,有私營部門如跨國公司、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和私人投資者參與的較為稀少。亞投行等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私營部門在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能力、降低融資成本與提高資本回報率方面的巨大潛力和專業知識。對此,亞投行等機制亟需創新涵蓋私營部門在內的多元投資與融資模式,鼓勵私人投資者和社會資本發揮更大作用,為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提供更多的融資平臺與合作路徑。
余 論
近年來,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機制變革進程明顯加快,金融改制與金融創制并舉的雙軌策略日益明顯。中國既取得了一系列積極進展,但也遇到美國金融霸權的壓力及諸多現實問題等挑戰。中國對其復雜性要有充分認識。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內,除非國際金融體系發生顛覆性變革,美國及其領導的國際金融機制仍將發揮支柱性的作用。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及其變革中顯示出強大的行動力,但較之于美國長期執掌全球金融治理牌局的豐富知識和雄厚金融資源,仍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且在制度性權力提升方面受到較大的限制。中國對此要保持戰略定力并積極施策。同時,最近一段時間新冠肺炎疫情、沙特原油擴產降價和美股熔斷等金融黑天鵝事件對全球金融治理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為亞投行等新機制在推動國際金融機制變革提供了新的契機。與世界銀行和IMF等傳統機構相比,中國創設的新機制具有較高的靈活性、較低的行政協調成本和較低的制度惰性等特點,因而能夠比較迅速地回應全球金融治理新需求。加上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自身金融治理能力提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樂觀預期,中國有理由相信,在建立更為完善的制度標準和治理模式后,這些新機制將有足夠的能力和空間不斷推進國際金融機制的改革,中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權力和話語權自然也會隨之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