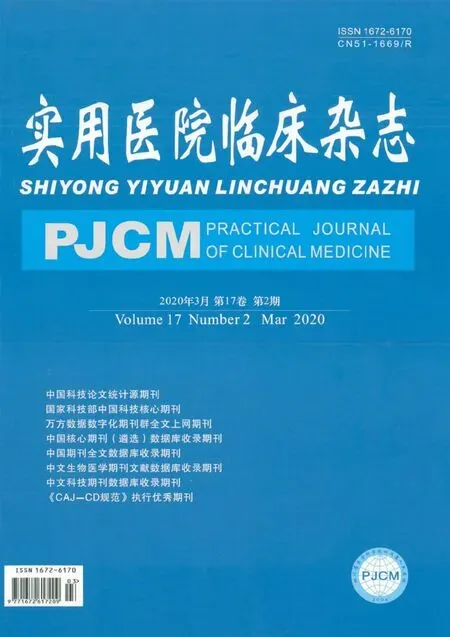對α-干擾素霧化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認識
周光紅,余旭東,郭建婷,黃 靜,魏 維,吳 波,龍懷聰
(1.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 a.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b.老年重癥監護室,四川 成都 610072;2.川北醫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0;3.四川省儀隴縣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四川 儀隴 637600;4.四川省安岳縣人民醫院 a.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b.重癥監護室,四川 安岳 642300)
自2019年12月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對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標本全基因組序列分析發現病原菌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2019 nCoV),與蝙蝠攜帶的SARS樣冠狀病毒RaTG13株全基因組親緣關系最近,同源性為96%。雖然我國積累了大量治療SARS的寶貴經驗,但目前尚無特效藥物或疫苗被批準用于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由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治方案(試用版)中提出了抗病毒、康復者血漿治療等多種治療方案,其中第二、三、四、五、六版診治方案中均提出可試用α-干擾素(Interferon-α,IFN-α)成人每次500萬U或相等劑量加入滅菌注射用水2 ml,每天兩次霧化吸入。IFN-α 為一種廣譜抗病毒藥物,重組人IFN-α1b霧化治療小兒呼吸道病毒感染已在我國得到兒科臨床專家的廣泛認同并A級推薦[1],在病毒性肝炎中亦應用廣泛,但在COVID-19的治療中占據怎樣的地位,本文將結合國內外研究成果一探究竟。
1 干擾素(interferon,IFN)的分類及作用機理
1.1 IFN的分類IFN是機體細胞受適宜刺激后分泌的一類具有多種生物學活性的糖蛋白物質,根據其來源、基因序列及特異性受體的不同,可分為Ⅰ型、Ⅱ型和Ⅲ型干擾素。Ⅰ型干擾素主要包括IFN-α、IFN-β、IFN-ω、IFN-κ和IFN-ε,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為抗病毒,其中IFN-α為目前應用較廣的抗病毒藥物之一;Ⅱ型干擾素只有一種:INF-γ,主要生物學活性為免疫調節作用;Ⅲ型干擾素主要包括IFN-1、IFN-2和IFN-3,具有廣譜抗病毒及免疫調節作用[2]。人類許多種細胞均能產生IFN,不同的細胞分泌不同IFNs。關于不同種類IFNs的來源、結構及生物學作用見表1。
1.2 IFN的作用機理IFN具有廣譜抗病毒、免疫調節、抗細胞增殖等作用[2]。本文將重點闡述IFN在冠狀病毒治療中的抗病毒作用機理。病毒感染機體后,宿主細胞經過一系列反應引起IFN等抗病毒細胞因子表達,IFN進一步激活IFN信號通路,使得數以百計的IFN刺激基因(Interferon-stimulated genes,ISGs)表達,并借由ISGs引發抗病毒效應。關于IFN用于治療冠狀病毒感染的作用機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確,比較認可的觀點是IFN通過誘導限制病毒復制不同階段的ISGs表達來控制病毒感染。ISGs在上皮細胞、內皮細胞和巨噬細胞等屏障細胞中均有表達,在宿主抵抗病毒感染的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IFN通過與細胞表面的 IFN受體結合,啟動下游的JAK-STAT 信號通路,進一步誘導大量ISGs的轉錄表達。現將ISGs抗病毒作用機制的主要研究結果展示如下。

表1 不同種類IFNs的來源及生物學作用
1.2.1干擾素誘導跨膜蛋白(IFITM) IFITM是一種新型抗病毒細胞防御分子,由人類IFITM基因編碼,該基因定位于11號染色體上,由4個功能基因組成:IFITM1、IFITM2、IFITM3和IFITM5。在非IFN誘導情況下,IFITM1、IFITM2和IFITM3在上皮細胞和內皮細胞中廣泛表達,而IFITM5主要在成骨細胞中表達。I型和II型IFN均可刺激IFITM表達。IFITM1、IFITM2和IFITM3通過改變病毒與細胞的融合部位來阻止包括SARS-CoV在內的多種病毒入侵[3,4]。因此,推測霧化吸入IFN,可以直接刺激氣道上皮細胞誘導IFITM1、IFITM2和IFITM3的表達以產生抗病毒效應。
1.2.2γ-干擾素誘導的溶酶體巰基還原酶(gamma-interferon-inducible lysosomal thiol reductase,GILT) GILT是一種與溶酶體相關的ISGs,在抗原提呈細胞(如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和B淋巴細胞等)的溶酶體中大量表達,且可被II型干擾素誘導表達,通過限制被選擇的包膜RNA病毒的進入而發揮抗病毒效應。GILT通過甘露糖-6-磷酸受體途徑內吞進入溶酶體,作為溶酶體和吞噬體中唯一的巰基還原酶,GILT有助于溶酶體蛋白酶組織蛋白酶的降解、維持細胞正常的氧化還原狀態和禁止異常自噬[ 5,6]。研究發現SARS-CoV和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EBOV)通過進入溶酶體的方式實現病毒播散[7],而GILT在打開內化病毒糖蛋白和調節溶酶體內環境方面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溶酶體是SARS-CoV、EBOV和許多病毒侵入宿主細胞胞質并啟動病毒復制的一個重要細胞小體[7~9],因此,推測GILT可能會影響這類病毒入侵宿主。2019年,我國學者研究證明了GILT亦在肺上皮細胞中表達,并且GILT可通過病毒包膜糖蛋白的介導限制SARS-CoV、EBOV等病毒進入宿主,且研究還發現改變CXXC基序中的兩個半胱氨酸殘基或取消N-連鎖糖基化的突變可損害GILT的功能,這意味著溶酶體和硫基還原酶功能是GILT抑制這些病毒進入宿主細胞的必要條件[10]。
1.2.32′-5′ 寡腺苷酸合成酶 (2′-5′-Oligoadenylate synthetase,OAS) OAS基因是另一類重要ISGs,其編碼的功能蛋白OAS是一種活性蛋白激酶,該酶通過抑制病毒蛋白合成來產生抗病毒效應。最初由 IFNs誘導產生的 OAS 并無活性,在被病毒雙鏈RNA (dsRNA) 激活后才具有抗病毒功能,激活后 OAS 可誘導 ATP 水解產生 2′-5′寡腺苷酸,再借 2′-5′寡腺苷酸激活內源性內切核糖核酸酶 L (RNase L),激活的RNase L是發揮抗病毒的關鍵,病毒和宿主的單鏈RNA(ssRNA)均可被其裂解(被識別的RNA裂解產物可進一步誘導IFN產生及信號傳導[11]),導致病毒基因翻譯停止、細胞凋亡,限制病毒在體內外復制和傳播,進而發揮抗病毒功能。
1.2.4骨髓基質細胞抗原 2 (Bone marrow stromal antigen 2,BST2) BST2 是一種脂筏相關跨膜蛋白,I型IFN可誘導多種細胞表達BST2。BST2的結構為N端跨膜結構域,C端糖基磷脂酰肌醇(GPI)錨定,其胞外結構域中有兩個N-連接糖基化位點,并以二硫鍵連接的二聚體形式存在,而二聚體形式是BST2發揮抗病毒功能的關鍵。BST2通過限制病毒在高爾基體或細胞膜上出芽而阻斷包括人類冠狀病毒229E(hCoV-229E)[12]、SARS-CoV[13]在內等多種包膜病毒的釋放,依此產生抗病毒效應。
1.2.5其他機制 另外,膽固醇-25-羥化酶(cholesterol-25-hydroxylase,CH25H)[14],ADAP2[15]和NCOA7[16]也已被證實通過抑制病毒宿主細胞膜融合或內源性病毒離子的內吞轉運來阻斷病毒的進入而發揮抗病毒效應。總之,ISGs 是宿主發揮抗病毒作用的一類效應分子,降解病毒基因、抑制蛋白質合成、翻譯和裝配,在病毒感染的各個階段均能發揮作用。盡管一些ISGs在控制病毒感染方面的作用已被揭示,但仍不能完全解釋IFN的抗病毒作用機制,因此仍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來助力人類戰勝冠狀病毒。
當然,IFN尚有增強免疫及抗腫瘤作用:它通過作用于腫瘤細胞膜上的特異性受體,激活腺苷酸環化酶(AC)的表達,從而抑制腫瘤DNA的合成和細胞的分裂;它誘發腫瘤細胞MHC(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因子)的表達,增強免疫監視作用而利于清除腫瘤細胞;另外,IFN也可提高CD4+細胞反應性以誘導 T 細胞的增生以及活化細胞毒性 T 淋巴細胞、激活B淋巴細胞產生各種特異性抗體、激活NK細胞發揮殺傷活性、激活單核巨噬細胞發揮吞噬功能,從而抑制腫瘤細胞活性或殺傷腫瘤細胞。我們認為,IFNs的上述功能在抗病毒作用中亦是不可分割的。
2 霧化治療的作用機制
霧化吸入是呼吸系統相關疾病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霧化吸入通過特殊裝置將藥物轉變為氣溶膠形態,經口腔或鼻腔吸入,沉積于呼吸道和肺泡,以達到治療疾病、改善癥狀和濕化氣道的作用。因其具有用藥量少、局部藥物濃度高、起效快、不良反應輕、操作方便及患者舒適度高等優點而被廣泛使用。目前臨床上常用的霧化吸入裝置可分為射流霧化器、超聲霧化器和振動篩孔化器,IFN作為一種基因重組蛋白產物,霧化給藥時為保證其生物活性及分子結構完整性,建議選用振動篩孔化器及射流霧化器,而超聲霧化產生的熱量可能會破壞IFN的生物活性,故不建議使用[17]。氣溶膠微粒在氣道的沉降是藥物發揮作用的關鍵,其影響因素主要取決于氣溶膠微粒大小和患者呼吸方式,直徑1~5 μm(1~3 μm最佳)的氣溶膠微粒可較多沉降在下呼吸道和肺泡內,而緩慢而深長的呼吸,有利于增加氣溶膠微粒在肺內沉降。此外氣溶膠發生裝置、吸入藥物的藥代動力學對氣溶膠微粒在氣道沉降也均有影響。IFN-α1b注射液經霧化吸入后,霧滴粒子的粒徑分布適合呼吸道藥物遞送,并可沉積于各級支氣管、細支氣管和肺部等部位[18]。可見,霧化吸入IFN-α注射液的空氣動力學能夠支持其用于COVID的療效。
3 IFN在冠狀病毒中的治療
由于2019-nCoV 與SARS-CoV和MERS-CoV均屬于β-冠狀病毒,其與SARS-CoV 存在約70%的序列同源性,與MERS-CoV約40%的序列同源性。目前對于冠狀病毒的認識主要基于前期對于SARS-CoV、MERS-CoV 的相關研究。
2002年SARS肆虐中國時,抗病毒藥物利巴韋林聯合IFN是治療SARS的一種選擇[19],但最終的回顧分析并未肯定IFN在SARS中的療效[20]。即便如此,學者對干擾素在冠狀病毒治療中的探索并未止步。2012年MERS-CoV爆發,IFN再次被納入治療方案。Falzarano等[21]發現利巴韋林聯合IFN-α2b,在較低治療濃度下就能有效抑制MERS-CoV 在培養細胞內的復制(IFN-α2b從250 U/ml開始降低致細胞病變效應(CPE),在1000 U/ml及以上濃度時完全消除CPE;利巴韋林從100 μg/ml濃度開始降低CPE,在200 μg/ml及以上濃度時完全消除CPE),且二者具有協同效應。感染MERS-CoV的恒河猴在病程最初8小時內使用利巴韋林聯合IFN-α2b,能降低病毒在體內的復制,改善臨床癥狀,顯著減輕肺損害[22]。但該聯合療法可能僅適用于疾病早期階段,而對具有嚴重并發癥的晚期患者療效并不顯著[23]。因此,用藥時機也是影響治療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研究證實MERS-CoV對IFN-α的治療敏感性高于SARS-CoV 50~100倍[24]。由此可見,不同冠狀病毒對IFN的治療反應亦不相同。但總體來說,IFN用于MERS-CoV的治療價值還是得到一致認可。2014年發表于柳葉刀的一篇回顧性研究顯示口服利巴韋林聯合皮下注射IFN-α(IFN-α:皮下注射,180 μg/周,連用2周;利巴韋林:口服2 000 mg負荷劑量后,根據肌酐清除率不同選擇不同劑量與頻次,8~10天)治療MERS-CoV可顯著降低重癥患者的14 天病死率,但不能改善28天病死率[25]。上述研究顯示:IFN-α在SARS和MERS的抗病毒治療中有一定應用價值,但均為肌肉注射或皮下注射。
鑒于2019-nCoV 與SARS-CoV和MERS-CoV的同屬及同源性,肌肉注射或皮下注射IFN的不良反應較大,我國針對COVID-19的治療方案推薦嘗試霧化吸入使用IFN-α。霧化吸入可使藥物直達呼吸道,具有靶向性強、安全性好及依從性高等優點。
我國尚無IFN-α專用霧化制劑,注射劑品種包括重組人IFN-α1b、IFN-α2a及IFN-α2b。目前,國內使用的主要是IFN-α1b 與IFN-α2b,其中,IFN-α1b 基因由我國侯云德院士于1982 年從健康中國人臍血白細胞中獲得,是中國人機體主要抗病毒的IFN 亞型,而IFN-α2a 和IFN-α2b 的基因來源于西方白種人。關于霧化吸入IFN-α用于病毒性肺炎的嘗試主要源于我國的兒童病例。目前我國學者研究發現,霧化吸入IFN-α1b能改善兒童腸道病毒71型手足口病患兒及小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患兒的臨床癥狀,且不良反應少[26,27]。故重組人IFN-α1b霧化治療小兒呼吸道病毒感染已在我國得到兒科臨床專家的廣泛認同并A級推薦[1]。但筆者仔細查閱國外文獻,并未發現霧化吸入IFNs治療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報道,僅有少數的研究顯示霧化吸入IFN-γ可能有助于耐藥肺結核的控制和IPF的治療[28],說明霧化吸入IFNs可能在呼吸系統疾病的治療中具有一定應用前景。但目前缺乏關于IFN-α霧化吸入治療COVID-19的臨床研究結果,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尚需進一步研究。
4 霧化吸入IFN治療冠狀病毒肺炎的不良反應
總體來說,霧化吸入IFN具有作用迅速、用藥劑量小、全身不良反應輕等優點,但仍不能忽視其不良反應。肌肉注射IFN-α的不良反應主要包括低熱和流感樣癥狀群[29],也可引起厭食和疲勞等不良反應。國內學者在總結了99例IFN使用者的不良反應后指出IFN引起的不良反應大多輕微而可逆,但也有部分為嚴重的,甚至是致死的反應[30]。一項研究在比較了IFN-α1b 不同給藥途徑治療兒童病毒性肺炎中的不良反應后發現,肌注組不良反應發生率為 7.59%,而霧化組未發生明顯不良反應[31]。另一項關于霧化吸入IFN-α2b注射液治療小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研究,亦表示霧化吸入IFN-α2b與常規治療相比,二者間的不良反應并無統計學差異[28]。但研究顯示IFN霧化治療過程中產生的微生物氣溶膠,大部分會隨呼吸呼出[32],在相對密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于高濃度含新冠病毒的氣溶膠,可能會增加交叉感染風險[33]。為此,近期倪忠等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霧化吸入治療的建議指出:應選用霧化專用劑型進行霧化,在選用霧化藥物時,關注各種藥物霧化藥物的不良反應,并選用正確的霧化裝置,當然,應嚴密保護醫護人員[34]。并且霧化氣溶膠溫度不適宜易誘發患者出現氣道高反應、支氣管痙攣、高反應性咳嗽等不良反應,尤其易發生于合并基礎肺病的患者[35]。此外,部分廠家生產的IFN-α的輔料中含有苯甲醇等防腐劑,霧化時可能會導致呼吸道黏膜損傷,誘發哮喘發作[36]。不適當的霧化治療也會加重呼吸道疾病,造成缺氧甚至肺水腫。再者,目前國內生產的IFN-α均為注射制劑,雖然有文獻支持其空氣動力學符合霧化制劑的要求,但其用藥說明中沒有提到其可用于霧化吸入,屬于“超說明書用藥”范疇,臨床醫生應注意請患者及家屬簽署應用同意書。
5 總結
隨著 COVID-19疫情向全球逐漸蔓延開來,全球均積極應對,致力于探索潛在的有效藥物并大力研制新藥(包括疫苗),但新藥的開發需一段漫長的時期,諸如氯喹、IFN、利巴韋林等老藥新用成為當下治療熱點。IFN作為一種廣譜抗病毒藥物,是20世界人類基因工程的產物,曾參與SARS 和 MERS的治療,且發現有一定的治療價值,因此再次登上COVID-19的治療舞臺。但IFN在SARS 和 MERS的治療中一般采取肌肉注射或皮下注射,霧化吸入途徑既往僅用于兒童病毒性肺炎患者,鑒于霧化吸入IFN用量少、局部藥物濃度高且不良反應輕等優點,國家衛生健康委合理且大膽地提出試用 IFN-α 霧化吸入治療COVID-19。由于霧化吸入IFN治療冠狀病毒實屬首次,因此需嚴格把握其治療時機,高度重視不良反應,并規范操作,減少不必要的交叉感染。更重要的是開展大規模的臨床應用研究,獲得更多的證據,應對呼吸道病毒的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