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華德·雅各布森:我害怕眾口一詞和人群中洶涌的情緒
李乃清

“不是只有病毒出現時,人與人之間才需要保持距離;這個世界已變得危機四伏,無論到哪里,總聚集著一群烏合之眾。”歐洲疫情肆虐期間,布克獎得主、英國猶太裔作家霍華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與我討論到對未來的恐懼時,坦承自己對人群密集的恐懼——“我害怕人群中那種浪潮般洶涌的情緒。”
2014年,雅各布森出版了長篇小說《J》,這部令人深邃不安的災難預言性作品很快進入當年布克獎的決選名單。英格蘭詩人、艾略特詩歌獎得主約翰·伯恩賽德曾在《衛報》撰文,稱其可與《1984》和《美麗新世界》相媲美。——“《J》可被視作當下的英國反烏托邦小說,從流行文化泛濫到消費狂熱,從回避嚴肅事物到系統性侵犯個人隱私,它巧妙地折射出我們時代生活方式的種種詭異。”
《J》的故事設定在未來社會的濱海小鎮魯本港,這個社會試圖掩蓋一場大屠殺式的歷史災難,官方對災難從未有過正式認定,而是遮遮掩掩,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中,大家僅以含混不清的“出了事——如果真的出過事”來指稱它。
雅各布森筆下的這個社會看似正常,但種種現象又顯得“有點不對勁”。法律從未明令禁止某些書籍和音樂,但它們自動消失了。流行文化取代了嚴肅的審美趣味,人們只閱讀成功學、烹飪書和羅曼史,情歌小調代替了自由即興的爵士樂。“沒有禁止——從來都沒有明確禁止過什么——只是不再放了而已。它們被漸漸廢除,有如‘廢除這個詞本身。”
《J》中的男女主角凱文·柯恩和愛琳·所羅門斯,他們的姓名都是一個凱爾特名字與猶太姓氏相混雜的奇怪組合。經歷大屠殺式的災難后,官方抹去書本記載,迫使人們改名換姓,以此消除對個人、宗族和歷史的清晰記憶。雅各布森以荒誕筆法描繪了“出事”后的大規模改名行動:老老小小在公園里一起跳舞,陌生的人們彼此擁抱,等待隨機發放乃至搖號產生的新姓名。“你將會進入深度狂歡的睡眠之中,夢境里你跳舞尋歡,等數到十的時候你醒過來了,那時候你還能記得自己是誰,但不會記得你以前叫什么名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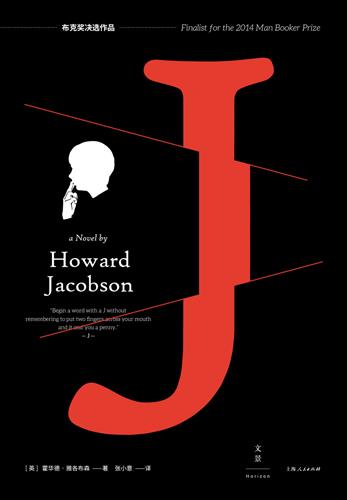
新姓名試圖創建一個不分你我的烏托邦,“所有人都屬于一個快樂的大家庭”,人們相信再也不會出現仇恨,因為所有人已無差別。但現實并未按照設定好的軌道奔向美麗新世界,人們陷入不停地“為了歷史”而道歉卻不知歷史究竟發生了什么的悖論中。若隱若現的噩夢襲來,人們在虛無感中沉浮,為戾氣所籠罩,每個人都變得暴躁易怒,為了一點小事就大打出手……
“當代文學已有太多表達未來恐懼的作品:被摧毀的景觀、被火焰焚燒的社會等等,”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但雅各布森呈現了一種新的憂慮,他將毀滅轉向我們的內心,在那里成為廢墟的是我們的語言、想象力和愛。”
“我從沒見過樂觀的知識分子”——雅各布森認為,小說家有責任講述對未來的悲觀預期,“我總是覺得自己像是《舊約》或古希臘神話中的預言家,恨不得跑到大街上去警告人們即將到來的危險……有人總勸我別那么悲觀,但一個作家的工作就是將它指出來。”
災難會和以前一模一樣地發生
雅各布森1942年生于英國曼徹斯特,畢業于劍橋大學唐寧學院,曾在悉尼大學、劍橋大學等多所大學擔任教職,迄今已出版小說16部、非虛構作品5部。
雅各布森以喜劇創作見長,作品致力于探索當代猶太人在英國的境遇及兩性關系,他的喜劇小說既喧鬧又辛辣,筆法精微,帶有強烈的智性游戲特征。2010年,雅各布森憑借小說《芬克勒問題》摘得布克獎,評委會主席稱贊他的作品“充滿了睿智與幽默、憂傷與感性。它使人大笑,但卻是在黑暗中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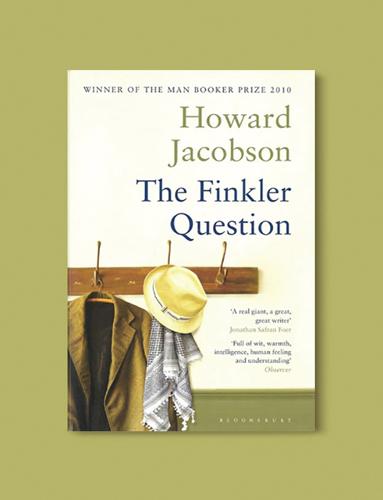
但小說《J》的主題和風格與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華盛頓郵報》評論道,“《J》是雅各布森迄今為止最嚴肅、最令人不安的作品……比起機器統治,雅各布森對人類未來的憂慮更加深邃,他提出一個黑暗、絕望卻被血腥歷史不斷驗證的疑問:仇恨是人類文化的必需品嗎?”
《J》中的男主角凱文是一個獨來獨往的怪人,每次出門前都要強迫癥式地反復檢查門鎖和郵箱,確保外人誤以為他在家,不會伺機闖入。小時候父親曾和凱文玩過一個游戲,只要講出以J開頭的詞語,就要用兩根手指壓住嘴唇。
作為猶太裔作家,猶太人的境遇是雅各布森反復書寫的母題。“J”是書中從未明確提及的“猶太人(Jews)”首字母,具有強烈指向,但也包括“爵士樂(Jazz)”等禁忌之詞。在半隔絕的小屋里,凱文閱讀嚴肅書籍,聽父親留下的爵士樂唱片,他的生活讓鄰居感到迷惑:“他們沒以為他愚蠢,反倒覺得他可能聰明過頭了。不過人類歷史上總有些時候,聰明也就意味著愚蠢。”
凱文想知道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他對周遭一切神經質地敏感,總以為有人要窺視他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愛上了遷居此地的同類愛琳。在復雜而精細的監視網絡中,愛琳借用梅爾維爾《白鯨》的情節說出了她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一直以來亞哈都在追蹤我們。”
隨著小說情節逐漸深入,陰謀論警官和勢利的藝術教授暗中盯上了這對戀人,整個社會就像是一場實驗,作為殺戮的幸存者,艾琳最終選擇與過去和解,但無法忍受命運的凱文卻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社會的每個單元都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我無意追究誰的責任,不管是對是錯,過去的已然過去,什么也不用說了——這點我們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沒有人可以指控,所以也沒有人去彌補,即使彌補是合適的,而且有辦法去彌補。但要是不能從過去總結教訓,過去的意義又是什么——”小說中,雅各布森虛構了一個重要角色:公眾情緒觀測機構的調研員埃斯米,她對官方行動的有效性發出上述質疑,但只得到主管的一句簡短回答——“過去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讓我們可以忘記。”
“巧合”的是,埃斯米第二天上班路上被摩托車撞至昏迷,但在后來的康復過程中,她似乎“開竅了”,認清了社會關系的本質是敵意的對抗平衡。一旦社會發生危機,一個族群總要找個目標來承擔責任。如果“出事”打破了這一平衡,那么只有重新尋找、培養災難幸存者的后裔,創造未來的“仇恨目標”,社會才能復歸平衡。
“哪個國家不是它自己歷史的藏骨屋呢?一些人的春天,就是另外一些人的嚴冬。”穿透娛樂至死的社會中五光十色的泡沫,直視生活的黑暗底色,雅各布森借小說人物之口發出令人震驚的哀嘆——“(災難)會怎么發生呢?和以前一模一樣地發生……”
人:人民周刊 雅:雅各布森
夾雜舊疾的重啟真的是新生活嗎?
人:《J》被視作精彩的災難預言作品,約翰·伯恩賽德將它與奧威爾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相提并論,你如何看待這一評價?
雅:他真是過獎了!那兩本都是具有影響力的小說,但我認為它們比我的作品更側重預測未來,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寫的《J》其實更針對當下。
人:小說中反復出現一句話:“出事——如果真的出過事。”書中人物也發出哀嘆:“(災難)會怎么發生呢?和以前一模一樣地發生……”寫下這些警告時你是怎樣的心態,為何會寫這些?
雅:這只是源于我所相信的——某些殘忍、毫無理性的事情曾經發生過,將來還會再現,而且常以無法接受的方式重現。我們為了防止下一次對人類的蓄意傷害已經忍受了太多,寄希望于此事再也不會發生的態度其實是不負責任的。可怕的事實是,已有災難可能一次次持續再現。“(災難)會怎么發生呢?和以前一模一樣地發生……”,經常發生的還有忽視和恐懼,不只是對他人的恐懼,更是對未知和各種模棱兩可說辭的恐懼。人們想要相信,并且確認自己是某種存在,而達成這種確認的手段卻是消滅他者。《J》道出了某種緊迫性:不只是愛我們眼中的他者,更要接受一個重要觀念:我們眼中的他者也是“我們”。
人:小說開篇,你引出一則狼與狼蛛的對話,具體介紹下這則隱喻?
雅:在那些古老精妙的敘述傳統中,人們常常通過描寫動物行為來揭示人類本性的真相,這能讓我們除去政治或社交因素的干預,直面人類的欲望和動機。我創作了開篇狼與狼蛛的對話,它的寓意很清楚:如果你將一切吃得一點不剩,最后填飽肚子的只剩下你的家人甚至你自己。這也是《J》整部小說所講述的:永遠不要趕盡殺絕,否則你終將引向自我消滅的結局。

5月5日,工作人員在意大利羅馬附近的韋萊特里公墓進行消毒
人:如今新冠病毒肆虐,對眼下這場掃蕩全球的大災難,你有何觀察和思考?
雅:如此規模的大災難后,未來勢必發生變化,但誰也不知道將來會更好還是更壞,因為我們期望更好的變化,試圖在無意義中尋得意義,那樣才能解釋我們經受苦難的目的。《J》中的男主人公凱文,堅信已有的罪惡中不會生出任何好事,他不愿讓施惡者獲得這樣的滿足感,他認為這些人理當被剝奪赦罪機會。但我們在小說結尾,聽到的卻是女主人公愛琳吊詭的聲音,她迎來新啟的生活卻仍充斥著昔日的混亂,這樣夾雜舊疾的重啟真的是新生活嗎?
人:說說《J》中公眾情緒觀測機構工作人員埃斯米這個人物的設定?凱文、愛琳和埃斯米三人在書中的形象比較清晰,那些觀察、監視他們的配角(警長、藝術教授等)在這場社會實驗里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雅:埃斯米是完全虛構出來的,她原本是個很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女人,但惹禍上身,最終變成了一個失去人性、像機器般冷酷的人。那些配角的出現代表著災難發生后出現的各種質疑甚至仇恨的聲音。
人:書中凱文所生活的濱海小鎮魯本港的環境是如何創作出來的?有何隱喻?
雅:我曾經在康沃爾郡生活了多年,當地見聞呈現在小說里我對凱文生活之地的描述中——一片荒蠻原始之地,裹挾著一段暴力且具毀滅性的歷史,常年被謠言、懷疑和盲目的恐懼撕扯著。我無意描述某個真實的地方,這都是腦中想象出來的,但事實上,所有地方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人:小說中你描繪了一座極具科幻感的城市尼科洛波利斯,那里布滿了電子屏和透明汽車,你對眼下急速發展的高科技持怎樣的態度?
雅:我害怕高科技,和過去那些人道主義者一樣,我厭惡高科技導致的去人性化。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眼下大家都隔離在單人間里,互聯網無人性、免接觸的冷冰冰的文化卻成了所有人的拯救。我最討厭那些社交媒體,它們四處散播各種未經核實、缺乏質疑精神的論斷和主張,這是藝術和想象力的大敵。互聯網看似要解放我們,但種種跡象顯示,我們將被它奴役。盡管它允諾將我們聯于世界,但事實上,它驅使人們將自己禁錮在一小塊蒼白無力的屏幕前,沉溺于個人瘋狂而不切實際的幻覺中,彼此聯系的還都是些同類。
人:和諸多反烏托邦作品直接批判權力制度、技術焦慮或機器統治相比,《J》描繪的世界更為日常,你如何看待當下蓬勃的消費主義及流行文化?
雅:消費主義并未引起我的困擾。但人們日益缺乏獨立思想,這一現象讓我感到憂心,社交媒體正是由于人們缺乏獨立想法才流行起來的。流行文化是對我們自由的最大威脅,我甚至可以說,它是對我們文明的最大威脅,流行文化本質上就是不加質疑的眾口一詞。
人:小說中,你借藝術教授之口道出“藝術,恰恰在于冒犯”的“真諦”,如許反諷,也說出了你本人對藝術的看法?
雅:我想,書里那句話算是對概念主義等運動所踐行的藝術創作的中肯描述吧。某種程度上,那些不懂當代藝術語匯的人被激怒了,這正好說明藝術完成了這項工作,換言之,對抗中產階級成了藝術的首要功用。也許我應該支持這種對流行文化的反抗,但這個鐘擺似乎甩得又太偏了。藝術不必立時立刻就能看懂,但也不該竭力追求“高不可攀”。所有高質藝術和思想都處于個人與公眾、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平衡區間,一旦平衡被打破,我們就把藝術給毀了,也毀了我們鑒賞藝術的初衷。

5月1日晚,法國巴黎第5區的多邦東大街,人們觀看在墻壁上放的電影
“喜劇”是殘酷的詞匯
人:你的作品文字機敏俏皮,情節往往有點荒唐可笑,大家常稱你是“喜劇小說家”,但你探討的主題通常又是嚴肅沉重的,例如猶太人的歷史、種族大屠殺、災難等等,創作時如何保持“莊”與“諧”之間的張力?
雅:的確,如果我能游刃有余地掌控藝術,這種張力就是其魅力所在。我喜歡那些開頭戲謔、結尾讓人心碎的組合,反之亦然。我不認為有何主題是喜劇無法處理的,但我個人不喜歡、也不追求創作那種所謂光明的喜劇,我認為喜劇應該是深刻的,它的思想和言行建基于將讀者引向驚恐萬狀的那個爆破點。
人:就如你曾說的,“‘喜劇是殘酷的詞匯”?
雅:沒錯!最好的喜劇將我們帶到災難的懸崖峭壁,并且逼著我們去看。它其實不太討好讀者,悲劇迎合我們的人性需求,與之相比,喜劇更殘酷。在悲劇中,至少我們瞥見了人性的高尚尊貴,但在喜劇中,我們只看見丑陋的獸性。
人:創作小說之外,你曾撰寫專欄、主持電臺節目,你如何看待媒體在當代社會的作用?在眼下這場全球災難面前,媒體應該發揮怎樣的功效?
雅:當下世界,不負責任的大眾流行媒體肆虐橫行,有的倡導陰謀論,有的趨炎附勢,人們從沒這么急迫地需要一個誠信優質的獨立媒體,但它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和懷疑,眼下的時代,沒有什么派別是完全正確的,只是看誰少犯錯而已。媒體需要發出清晰理性的聲音。
人:詩人米沃什曾說:“大眾傳播媒介奇妙擴展,我們的星球每年都在變小,見證著一個難以定義的過程,其特點就是拒絕回憶。詩人感到焦慮,因他感受到,不遠的未來,歷史將化約為電視上播放的,而真理,因太復雜,就算不被完全銷毀,也會被埋葬在檔案室。”遺忘也是你在這部小說中重點處理的主題。
雅:我完全贊同米沃什關于時代拒絕回憶的描述,這也是《J》所探討的。如今的年輕人似乎都已習慣了遺忘,這種失憶癥表現在他們對曾發生過的任何事情都失去了興趣。我們以為互聯網會提供給我們探索歷史更豐富便捷的渠道,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如今的人們只關注眼下。
人:關于遺忘,《J》中那位哲學家表示:無需深究,我們只要說抱歉。“‘說抱歉將我們所有人從相互指責的過往中解放出來,去往一個無可指摘的未來時代。”我記得你有部作品就叫《此刻誰抱歉?》,我們應以怎樣的態度對待歷史上發生的災難,只是“說抱歉”嗎?
雅:我不確定自己曾否見過真正有價值的道歉。大多數時候,致歉者向那些深受傷害甚至毀滅的受害者說抱歉為時已晚,而且誰被授權代表這些受害者接受道歉呢?災難之后我們所期望的是對它的認知——既包括各種文字、信息,也包括深層的理解。《J》非常關注機密及諱莫如深的狀態,當前的各種危機都深受紛繁復雜的秘密攪擾。秘密滋生懷疑,懷疑滋生關于陰謀論的各種猜想,這是個難以打破的惡性閉環。
人:小說中有個角色指出:“仇恨存在于人之外。我把它比作病毒。人們會抓住它………所以我給你的建議是永遠不要去激發它。”有人認為,你在寫作中指出種族仇恨仍在歐洲游蕩,表達了對歐洲的一種隱憂。
雅:是的,這是《J》最集中的一個觀點。對很多人而言,曾激起種族大屠殺的仇恨余毒依然存在,許多人在爭辯“發生了什么”、“沒發生什么”,但卻希望“發生過”或者“它會發生”。種族大屠殺過去才多少年,要是致命而有毒的反猶主義再次出現,沒有什么比這個更讓人絕望的了。
人:面對那些近乎絕望的事態,你通常會從哪里找尋“希望”?
雅:我從各處找尋“云朵的銀邊”——那一線希望。我多愁善感,高度關注個人快樂,甚至到了某種荒謬的程度。即便觀看悲劇氣氛濃烈的歌劇,到了結尾我還是執拗地希望戀人能重聚。但那是我的心,我的頭腦想的卻不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以說,生活經常都是恐怖又令人失望的,但在某些小角落,你必須繼續相信,事實并非如此。
人:對于未來,你最大的恐懼是什么?
這是個大問題。我懼怕流行文化、缺乏獨立主見、輿論一邊倒、烏合之眾、暴民,以及這些人追隨的各種大眾傳媒上的表達。不是只有病毒出現時,人與人之間才需要保持社交距離;這個世界已變得危機四伏,無論到哪里,總聚集著一群烏合之眾。有些人享受流行音樂或體育賽事的大眾狂歡慶典,但我不喜歡。我害怕人群中這種浪潮般洶涌的情緒。在我看來,人們保持一定距離才是安全的,當然,也不是那種遠到各自關在臥室、整日沉溺于社交媒體虛設的幻夢中的距離……兩者之間需要一個平衡。
(感謝楊沁、楊朗協助聯絡專訪,實習記者陳梵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