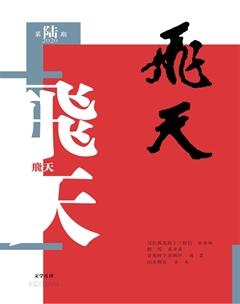我與賈平凹
何勝江
與賈平凹先生相識是在上個世紀,算來已經快二十個年頭了。第一次是我和靖安兄專程到西安拜訪他。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初冬,平凹的朋友提前約好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去他的書房。我和靖安兄前一天晚上從蘭州坐火車,第二天一大早就到西安城了,一下火車我們就搭車直奔他的住處。那時他住在太白南路廣電家屬院。賈平凹是名人,此前我閱讀了他的好多書,是他著作的忠實讀者,用現在人的話說是他的“粉絲”。要去見這樣一位大名人,一路上設想了好多,心情總是忐忑不安的,心想這人肯定是文質彬彬的,大派頭的。想著想著就到了他的樓下,電話聯系,住在六樓左手,他正在書房等著哩。我們急急上到六樓,左手門上貼著一張民間木刻板印的門神像,陳舊的保險門框周圍油漆多處脫落,露出了斑斑鐵銹。我對著門輕輕敲了三下,鐵門上方的貓眼窗打開了,隔過鐵格護欄看到了一張鄉村教師模樣的臉面,隨即門被打開,一口濃濃的陜西腔:“來哩!”一進門,看見室內隨處堆置著各種陶罐、佛像,大書案上一方很大的端硯石內盛滿的清水倒映著墻壁上的“大堂”兩字,整個書房彌漫著古氣。
早就聽說先生不愛多說話,特別疲于和生人進行長時間的語言交流。我們喝著先生親自沏的好茶,聊著聊著,竟意趣情投。他看著我寫的字,我幫他鋪紙調墨;出于心中的愉悅,他欣然揮毫寫了好多書法作品。短暫的接觸,他獨具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精深的學養深刻地打動了我。喝了一天茶,也說了一天話,寫了一天字。時間過得很快,在快樂中我們成了兄弟一般的朋友。
此后的接觸,短信電話經常聯系,有時書寫明信片祝福。我們都是農民出身,我們都喜歡吃從大山的土里長出來的五谷雜糧。這以后,我經常給他帶去通渭的苦蕎面饃饃等。我介紹著自己土里土氣的故鄉,邀請他到我的家鄉來。賈平凹是名人,名人很忙很累;他不缺錢,不缺名,缺的是時間。許多找上門來的人和事總是粘住他,多時讓他集中不下時間來寫作和休息。我怎么能隨便把他邀請到我的家鄉來哩,當時只是說說而已吧。
賈平凹是壬辰龍相,農歷二月二十一日是他的生日。二○○一年,我受邀到西安給他過生日。男人四十九是人生的大坎,好多遠近的朋友為他祝福祝壽,場景自然熱鬧。席間,我又邀他到我的家鄉走走,散散心,看看我那兒的風土人情。這次他應承了,說天暖和了到你那換換空氣,歇歇腦子,去看一下你生活的地方。
二○○一年,五一剛過,我就與平凹先生聯系,直到六月底計劃成行。那時,我在通渭縣糧食局工作,請了一周事假,準備去西安接賈平凹。路途遙遠,還得有個好車去接,不得已只有向靖安兄借車,連車帶司機,從平涼到西安。第二天早上,我和賈平凹及隨行的陜西省教育學院畫家王志平老師一行,經長武、華亭、隆德、六盤山、平川、白銀、靖遠、會寧、蘭州、定西,一路走下來。高山平川,沙漠煤田;長天大日,陽光風雨;觸景生情,笑語歡歌。所到之地,盡興揮毫,留下了很多墨寶。最后他來到了我的家鄉。
前一天我們住平川靖安兄家,定西市委石晶書記是靖安兄的好朋友。賈平凹是有身份的名人,想讓地方上接待得體面些,當時靖安兄便給石書記打了電話,并求平凹先生寫了個字帶著。我們來到定西市后,石書記因剛上任,當天他陪省上老領導考察,便安排接待處的羅小平主任招呼。黃周會副書記趕來認賈平凹這個老鄉,陪同吃了晚飯后便安排我們住到了定西賓館。市上領導忙,石書記晚飯后匆匆到住處看望了一下賈平凹,囑羅小平安排通渭縣委接待。賈平凹怕打攪,早起就往通渭走。
當時,通渭縣委書記張敏政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主持工作的是副書記雷長丁,雷書記有病又不在單位。我當時就給石書記說縣政府鄭紅偉縣長熱心文化,給鄭縣長說說安排接待更好。不巧的是鄭縣長帶著幾個部門的領導到北京出差了,安排政府辦副主任李進林出面作陪。住通渭賓館后,賈平凹要求到農村走走。賈平凹、王志平、李進林、我和司機何東濤一行五人到我生長過的碧玉鄉。原本是到我家去的,司機一腳油門把車開到了碧玉鄉老虎灣山下,就近到了景木岔。這個村莊坐落在老虎灣山腰處,這里又是政府樹立的“121”集雨抗旱工程點。時值初夏,天氣異常干旱,由于村莊地處高山腹地,再加集雨節灌,水肥充足,農戶園中果蔬正長得郁郁蔥蔥。避開了城市的喧囂,在這樣的環境中行走,先生自然高興,在一個用紅漆寫著“隴原第一窯”的集雨窯前我們合了影。
通渭人歷來勤勞,農村的巷道、農家院落都收拾得干凈利落。我們在村子里隨意行走,也沒提前給任何人招呼,一切都是隨機的。時值農忙,村民都上屲干農活去了,莊子里的道上除了幾只貓狗穿過,看不到人影。奇怪的是幾十戶人家的大門幾乎都未上鎖,足見莊風良好。從一家的莊墻根經過時,看到這家的一棵牡丹樹枝從丈把高的墻頭伸出,先生說這家肯定有漂亮女子。我笑了笑,為了驗證先生的話,便推開這家虛掩的大門。走到院子中央,果然從西邊廂房走出個端莊素樸的少婦,手里提著一籃野菜,一邊撿一邊笑著,招呼著我們,沒有一點陌生感。把我們引到東邊的廳堂,給每人倒了一碗泡著香椿皮的滾水。先生朝我笑了笑,我們都會心地笑了。這個家收拾得干凈衛生,院子里的一側靠墻處圍了一個大花園,高大的牡丹樹蓋住了半個院子,園子里眾多的小花簇擁著牡丹樹。
一只大紅冠子的公雞把我們帶到了另一個農家。大門敞開著,黃土院子用糜子做的細掃帚掃得明光發亮。大公雞在廚房門口昂首站立不走了,一位滿頭銀發面容慈祥的老媽媽笑著走來,從門洞往里看,廚臺架板上,碗口朝下錯落地壘起來,一眼看去像纏枝花團一樣。平凹先生不由地走了進去,“藝術”、“干凈”、“衛生”、“科學”,先生的嘴里不住地自言自語著。出門后先生還在不停地念叨,這兒的農民真好。一個扣碗的方法,就讓先生贊嘆不已。
有戶農家的大門是厚厚的榆木板做的,門板的年輪被風雨捶磨得深渠條條;曲線上留下的歲月包漿,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門緊閉著,沒有鎖,但無法敲開。我們正要離開時,一位老翁走來,笑瞇瞇地說,你們在研究我的門嗎?我看你們都是高人,打個賭,誰能打開我家的門,就請喝我的罐罐茶。我們便圍著土門怎么弄都打不開門,而且沒發現有插銷或上鎖的地方。老翁見無著,便讓我們靠一邊,他走到離門不足一尺的地方動了一下墻上的磚塊,大門“咣當”一聲開了。此后老人告訴了這個秘密,說這是祖上為防盜賊偷驢而發明的一種帶有機關的暗鎖,從不傳外人的。哈哈,老翁把我們當自家人了。
先生興致頗濃,感到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他說,你說這里窮,我看比我們陜南富得多,特別是精神上。邊走邊問這里的民俗民風、居家風水、建筑構成等,我告訴他,我們這里農村建宅很講究,從大的風水講,要藏風聚氣,后靠前照。就是說住宅后背要有靠山,門前要有水照,左青龍右白虎相輔相映,山為仁德,水為智慧財源。建筑構成上,什么“四檁四噙口”“四門八窗”“滾椽掛椽”“里滾外掛”等等,按人家的品行德望而定。先生問我,這家客房用椽“里滾外掛”,為何大門上用滾椽不用掛椽?我說,這個很重要,若大門外掛,就是“亂箭射主”,是建筑大忌;且大門內外的照壁、門墩的高低、門的大小等都有講究。進得一家廳堂,先生問:家家廳房掛中堂對聯,而所有對聯都是七言,這有啥講究?我說,我們這兒農村人掛字畫真有講究。廳房是一家請神祭祖、招待貴客的地方,不能亂掛字畫。中堂內容必須選吉慶、祥瑞、陽光、向上的;對作者的人品也有要求,若作者品德不行,所作中堂恐沖犯堂上祖宗神靈,絕不能入室懸堂。在對聯上特別講究字數,以“魯班文公尺”取吉,以“生、老、病、死、苦”的人生過程,取“生”為始,“老”為終,吉數為“七”,求做人做事有始有終之意!先生聽得興奮,怕一時記不住遺忘,便隨身掏出一個小本子記下來。在農家每每見到一些諸如紅泥火爐、鑄鐵火盆(熬罐罐茶用)、水煙瓶、廳堂供器類的老物件,先生都要詳細地詢問使用方法,還不時地讓隨行的王志平老師拍照。
夜幕漸漸降臨,肚子也餓得嘰咕響。先生毫無餓意,還不想回城,我可受不了啦。我想把晚飯臨時定在農家。村子里的農民陸續地從地里往家走,我挨個問了幾家,都說一下子做不出這么多人吃的飯。正愁時,我看到兩個大麥垛旁站著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伙子在看著我們,一問在上初中哩,我便招呼他,說這位先生是你們課本上寫《丑石》的作者賈平凹,和他照個像,你就一定能考個好學校。
在草垛下我給先生和小伙子照了個相(幾年后,我去景木岔,拿著照片找這個小伙子時,他真的已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學)。當時我讓小伙給他媽說給我們做頓飯吃。孩子的媽媽很熱情,放下了家里的活,說家里沒有好吃的,只有黑面和苦蕎面,洋芋這個季節沒有新的,只有出過芽的舊洋芋。我說行,就做“綠蕎面酸棒棒”。雖是舊洋芋,孩子從園子里割了一撮韭菜,精細的刀工,純正的胡麻油,一碟洋芋絲,一碟綠韭菜,炒出了滿院子的清香。小院里,大杏樹下,一張長方茶幾,大家圍了坐定,可口的農家飯上桌了。先生也不客套,大嚼大咽起來,一連吃了三大碗,還直嚷嚷著沒吃夠。臨了他還說:“這頓飯是我大半輩子吃得最美的一頓,在城里有這樣吃的就好了。”還建議我到西安城開個這樣的農家小吃館,保證生意紅火。
在賈平凹先生離開通渭的前一天晚上,鄭紅偉縣長出差從北京回來,和鄭俊清副縣長到賓館看望了賈平凹先生并詳細介紹了通渭縣書畫事業的發展情況。
通渭一行,對先生感觸良多。墻上有字畫,門上有齋名,字畫的格式、內容、書寫者的品行都有講究,“耕讀第”、“居之安”、“厚德堂”,先生看著看著,時不時地發出由衷的贊嘆。住在這窮山僻壤的人們竟然這等酷愛字畫,崇尚文化,真是不可思議。早茶時,先生還讓我再講講通渭,通渭的文化、通渭的人、通渭的事。在陪先生聊天的同時,又陪他走了通渭城里的許多大街小巷,吃罐罐面、喝罐罐茶、抽水煙瓶……我看到了先生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記錄,他說回去要寫個東西。
第二年(二○○二年)的春天,我去西安看望先生,給他祝五十大壽。在他的書房,他讓秘書小施拿來剛出版的一本《美文》雜志,翻開第一頁,遞到我面前說我寫了一篇小文,記錄我們當時的行蹤,作個紀念吧,并在扉頁題詞:“我去通渭,勝江陪我去了多處,相談甚歡,此文小記當時行蹤,以存懷念。”《通渭人家》后來又被《新華文摘》、《讀者》、《書法報》等二十多家報刊轉載,并入編賈平凹《五十大話》等散文集。通渭由此一時在全國出了名:“耕讀之家”、“忠孝為本”、“民風淳樸”、“知法守法”、“翰墨飄香”、“書畫通渭”。記得當年賈平凹去平涼,在金絲猴香煙皮上寫了一篇《柳湖春色》的短文,后來多次被散文選集刊發,雖寥寥數語,對平涼的宣傳影響極大。在散文《通渭人家》中,平凹先生真是說盡了通渭的好話。“正是心里干凈,通渭人處處表現著他們精神的高貴。你可以頓頓吃野菜喝稀湯,但家里不能沒有一張飯桌;你可以出門了穿的衣裳破舊,但不能不洗不漿;你可以一個大字不識,但中堂上不能不掛字畫。”“通渭的孩子以能考上大學為孝子”,誰家的孩子考上大學,就是“誰家的門風好”。“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就連爬在父背上的小兒也會用手指在父親的光頭上寫字”。
平凹先生曾兩次到通渭。第一次是二○○一年七月二日,是從白銀平川一路采風路過,在通渭住了三天,走了碧玉鄉景木岔,寫了《通渭人家》的散文,當時我們接待賈平凹很簡陋。第二次是二○○四年元月,住了一周,主要是散心、寫字。因時近年關,氣候變冷,每當應付完求字、求教、求見者之后,我陪他上清涼山、登筆架山,聊天散步。到我家喝茶時,他見我蓋了新樓房,笑著說:“你還真行,鳥槍換大炮哩。”到家,他幫我鑒定古陶器、古書畫。其中,有一馬家窯紅陶和小洮硯,他喜歡,我便送給了他。他還和隨行者站在我的書房欣賞五年前給我寫的“自有清正之氣——讀勝江書法作品有感平凹己卯”的橫幅。平凹先生說:“現在看來,這字寫的還算灑脫,今天還寫不出來呢。”這天晚上,時任縣委書記鄭紅偉和副縣長盧效英到我家看望賈平凹先生,并一同喝了罐罐茶。
今又是一個七月初,麥浪滾滾時,“我還要來通渭,帶上我那些文朋書友”,“我要讓他們都來一回通渭!”。
記著先生的承諾!
責任編輯 閻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