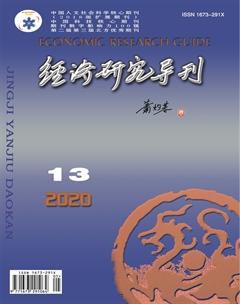大學生留學決策的模糊厭惡
屈博韜



摘 要:近年來,雖然國際形勢愈加復雜,但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數量依然呈高速增長的態勢。針對不同學科的中國學生對自己未來留學的決策。從模糊厭惡的角度進行探討和對比,首先通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影響大學生出國留學的因素進行篩選,之后通過KL散度對這些因素進行探討,進一步確認學生決策方式的模糊性,最后通過埃爾斯伯格的實驗比較不同學科學生的模糊厭惡程度。
關鍵詞:留學決策;模糊厭惡;多元線性回歸;埃爾斯伯格實驗;KL散度
中圖分類號:G648.9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0)13-0134-03
一、文獻綜述
模糊厭惡意指在所有伴隨風險的不確定性中選擇,人們傾向于選擇已知的不確定類型,而不是未知類型。人們厭惡主觀的或模糊的不確定性,甚至討厭客觀的不確定性[1]。
基于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論,人們決策的目的不是為了利益最大化,而是為了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2]。
期望效價理論和主觀期望效用理論所描述的決策行為都是屬于概率思維模式的決策,而Kahneman和Tversky等人描述的啟發式決策都是屬于非概率思維模式的決策[3]。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Richard Thaler所創立的行為金融學,通過探索有限理性、社會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他展示了這些人格特質如何系統地影響個人決策以及市場成果。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從行為經濟學中的模糊厭惡方面入手,來分析大學生選擇出國進一步深造時面臨風險時的一系列反映原理。
二、計量檢驗
(一)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我們需要確定在影響出國留學的因素中,是什么因素的影響最為重要。
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來對因素進行描述。當多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是線性關系時,所進行的回歸分析就是多元線性回歸模型[4]。
我們將大學生出國留學意向的影響因素分為五個方面,包括學生的主觀意愿與學習成績、家庭因素、教育質量和就業。
對出國留學和以上因素的問題均設計為兩個選項,是或否,并對是賦值為1,否賦值為0。然后,對以上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1.就財經大學的統計結果而言(如表1所示)。根據表1中的統計結果,我們看到,學生的主觀意愿、學生的家庭經濟、國外教育質量和就業薪酬四個因素的顯著性水平 P<0.05,這些因素的影響全部與出國留學成正相關關系。這其中,就業薪酬、學生的家庭經濟因素,以及學生的主觀意愿是有效因素中排名前三的因素,系數分別為0.65、0.53、0.34。
2.就綜合高校的統計結果而言(如下頁表2所示)。根據表2中的統計結果可知,在有效因素中,占比重最大的前三項因素分別為國外教育質量、薪酬和家庭經濟狀況,分別為0.61、0.59和0.5。
對這兩份問卷綜合來看,就業薪酬和學生的家庭經濟因素一直都是學生出國留學時考慮得最多的兩個因素。
(二)通過KL散度對學生模糊決策的分析
我們希望通過比較學生出國前對自己畢業歸國可能獲得的薪資與留學歸國的學生目前在就業市場的實際薪資做出比較,通過描述兩種數據之間的差異來證實我們的假設是準確的。
Kullback-Leibler散度是兩個概率分布間差異的非對稱性度量。在信息理論中,相對熵等價于兩個概率分布的信息熵的差值[5]。
相對熵就是用來衡量這種情況下平均每個字符多用的比特數,因此可以用來衡量兩個分布的距離,即:
當兩個隨機分布的差別增大時,它們的相對熵也會增大[6]。也就是說,相對熵的值越大,我們就可以證明現實與期望的差距越大。
(三)數據驗證
在財經大學的問卷中,我們發現學生對于歸國就業薪資的預期遠遠高于了實際薪酬。尤其是在10萬~25萬元左右部分,遠遠高于實際薪資的平均水平。
在2017年,我們以5萬、10萬、15萬、20萬、30萬、40萬的數據為例,P1(x)=19%,Q1(x)=34%… … … …P6(x)=5%,Q6(x)=2%,Q代表實際薪資在畢業生中調查人數的分布比例,P代表期望薪資在畢業生中調查人數的分布比例。最終我們得出:
KL(P||Q)=0.55(2017)
KL(P||Q)=0.32(2018)
在綜合高校的問卷中我們發現,綜合類高校學生對于出國留學后的薪資預期雖然與實際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相對來講明顯好于財經類大學的學生。并且,過高的預期往往集中在10萬~20萬的區間,而不是大部分區間。
同樣的,我們對2017年和2018年的數據分別進行KL散度的計算,得到了如下結果:
KL(P||Q)=0.25(2017)
KL(P||Q)=0.17(2018)
綜合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財經類大學或者是綜合類及理工類學校,學生對于出國留學后薪酬匯報的期望明顯高于實際水平。對于我們的假設,這些過高的薪酬期望確實能夠證明,學生在做出出國留學的決策時,更多基于的是非理性的決策而非完全信息下的理性決策。
三、高校學生模糊厭惡實驗
(一)學生留學決策預期投入產出的平均水平
跟據我們提取出的兩個因素來看,出國留學可以近似于看作一個投資方案的問題,那么家庭經濟的問題就是投資的成本,而未來就業獲得的更好薪酬就是投資收益,我們希望知道在成本付出多少和投資收益在達到多少時學生愿意對出國留學進行投資。我們利用計算加權平均值得到:
對于財經大學,在出國讀研給家庭五年收入帶來的經濟負擔在時59.55%,并且在薪資水平上浮21.7%時,學生會選擇出國留學。
對于綜合類高校,在出國讀研給家庭五年收入帶來的經濟負擔在52.53%時,并且在薪資上浮水平均值達到16.5%時,學生會選擇出國留學。
(二)實驗設計
我們仿照埃爾斯伯格悖論的實驗[7],設計了如下實驗:
首先,我們假定了兩種情況:第一,不選擇出國,即選擇不付出成本,也沒有收益,表示為pd=?滋(0)。第二,選擇出國,但是薪資上浮和家庭經濟狀況下降是否會超過學生的平均期望的概率未知。我們將符合預期的狀況表示為pd=?滋(1)。
針對第二種情況,我們給出了四種概率?茁1、?茁2、?茁3、?茁4,分別為20%、40%、50%、80%。觀察在不同的概率下,學生更偏向于選擇出國或者是選擇留在國內讀研。對于出國留學的結果,?茁所代表的概率代表著投入產出使學生感到滿意可能性,從理性的角度上來說,一旦學生認為?茁>50%,就應該選擇出國留學。
但事實上,我們收集的數據顯示,由于先驗概率的存在,大部分學生往往在選擇了主觀認為在?茁>50%時,才更偏向于做出出國留學的決策,而在?茁=50%時,學生更偏向于選擇在國內讀研。
根據我們在財經類大學收集的結果(如表3所示),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在?茁=50%時,選擇出國留學和國內讀研的人數接近1∶2。而實際上,期望效用在?茁=50%時是相等的,即人數比例應該為1∶1。這充分說明,即使期望效用相等,學生依舊偏向于不選擇出國留學,學生的決策確實是模糊厭惡的。
根據我們在綜合類高校收集的結果(如表4所示),同樣,在?茁=50%時,選擇出國留學和國內讀研的人數依然相差較遠,證明了學生對出國留學的模糊厭惡性。
從50%的概率比來看,財經類大學學生選擇出國占比34.58%,而綜合類高校選擇出國占比30.32%。由此可以看出,與財經大學不同的是,綜合類高校的學生對于出國留學似乎更加保守,模糊厭惡的現象更加明顯。
四、結語
綜合以上我們發現,財經類大學的學生相對于其他兩校的學生,對于薪資的期望水平明顯過高。也就是說,模糊厭惡的假設是成立的。而從模糊厭惡的程度上來看,財經類大學的學生也對于出國留學更加熱衷,模糊厭惡程度相對更低,即對風險有更高的偏好。
參考文獻:
[1] ?魏華穎,曾湘泉.海外留學歸國人員就業的微觀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4,(10):84-86.
[2] ?姚志均,劉俊濤,周瑜,劉文予.基于對稱KL距離的相似性度量方法[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11):1-4.
[3] ?張鳳華.模糊決策中的決策偏好再探[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3,(6):884-888.
[4] ?南開大學課題組.中國90后大學生留學狀況調查:基于11所高校和9加留學機構的調研[J].世界教育信息,2013,(10):53-57.
[5] ?林越,劉廷章,黃莉榮,奚曉曄,潘建.基于雙向KL距離聚類算法的變壓器狀態異常檢測[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8,(4):20-26.
[6] ?魏景璇.基于KL距離的微博突發話題檢測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5.
[7] ?唐越越.風險厭惡與模糊厭惡淺析[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