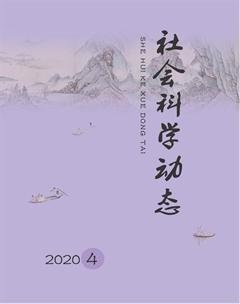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的易卜生翻譯與研究
劉婭
摘要:自20世紀初易卜生及其作品傳入中國,其思其作被中國學者、藝術家反復研討、搬演、教學、傳播,已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易卜生翻譯與研究更是數度出現熱潮,除了涌現出一批關于易卜生的譯著,在易卜生戲劇的總體研究、文化學研究、倫理學研究、地理學研究、心理學研究、生態學研究、詩學與美學研究、接受學與比較學研究等諸多方面出現大量成果,形成“中國易卜生學”的基本格局。然而,關于易卜生的翻譯和研究仍有很大空間:首先是需要從挪威語原著譯出《易卜生全集》;其次是對中國易卜生戲劇演出史進行系統地研究;再次是建立系統全面的中國易卜生研究數據庫,并在此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研究;此外應密切關注國外研究動態,在理論研究上取得突破。
關鍵詞:易卜生;易卜生翻譯;易卜生研究;中國易卜生學
無論在挪威文學史還是在世界戲劇史,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都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之后,近百年來易卜生的作品得到中國文化藝術界的高度重視,對中國現代劇作家群體產生了重要思想啟迪和藝術示范作用。無論是歐陽予倩、田漢,還是洪深、曹禺,他們都曾宣稱自己要做一個“中國的易卜生”。歷經幾代人的研究、闡釋、創化、演繹、教學、傳播,易卜生的思想與藝術,已成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國人的精神與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新時期以來,中國學者在易卜生翻譯與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新的進展,呈現出百花齊放、星火燎原之勢,值得進行全面而系統地梳理與研究。
易卜生在中國的接受情形,譚國根在《易卜生在中國(1908—1997):關于評論、翻譯和演出的釋評性文獻》中曾進行過初步的統計。而在1997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國學者對易卜生的研究逐漸走向國際,也更加多元化。據統計,新時期國內關于易卜生的譯著與專著有三十多種,其中譯著17種、專著及論文集20種(英文著作3種)。據“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顯示,以“易卜生”為名,按“篇名”檢索,有論文526篇。以“易卜生”為名,按“篇名”檢索,有博士論文8篇、碩士論文43篇,研究的對象以易卜生對國內作家的影響居多,也涉及其詩歌與后期戲劇。何成洲在《新中國60年易卜生戲劇研究之考察與分析》一文中,對新時期以來部分易卜生研究的狀況進行了深入分析,對筆者撰寫此文亦有啟發。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易卜生作品翻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易卜生作品翻譯充滿生機。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易卜生文集》(8卷本)包含易卜生25部劇作,除采用翻譯家潘家洵的全部精當譯本,并加入了此前缺漏的劇本譯本,還收錄了易卜生部分詩選及文論譯本,附錄了6篇國外學者“論易卜生”的文章和《易卜生年表》,是相當全面地介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重要文集。此后,國內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易卜生的生平和劇作選集: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易卜生戲劇選》(潘家洵譯);200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易卜生精選集》;2006年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易卜生戲劇集》(3卷本),收錄了潘家洵、蕭乾和成時翻譯的易卜生劇作16部;201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易卜生戲劇選集》。
除了易卜生劇作的翻譯,國內學者還翻譯出版了易卜生生平、書信演講、詩歌及國外學者研究易卜生的著作和論文。1982年中華日報社出版《易卜生傳》(愛德伍德·貝爾著,杜若洲譯),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戲劇大師易卜生》(哈羅德·克勒曼著,蔣嘉、蔣虹丁譯),2005年海燕出版社出版《易卜生》(明斯基著,翁本澤譯),對易卜生的生平及其作品進行了介紹和評述。1982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易卜生評論集》(高中甫選編),匯集一些從各個角度分析和評論易卜生的、具有代表性的論文28篇。201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書信演講集》(汪余禮、戴丹妮譯),是國內第一部系統介紹易卜生書信演講的著作,涵括了易卜生從青少年時代到老年的近三百封書信和十余篇演講,對于深入了解易卜生的人生經歷、內心世界、精神個性、核心思想等具有重要參考價值。2013年世界圖書出版社出版《易卜生詩歌譯介與研究》(袁藝林著),翻譯了約翰·諾瑟姆英譯本《易卜生詩集》168首詩歌,為國內易卜生詩歌和詩劇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此外,2004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閣樓里的女人——莎樂美論易卜生筆下的女性》(馬振騁譯)展示了女作家路·莎樂美對易卜生戲劇人物的詩性闡釋。200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易卜生——藝術家之路》(比約恩·海默爾著,石琴娥譯),廣博而深入地論述易卜生寫作生涯各個時期的作品,對易卜生復雜多變而富有挑戰性的戲劇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2016、2017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易卜生的工作坊》(汪余禮、黃蓓譯著)和《易卜生評傳》(埃德蒙·葛斯著,王閱譯),通過介紹國外學者對易卜生的評論和研究,為國內學者進行易卜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此外,還有大量關于易卜生其人其作的論文被翻譯過來,如1995年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易卜生研究論文集》(孟勝德、阿斯特里德·薩瑟編選)和《二十世紀的西方易卜生批評》(艾羅爾·杜爾巴赫著,戴丹妮譯),分別介紹了從西方早期到當代的易卜生研究方法,對西方的易卜生研究進行了學術梳理。馬丁·艾思林的《易卜生與現代戲劇》則指出易卜生的作品對現代戲劇各流派的發展都有所貢獻,可以被視為整個現代戲劇運動的首創者和源頭之一。①
從以上易卜生相關翻譯統計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對易卜生作品及相關研究的翻譯不再僅僅局限于對其某些劇本的翻譯,而是擴展到了對易卜生詩歌、文論、傳記及其書信演講的翻譯,給中國學者和讀者呈現出了一個更完整、更加多面化的易卜生,也為易卜生研究提供了更多更直觀的素材。除此之外,相關譯著還涉及到西方對易卜生的研究和評論,介紹了西方學者對易卜生研究的現狀和觀點,也讓國內學者能夠有所了解和借鑒,能夠更好地與國際易卜生研究接軌。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易卜生研究
中國現代文化對易卜生思想接納、融化的重點,經歷了從“個人主義”、“反叛主義”、“人道主義”到“自審主義”的嬗變。最初易卜生是作為一名具有先鋒意識的思想家和革命批判者傳入中國,十分契合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反封建、反資本主義、反法西斯主義和追求個人自由。因此,易卜生更多的是被當作一名社會問題劇作家和現實主義大師而得以傳播與被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對易卜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有了更廣闊、更多元化的探索,在易卜生戲劇的總體研究、文化學研究、倫理學研究、地理學研究、心理學研究、生態學研究、詩學與美學研究、接受學與比較學研究等多個方面,涌現出了一大批重要的學術成果。
(一)易劇總體研究
中國學者研究易卜生,最初主要關注的是其“社會問題劇”和社會哲學思想,側重對其中期戲劇中的社會批判內容和社會思想進行研究。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茅于美《易卜生和他的戲劇》,對易卜生及其作品進行了總體研究,除了對易卜生的生平作了詳細介紹,還對易卜生戲劇的思想、藝術成就展開了深入的分析。2002年華夏出版社出版了王忠祥的《易卜生》,該劇融匯了作者長期從事易卜生研究的重要心得。新時期以來,學者們更加關注易卜生的中期社會問題劇,如王忠祥的《易卜生“社會問題劇”舉隅》認為易卜生“社會問題劇”體現了易卜生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藝術;何成洲從“語言形式、結構技巧和美學觀念”等方面分析了易卜生社會問題劇對中國話劇所產生的影響②;周凌楓則指出“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并沒有過時,在今天同樣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深刻的社會意義”③。除了其社會問題劇,研究者還特別關注“易卜生主義”。在《關于易卜生主義的再思考》一文中,王忠祥認為所謂的“易卜生主義”,其實是一種易卜生式的人道主義,一種審美的人文主義。汪余禮強調易卜生的“自審精神”,在《易卜生晚期戲劇與“易卜生主義的精華“》和《重審“易卜生主義的精髓”》兩文中,他從易卜生戲劇的內在精神與藝術追求兩個方面,重新考察“易卜生主義”,認為易卜生晚期戲劇更能體現易卜生主義的精華,進而指出“自審 ”是易卜生主義“活的靈魂”,易卜生最精粹之處就在于靈魂自審和藝術自審,“雙重自審”使易卜生晚期戲劇達到了“現代主義與先鋒主義完美結合的境地”。
(二)易卜生及易劇的文化學演究
易卜生不屬于某一個時代和一個國家, 而屬于所有的時代和全世界,對不同國家的文化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對中國的現代文化有著重要的推進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多次召開學術會議,探討易卜生及其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意義。1999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易卜生與現代性:易卜生與中國國際研討會”并出版論文集《易卜生與現代性:西方與中國》,分“易卜生與現代性”、“易卜生與中國”和“易卜生作品新解”三個版塊,對易卜生的文學創作進行了探討。為紀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2005年5月,在武漢召開了“易卜生戲劇的自由觀念——中國第三屆易卜生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國際視野下討論易卜生戲劇與婦女解放、道德進步、政治獨立、經濟改革之關聯等學術問題,“涉及到易卜生戲劇與中國自由進步、同國際學術界的聯系”等話題。2009年6月,在上海召開了“跨文化的易卜生國際研討會”,討論易卜生作品在不同文化中的研究和傳播,交流從不同文化視角研究和改編易卜生作品的成果。此外黃小蘋、李貴蒼以會議論文集《易卜生與現代自我概念》為基礎進行話語分析,從政治話語和遮蔽/解蔽話語兩個角度,分析易卜生戲劇在現代自我話語中的跨文化重構,反思現代自我話語給易劇重構帶來的啟示。李銀波、蘇暉的《論德國文化對易卜生戲劇創作的影響》從跨文化傳播角度,探討德國文化對易卜生戲劇創作的影響,認為其戲劇具有鮮明的德國文化烙印。
(三)易劇易詩倫理學研究
注重倫理闡釋與強烈的現實關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易卜生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聶珍釗《易卜生戲劇在中國及其倫理價值》一文,認為易卜生戲劇在中國傳播的價值集中體現在倫理價值上,離開了倫理思考就無法對易卜生戲劇進行深入分析;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是倫理道德劇,蘊涵著強大的道德力量④。鄒建軍《易卜生詩歌的倫理主題》一文,從倫理與道德的角度,深入探討易卜生詩歌中的倫理與道德因素,及其對于文學的意義與價值⑤。杜雪琴、鄒建軍以易卜生長詩《在高原》主人公身上“五種倫理身份的糾結為著力點,分析其在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困惑及其體現的悲劇精神”⑥。此外,還有不少論文從倫理學角度對易卜生作品進行細讀,如曹山珂《人生長恨水長東——〈群鬼〉的生態倫理解讀》、蔣文穎《女兒”或“妻子”:論海達·高布樂的倫理身份與倫理選擇》、楊革新《倫理責任與“生活的樂趣”:海倫·阿爾文的倫理困境》、李銀波《易卜生筆下凱蒂琳形象的斯芬克斯因子與倫理選擇》、袁運隆《從家族利益到國家政治——〈覬覦王位的人〉倫理沖突的核心》和段漢武《論海特維格之死——對〈野鴨〉的倫理學解讀》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學術見解。
(四)易劇易詩地理學研究
文學地理學批評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由中國學者提出來的一種研究方法,在易卜生研究領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鄒建軍、胡朝霞主編的《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易卜生詩歌研究》收錄三十多篇論文,探討易卜生詩歌中豐富的地理因素與濃郁的地方色彩,著重研究地理景觀、地理意象、地理生態、地理空間、地理基因,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重要問題。杜雪琴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專著《易卜生戲劇地理空間研究》,集中探討了易卜生劇作中建構的五重地理空間與劇作中存在的深層問題。胡朝霞、鄒建軍關于易卜生長詩《泰爾耶·維根》中所呈現的“倫理景觀”及其結構以及獨特的審美意義的探討,也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⑦。
(五)易劇心理學研究
易卜生戲劇一直與社會改革、社會批判之類的觀念,密切相關。但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學者開始通過弗洛伊德的視角去解讀易卜生后期那些往往使人陷入困惑的“神秘劇作”。李兵專著《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心理現實主義劇作研究》借用弗洛伊德的論點,解讀了易卜生從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轉向“心理現實主義”的原因,以及這一重大轉變的歷史契機和個人復雜的內心過程。此外,有學者運用不同的心理學理論對易卜生的作品進行了個案分析。如張春蕾的《穿越現實腹地的理想追尋》指出易卜生的《野鴨》開啟了此后一系列心理戲劇和象征戲劇的源頭;周馥婧從“女性的自我犧牲情結”這一心理現象入手,探討了《玩偶之家》中的女性形象;王天璐對“幻想浪漫并且想要擁有獨立權力的海達·高布樂進行了人格特征分析”;李定清以《布朗德》和《培爾·金特》兩劇中主人公的自我精神建構過程為例,深入地解析了易卜生戲劇中“自我”觀念的神秘性。
(六)易劇生態學研究
隨著21世紀生態文學批評的興起,學者們也開始從生態角度對易卜生作品進行全新的解讀。2009年5月,在武漢第一次召開以生態為主題的易卜生研討會,圍繞易卜生戲劇的生態思想、易卜生戲劇的生態倫理價值以及對易卜生戲劇的生態評價等議題展開,并出版《易卜生創作的生態價值研究:綠色易卜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內學者對易卜生戲劇從不同生態角度進行了解讀,汪余禮的《易卜生晚期戲劇中的生態智慧》從生態學的視角來分析易卜生晚期戲劇中的生態智慧,認為易卜生晚期戲劇凝聚了極為深邃的生態智慧和非常深遠的人學關懷。他以《建筑大師》中所體現的生態思想為例,指出易卜生“主張藝術、哲學和宗教融合為一個新的范疇和新的生命力,從而為人類詩意地棲居于天地神人的和諧整體中暗示了方向”。姜小衛則認為在《人民公敵》這部歐洲戲劇史上的第一部生態戲劇中,“易卜生展示了環境倫理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民主以及大眾啟蒙之間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 揭示更為深刻的環境倫理觀念”⑧。劉富麗的《易卜生詩歌的生態倫理意蘊》通過分析“絨鴨”、“鳥與捕鳥人”和“一朵玫瑰”這三首詩中的自然意象所蘊含的生態倫理內涵,解讀了詩人身上那種超越其時代的生態思想。
(七)易劇詩學與美學研究
國內易卜生研究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更加關注易劇的審美學研究,包括詩學研究與美學研究。2002年9月,在上海召開了“易卜生與中國:走向一種美學建構”國際研討會,并出版論文集《易卜生與中國——走向一種美學建構》。會上有學者指出,從藝術上接受易卜生并超越易卜生的戲劇藝術程式,是中國戲劇藝術家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重要任務。王寧在《易卜生劇作的意義重構》《作為藝術家的易卜生:易卜生與中國重新思考》《超越“易卜生主義”》《易卜生與世界主義:兼論易劇在中國的改編》等一系列文章中,從戲劇藝術本身來探討易卜生的成就,提出“易卜生化”的美學建構這一命題,呼吁一種“美學轉向”的出現。劉明厚《真實與虛幻的選擇——易卜生后期象征主義戲劇》一書,在總瞰易卜生戲劇創作整體和歐洲象征主義運動的基礎上,對易卜生后期劇作分別作出具有獨到見解的論析,認為象征主義戲劇是易卜生戲劇創作的又一個高峰。鄒建軍《易卜生詩劇研究》一書共收錄易卜生早期詩劇研究論文36篇,主要研究對象為易卜生早期創作的11部詩劇,認為易卜生早期詩劇創作的實質,即民族浪漫主義與時代精神的詩劇化,以及凸顯其諷喻現實、探究人性的歷史性和哲理性的總主題。汪余禮《易卜生晚期戲劇的復象詩學》一文,闡析了易卜生晚期戲劇在審美形式上的獨特創構和審美效果上的高妙境界。此外,汪余禮用審美感通學批評的視角與方法來解讀易卜生晚期戲劇,出版專著《雙重自審與復象詩學——易卜生晚期戲劇新論》,發現并著重論述了易卜生后期八劇貫穿始終的主軸(即“雙重自審”),由此闡釋了互文性與現代性等重要問題;他還提煉、抽繹出易卜生晚期戲劇的“復象詩學”,論述了易卜生晚期戲劇所具有的獨創性與先鋒性問題。
(八)易劇接受學與比較學研究
研討易卜生與國內外劇作家的深層關聯,尤其是藝術家易卜生在中國的接受與影響,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易卜生研究的又一重點。王忠祥《易卜生戲劇創作與20世紀中國文學》一文,全面系統地探討了易卜生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以及對本土文學話語和藝術風格的革新所產生的作用;同時探討了中國現當代作家是如何將吸收易卜生精神精華和弘揚中國文學優良傳統有機結合起來的問題。何成洲《易卜生和中國現代戲劇》一文,將20世紀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分為三個階段,并從歷史、文化和文學的角度討論曹禺、田漢等中國戲劇家對易卜生的接受,深入地探討了易卜生與中國現代戲劇的關系。陳惇和劉洪濤選編的《現實主義批判——易卜生在中國》搜集了從20世紀初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的關于易卜生研究材料,梳理了中國接受易卜生及其文學創作的歷史軌跡。此外,還有一系列關于易卜生在中國的接受現象的論文,如《魯迅·胡適·易卜生》《從“啟蒙”到“立人”:魯迅對易卜生的接受》《曹禺與易卜生》等。易卜生與國外戲劇家的關系問題也受到了研究者關注,田民認為“莎士比亞對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畫對易卜生所產生的影響是深刻的”⑨;孫惠柱將同是挪威人卻獲得諾貝爾獎的比昂遜與易卜生進行了比較,指出“兩人文體越是相似,他們個性和寫作內容差異也就越明顯”;楊挺指出“易卜生的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和象征主義手法都對奧尼爾的晚期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吳學平分析了“王爾德接受易卜生影響的文化境遇與內在心理機制”;楊建認為易卜生是喬伊斯的“精神上的父親”,對喬伊斯的文學創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易卜生研究的深度、廣度和新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易卜生研究成果百花齊放、建樹頗多,易卜生的作品與思想研究已成中國現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系列國際性易卜生研究學術會議,提升了國內易卜生研究的水平,也擴大了國際影響。中國的學界泰斗已經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易卜生學”,與國際的易卜生研究也在進一步的接軌和融合。
三、易卜生翻譯與研究的發展空間
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從報刊到書籍到劇場、從北方到南方到中部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易卜生研究非常活躍,不少學者走向國際,在擴大國際影響的同時,也提升了國內易卜生研究的水平。在此過程中,王忠祥、王寧、譚國根、聶珍釗、何成洲、鄒建軍、汪余禮、杜雪琴等作為中國易卜生研究的領軍人物,主持了多項易卜生研究項目,組織了多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中國易卜生研究及中國“易卜生學”的建構,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與此同時,中國易卜生翻譯和研究還存在不少缺失和不足,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比如:從挪威語原著譯出《易卜生全集》;對中國易卜生戲劇演出史進行系統研究;建立系統全面的中國易卜生研究數據庫,并展開進一步的研究;密切關注國外研究動態,在易劇理論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服務于中國現代戲劇理論建設的同時,擴大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