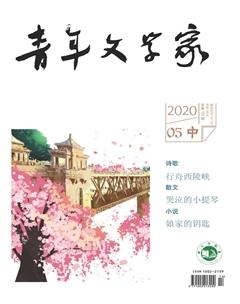《金瓶梅》的匈牙利傳奇之旅
王雪彤 王治江
基金項目:該文為2019年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文化典籍在匈牙利的翻譯和傳播研究”(項目編號:HB19YY005)的階段性成果。
摘 ?要:匈牙利的《金瓶梅》翻譯和傳播可謂傳奇之旅。匈語《金瓶梅》轉(zhuǎn)譯自庫恩1930年的德語節(jié)譯本,比歐洲最早的譯本晚了將近一個世紀之久,比德語譯本也晚問世了半個多世紀。自60年代《金瓶梅》翻譯成匈牙利語后,7次再版,并被改編為話劇和廣播劇搬上匈牙利舞臺和電臺。《金瓶梅》超越了《紅樓夢》等中國名著,成為匈牙利最受讀者歡迎的中國古典小說。匈語全譯《金瓶梅》事業(yè)仍在繼續(xù),《金瓶梅》的匈牙利之旅也遠沒有結(jié)束。
關(guān)鍵詞:《金瓶梅》;匈牙利;翻譯和改編
作者簡介:王雪彤(1992-),女,河北唐山人,華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碩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區(qū)域與國別研究;王治江(1965-),男,河北唐山人,華北理工大學匈牙利研究中心主任,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區(qū)域與國別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14-0-02
《金瓶梅》的匈牙利之旅并非始自中國母港,而是經(jīng)由德國這個中轉(zhuǎn)站開始的。1928年,德國翻譯家基巴特(Otto Kibat)的節(jié)譯三卷本《金瓶梅》第一卷在德國出版。1930年,庫恩(Franz Kuhn)的德語節(jié)譯本《金瓶梅:西門及其六個妻子的冒險故事》在萊比錫出版。該譯本被轉(zhuǎn)譯成了多個歐洲語種,如1939年米奧爾(Mernard Miall)的英語版《金蓮》(The Golden Lotus)[1],對《金瓶梅》在歐洲的廣泛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當時由于缺乏可以直接從漢語原版翻譯中國典籍的翻譯家,自德語版本轉(zhuǎn)譯便成了歐洲通常的做法。這個通常的做法也成了匈牙利中國古典文學早期翻譯的傳統(tǒng)。千呼萬喚始出來,匈語《金瓶梅》終于在上世紀60年代問世了,從此開啟了它在匈牙利的傳奇之旅。
一、《金瓶梅》的匈語翻譯
50、60年代,匈牙利歐羅巴出版社制定了規(guī)格龐大的中國文化典籍出版計劃,《金瓶梅》也在計劃之內(nèi)。當時唯一能直接從漢語翻譯中國古典小說的合適人選漢學家陳國教授正忙于《西游記》的翻譯,因此匈牙利也不例外地延續(xù)了通常的歐洲做法,以庫恩的德語版本作為源語文本進行轉(zhuǎn)譯[2]。
1964年,匈牙利翻譯家馬特拉伊·托馬什(Mátrai Tamás)以庫恩的德語譯本為源本,翻譯了匈語《金瓶梅》,小說中的詩詞則由女詩人普勒·尤迪特翻譯,書名為《富人家中的美女們》或《豪門艷婦》[3],由歐羅巴出版社出版。著名漢學家杜克義為該譯本撰寫了《后記》。
后又在1968、1971、1973和1978年再版了4次。1983年,阿卡迪亞(Arkádia)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匈語《金瓶梅》。十年后,法藤阿爾斯(Fátum-ars)出版社于1993年再次出版該書,副標題是“十六世紀中國無名作家的小說”。1971年出版的第一卷,收錄了前28章,1973年出版的第二卷,收錄后21章,兩卷共計49章。
由于當時歐洲一直也沒有其他語種的全譯本,德語全譯本是1983年才出版,法語全譯本是1985年出版,英語全譯本是2006年出版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到目前為止,在匈牙利還沒有匈語《金瓶梅》全譯本問世。因此,轉(zhuǎn)譯自德語的《金瓶梅》雖是節(jié)譯本,在匈牙利仍受到了讀者的普遍歡迎,甚至超過了《紅樓夢》等其他中國古典名著,成為在匈牙利最流行的中國古典小說。在這種情況下,1964年版譯本一直到了1990年后依然被一再重印,成為這個時期以后在匈牙利唯一再版的中國古典小說[2]。
二、《金瓶梅》在匈牙利的改編
《金瓶梅》在匈牙利先后被改編為話劇和廣播劇長時間上演和播出。
1984年,匈牙利“最偉大的一代”漢學家、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家陳國(Barnabas Csongor)將《金瓶梅》改編為話劇,搬上舞臺演出一百五六十場[4]。陳國是匈牙利著名漢學家,曾任羅蘭大學東亞系主任長達20年之久,也是匈牙利早期唯一直接自漢語原著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家,他曾完整翻譯《水滸傳》和《西游記》,并翻譯了大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著名詩篇。
《金瓶梅》在匈牙利能夠搬上舞臺,完全得益于布達佩斯的達麗雅劇院一項外國古典戲劇的長期演出計劃,劇院導演考西米爾·卡羅伊計劃每年在該劇院上演一臺外國古典戲劇,從1958年起已經(jīng)上演了20多臺。應(yīng)卡羅伊導演之邀,1984年初,陳國依據(jù)原著,用時3個月將《金瓶梅》改編為話劇,經(jīng)過3個月的排練,當年7月匈語話劇《金瓶梅》便在達麗雅劇院與觀眾見面了。自搬上舞臺共演了150-160場[4]。
話劇的開場形式頗具中國神話色彩,序幕中一位仙人首先登場,向觀眾介紹故事的梗概,最后是判官傳召西門慶的妻妾登場,她們輪流申訴潘金蓮如何害死了丈夫西門慶,隨著判官一句“我想看看事實”,劇情就此展開。而劇中的色情場景則通過幻燈投影舞蹈片斷做了象征性的交代。[5]
《金瓶梅》還被改編為系列廣播劇,在匈牙利電臺連續(xù)播出了好幾個月[2]。
三、未竟的事業(yè):陳國全譯《金瓶梅》
陳國20多年前就已經(jīng)著手了《金瓶梅》的匈語翻譯。1984年,他應(yīng)布達佩斯達麗雅劇院導演的邀請,直接依據(jù)漢語原著將《金瓶梅》改編為話劇在舞臺演出,場場爆滿,經(jīng)久不衰,前后上演了150多場。可以說,這次戲劇改編開啟了陳國翻譯《金瓶梅》全書的漫長歷程。直到幾年前,已是90歲高齡的陳國仍在翻譯著《金瓶梅》。
陳國本想把《金瓶梅》作為自己的收官之作,已經(jīng)譯完了全書,可惜未待他完成譯稿的最后校訂,沒有來得及看到他翻譯的匈語版全書《金瓶梅》在匈牙利出版,便帶著永遠的遺憾于2018年3月去世。
匈牙利翻譯家在中國文學典籍翻譯中采取了以歸化為主的翻譯策略,尤其是自德語版本轉(zhuǎn)譯的作品實際上是經(jīng)過了“雙重歸化”的過程,如對《金瓶梅》中的色情描寫等不適合匈牙利文化的內(nèi)容進行了嚴格的“凈化”處理,一方面在德語版本已經(jīng)大量刪減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刪除,另一方面則對于那些沒有刪除的性愛描寫進行了高度“隱喻化”處理[2],在戲劇改編中也采取了象征性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
匈牙利“最偉大的一代”漢學家和翻譯家杜克義親自為翻譯撰寫后記,陳國改編話劇,90年代后中國古典小說在匈牙利呈現(xiàn)出了衰弱的趨勢,但是《金瓶梅》卻被重印,并繼續(xù)創(chuàng)作著它的全譯本,充分說明了《金瓶梅》在匈牙利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和它的持久魅力。
陳國“出師未捷身先死”,帶著終生的遺憾、牽掛著《金瓶梅》全譯事業(yè)離開了我們,但是他未完成的事業(yè)定會有后來人繼承,《金瓶梅》的匈牙利之旅還遠沒有結(jié)束。
參考文獻:
[1]溫秀穎、孫建成.《金瓶梅》英譯中的中西文化互動與關(guān)聯(lián)[J].中國翻譯,2014(6):78-81。
[2]Hajdu, P.Classic Chinese Novels in Hungarian Translation [J].中國比較文學,2014(4):110-119。
[3]余澤民.譯不完的《金瓶梅》[J].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15期。
[4]馬祖毅、任榮珍.漢籍外譯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史遷.舞臺上的“金瓶梅”——匈牙利“中國熱”浪潮中的一朵浪花[J].世界知識,1989(6):29。